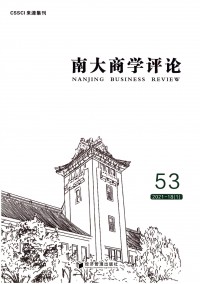威廉華茲華斯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威廉華茲華斯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威廉華茲華斯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記憶;自然;現(xiàn)實(shí);浪漫主義
1793年8月,23歲的華茲華斯曾獨(dú)自徒步旅行,游歷了風(fēng)景秀麗的懷河 (the Wye)河谷和古老的丁登寺 (Tintern Abbey)。五年之后偕其妹 Dorothy 重游故地,風(fēng)景依舊,而詩人卻意識到自己的感受與昔日已有所不同,于是發(fā)深遠(yuǎn)的幽思。其中既有對少年時代的留戀緬懷,又有對現(xiàn)代的評價和對未來的期待,一種淡淡的憂傷和對人生恬然自適的靜觀態(tài)度與詩人對自然的渴求和信念完美地揉合在一起,使這首詩成為代表華茲華斯藝術(shù)風(fēng)格與思想觀念最典型的作品之一。
《丁登寺旁》是華茲華斯在浪漫主義時期所寫。華茲華斯的最偉大的詩歌大多寫于1807年之前。閱讀這首詩時,你可以想象這個地方給你帶來的想象中的世界,你最喜歡的地方,想像風(fēng)景,顏色,氣味,思想,安全和滿足感。這就是華茲華斯在《丁登寺旁》描寫的情景。
丁登寺是華茲華斯年輕的時候去過的一個地方。它改變了他的生活。他長大了。五年后他故地重游,這次他的妹妹和他一起分享了這令人心曠神怡的經(jīng)歷。華茲華斯非常疼愛他的妹妹。縱觀他的一生,她是他忠實(shí)的陪伴,分享他的詩歌,幫助他的工作。他說,現(xiàn)在他回來,他長大了。他看到一個不同的丁登寺。當(dāng)前的景色和記憶中“心靈的畫像“(61行)之間令人費(fèi)解的差異讓詩人產(chǎn)生了一個錯綜復(fù)雜的冥想,在其中詩人評論了他的過去,評估(通過他作為中介的妹妹)了現(xiàn)在,預(yù)測了未來,直到悄悄地回到了他的出發(fā)地點(diǎn)。
這首詩一開篇作者就聲明五年過去了他又一次游覽這一地區(qū),感受到它的寧靜,質(zhì)樸的風(fēng)景,聽到潺潺的流水聲。他再次敘述了他看到的物體對他的影響:“陡峭的高聳的懸崖”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有了“更深入的隱居思想“,他靠在黑色的西卡莫樹上,注視著村舍-田地和果園里的樹,果子還是生的。他在樹叢中注意到村舍煙囪冒出的“裊裊的炊煙”,他想象著,他們可能會上升,從“樹林中流浪無房居民”,或從一個隱居在森林深處的洞穴。
詩人接著介紹這些“美麗的形式”的記憶是如何在他看不到的時候?qū)λa(chǎn)生影響的。當(dāng)他獨(dú)自一人,或在擁擠的城鎮(zhèn)和城市,他們給了他“甜的感覺,/在血液中,在心底深處”。樹林和農(nóng)舍的記憶讓他的腦海“恢復(fù)平靜”,甚至在他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影響他,影響他行善和施愛。他再次提到了是這些景色的記憶使他的心理和精神進(jìn)入一種狀態(tài),他感覺世界負(fù)擔(dān)減輕,其中他就變成了“活著的靈魂”注意到“生命的東西”。然后他說他相信樹林的記憶如此強(qiáng)烈地影響了他可能是“徒勞的”,但是如果是這樣,他仍然經(jīng)常在“焦躁的時刻”回想起這一經(jīng)歷。
第66行包含華茲華斯對他成長過程中三個階段的著名描述,他是以他與自然風(fēng)光的不斷發(fā)展的關(guān)系來定義的:年輕男孩的純生理反應(yīng)(73-74行);后青春期的疼痛,頭暈,模棱兩可的激情,讓人感到更恐懼的愛(行67-72,75-85:這是第一次游覽時他的精神狀態(tài));他目前的狀態(tài)(行85),其中第一次他在感官外補(bǔ)充了自己的想法。他對人類所遭受的苦難的認(rèn)識,在字里行間所感受的痛苦,像音樂的和弦讓他對景象的感覺更真實(shí)豐富也驅(qū)使著他。他還獲得了一種內(nèi)在的“存在”這一切把他的心和外部世界聯(lián)系了起來。
即使現(xiàn)在這一時刻這一環(huán)境,他過去的經(jīng)歷的記憶也不斷沖擊他對周圍景色現(xiàn)在的看法,重現(xiàn)這一切他有著苦樂參半的喜悅。他感覺快樂,他現(xiàn)在的經(jīng)歷將成為今后幾年許多美好的回憶。他承認(rèn),現(xiàn)在的他和以前的他是不同的,那時,作為一個男孩,他“傲群山之巔“,穿越潺潺溪流。在那些日子里,他說,自然構(gòu)成了他的整個世界:瀑布,山和樹林形成了他的激情,他的欲望和他的愛。那個時代已經(jīng)過去,他說,但他沒有悲傷,雖然他不能恢復(fù)其與自然的舊日的關(guān)系,他已經(jīng)得到了充分的補(bǔ)償,一套更加成熟的禮物,比如,他現(xiàn)在可以“看自然,而不是在一小時/沒有想法的青年時代,但時常/靜止的,悲傷的人性的音樂”。他現(xiàn)在可以在落日的余暉中,在海洋中, 空氣本身和人的思想中感受到更微妙,功能更強(qiáng)大的東西。這種能量對他是“一種運(yùn)動,一種精神,推動一個/所有思維的思想……/并通過所有的東西滾動”。出于這個原因,他說,他仍然熱愛大自然,仍熱愛山區(qū),牧場和森林,因?yàn)樗麄兺?恐罴儩嵉乃枷胍龑?dǎo)著他“道德人物”的核心和靈魂。
詩人說,即使他并沒有感到這樣或理解這些東西,這一天他仍然會有良好的心情,因?yàn)榕惆樗氖撬坝H愛的,親愛的妹妹”,也是他“親愛的,親愛的朋友“,觀察她的聲音、她的舉止,他看到的是他以前的自我,抱著“我曾經(jīng)是”,他向大自然祈禱,他可能會繼續(xù)禱告那么一小會兒,正如他所說, “大自然從來沒有背叛/愛她的心,而是將你帶到從歡樂到喜悅”。自然超越人的內(nèi)心的力量在于,它呈現(xiàn)力量,讓心靈不受“邪惡的舌頭”,“草率的判斷”, 和“自私的人”的影響,而是灌輸一個 “快樂的信仰”,即世界是充滿祝福的。詩人希望月亮照耀他的妹妹,風(fēng)對她而吹,他對她說,在以后的幾年中,當(dāng)她悲傷或恐懼,這段經(jīng)歷的記憶將有助于讓她恢復(fù)。而且,如果他自己死了,她能記住他對自然的愛與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她也會記得這片樹林對詩人意味著什么,以何種方式,在這么多年不見的情況下,它們對他而言變得更加親近,這既是它們的原因,也是因?yàn)樗幵谒鼈冎虚g。
當(dāng)詩人請求他的妹妹在懷河河谷記住他,他不僅是一個自然的崇拜者,“而是”作為一個具有更溫暖的愛的人,“更深的熱情”,“圣潔的愛”,可以肯定,他的感情就像子女對父母的孝順的感情。與此同時,他的感情強(qiáng)度的升級標(biāo)志著這份感情表達(dá)了他們的宗教崇拜,因?yàn)樗M麖?qiáng)調(diào),他想讓Dorothy相信五年后回到丁登寺的他是一個比之前更好的人,他的愛比在1793年“更加溫暖”,“更加深入”,更神圣(越來越像她這樣)。
《丁登寺旁》的主題是有關(guān)記憶的,具體地說,與自然之美交融的青年記憶。一般和具體而言,這一主題在華茲華斯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后來的詩“暗示的不道德頌” 重現(xiàn)了這一主題。 《丁登寺旁》是年輕的的華茲華斯對這一偉大的主題的莊嚴(yán)的聲明:即使是在成年后少年時心與自然純粹的交流的記憶也會存在,當(dāng)失去這種純粹的交流的途徑時,成年后成熟的心態(tài)也會為這一特定的交流提供補(bǔ)償,那就是“看待自然”和“傾聽音樂”的能力,也就是說,用一雙自然與人類生活相關(guān)的眼光來看待它。在他的青年時代,詩人說道,他沒有考慮自己與森林和河流的和諧統(tǒng)一,現(xiàn)在,五年后他舊地重游,他不再考慮不周,而是敏銳地意識到了眼前的美景賦予他的一切。此外,在妹妹面前他想象自己作為一個青年重新認(rèn)識自我。令人高興的是,他知道當(dāng)前的經(jīng)歷將成為他們兩個未來的回憶。就像當(dāng)他在林中游覽時他過去的經(jīng)歷與他眼前的景色總會交替出現(xiàn)在他眼前閃爍。
《丁登寺旁》是一部獨(dú)白,由說話者想象對自己說,引用其想像的場景的具體物體,偶爾說話的對象是其他人,一次是自然的靈魂,偶爾是說話人的妹妹。這首詩的語言驚人的簡單和直率,年輕的詩人絲毫沒有炫耀,而是以直言的方式從心底抒發(fā)感情。詩的意象主要限于詩人所活動的自然界中,雖然其中也有一些從航海到建筑的現(xiàn)在已丟棄不用的隱喻(“錨是詩人的純粹思想的記憶”)(思想是一個“宅第”的記憶)。
這首詩也有微妙的應(yīng)變的宗教情感,雖然丁登寺的實(shí)際形式?jīng)]有出現(xiàn)在詩中,但修道院――一個奉獻(xiàn)靈魂的地方的想法充滿著這首詩的場景,仿佛森林和田野本身就是說話者的修道院。這種想法在說話者對夕陽和人的頭腦的感覺描述中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他有意識地把上帝的思想、自然和人的心態(tài)聯(lián)系到一起,正如華茲華斯的余生中他的詩歌所體現(xiàn)的,是從“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平靜和自由”到不朽頌歌典型的概括。正是內(nèi)容和記憶的過程賦予他的詩歌生命之美和力量。我們在詩中感受到的是過去的經(jīng)驗(yàn)和當(dāng)前主動的、重要的關(guān)系。
在華茲華斯的詩歌中記憶過程通常會在他響應(yīng)自然界時運(yùn)轉(zhuǎn)起來,它是華茲華斯對自然界的回報,一次又一次他把自然看做人類幸福和滿足的巨大源泉。對大自然的熱愛,特別是湖畔地區(qū)景象、景色的熱愛對華茲華斯的性格和作品有著深深地影響,在那里他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成熟的時光。對他當(dāng)代和其后的思想和文學(xué)的影響是深遠(yuǎn)而持久的。他是一個高尚的抒情散文大師。
【參考文獻(xiàn)】
[1]陳嘉.英國文學(xué)史.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2]李正栓等編注.新編英國文學(xué)教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3]王佐良等主編.英國文學(xué)名篇選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
[4]朱維之,趙澧主編.外國文學(xué)簡編(歐美部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80.
威廉華茲華斯范文第2篇
英國桂冠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故事開始于坎布里亞郡北面的小鎮(zhèn)科克茅斯,1770年出生的他是家里五個孩子中的第二個。他家的房子是鎮(zhèn)里最氣派的,背靠德文特河河岸,能夠觀賞到四周環(huán)山的美景。
童年花園
詩人的父親是有權(quán)有勢的勞瑟家族的律師和人,他們的房子就是靠這份工作掙來的。一開始年輕的華茲華斯過著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家里人給予他完全的自由,在德文特河里游泳,和兄弟們?nèi)メ烎~,和妹妹多羅西在鄉(xiāng)間漫游,花園的圍墻外面就是德文特河在流淌,他還可以坐在岸邊,沉浸在書中打發(fā)一天,日子過得無比愜意。菜園里出產(chǎn)豐富,家里還有仆人,這樣天堂般的日子很快就結(jié)束了。
華茲華斯8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了,孩子們不得不接受祖父母或者不同的叔叔姑姑的照料。威廉被送到了霍克斯黑德文法學(xué)校,1779年至1787年在那里學(xué)習(xí)拉丁文、希臘文、數(shù)學(xué)、科學(xué)和文學(xué),據(jù)說每天都要上10個小時的課。妹妹多羅西被送到了哈里法克斯的一戶人家。孩子們就這樣分散了很多年。華茲華斯13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去世了,而且因?yàn)榕c雇主發(fā)生了爭吵,導(dǎo)致家里收入減少,孩子們的社會地位下降,同時孩子們也失去了童年時候的家。
與兄妹們分離,父母雙亡,對華茲華斯的詩有很大影響。比如《麻雀窩》,《致一只小蝴蝶》,都是在回憶小時候在科克茅斯度過的田園生活。在《麻雀窩》中詩人的妹妹多羅西變成了艾米蘭,“她給我一雙耳朵,一雙眼,銳敏的憂懼,瑣細(xì)的掛牽, 一顆心――甜蜜淚水的泉源, 思想,歡樂,還有愛。”在后來,多羅西記述了她再次回到第一個家的經(jīng)歷,那些通往河岸的臺地一直深深印在她的心里,再次見到已經(jīng)面目全非,她童年時期栽種的那些可愛的玫瑰和女貞樹籬因?yàn)闊o人修剪,漫天生長,古老的臺地被遮蓋起來,看不見了。
1937年,華茲華斯出生的家?guī)缀醣徊鸬簦慕ㄆ囌荆疫\(yùn)的是在截止日期前幾天,當(dāng)?shù)氐囊恍┤私M成的籌款委員會籌齊了1625英鎊,買下了房子,一年之后,當(dāng)?shù)匕逊孔咏唤o了英國國家信托。直到2004年的全面修復(fù)之前,科克茅斯的花園變成了草坪。
專家們經(jīng)過考古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了科克茅斯原先布局的很多線索,恢復(fù)成了現(xiàn)在我們熟悉的科克茅斯房子和花園。花園重新開始出產(chǎn)蔬菜,而且從房子里望去,景色宜人。但是2009年的一場可怕的洪水讓很多重建工作毀于一旦。洪水沖毀了花園的東墻,和多羅西記憶地的后墻。為了安全,臺地殘存的墻壁也不得不拆除。這個臺地不得不完全重建。這也為維修人員提供了機(jī)會,讓他們可以思考在花園中種什么,從而把更具有喬治亞時代趣味的植物重新引入到了花園中。讓花園與華茲華斯出生的18世紀(jì)70年代的風(fēng)格更接近。 鴿舍永遠(yuǎn)與詩人的浪漫詩歌聯(lián)系在一起。華茲華斯最主要的杰作在1807年之前完成了。
華茲華斯家的花圃中,如今有古老的玫瑰,藥用植物像拳參,草本植物像菘藍(lán),用于切花的藍(lán)刺頭,紫錐菊和傳統(tǒng)蔬菜,其中喬治亞時代的豌豆估計如今已經(jīng)很難在別處找到了。花園中還種了好多琉璃苣,旱金蓮,細(xì)洋蔥,鼠尾草,所有這些在18世紀(jì)都是可以用于餐桌的,花朵可以生吃,鮮美可口,也可用于為肉,魚提味,或者加入派中。沿著花園的磚墻,按照1768年的一本花園指南的要求搭起了橡木架,根據(jù)這本書的要求,為李子,蘋果和梨葡萄,鐵線蓮和玫瑰各搭建了所需要的格子。
雞窩附近圍著劈開的橡木柵欄,還種著榛子樹和柳樹。英國國家信托在重建時選用植物纖維和木樁,因?yàn)槿A茲華斯的時代只有這些材料。花園里的青梅,布拉斯李,莫利洛黑櫻桃掛著裝飾性名牌,使用的是當(dāng)?shù)氐目裳h(huán)的石片。
鴿舍時光
威廉和多羅西從童年時候就分開了,他們長大后夢想著能夠再次一起生活,但是很多事情都阻止這一天的到來。在劍橋求學(xué)期間,威廉到法國旅行,當(dāng)時正是法國大革命期間,威廉與法國女子安妮特墜入愛河。1792年,他們的女兒卡洛琳出生后,威廉打算與安妮特結(jié)婚,但是因?yàn)榫謩輨邮幒徒?jīng)濟(jì)窘境,不得不回到英國。在接下來的7年里,威廉有時與妹妹多羅西一同出游,但更多的時候是與詩人同行,朋友塞繆爾?柯勒律治游歷。
1799年威廉回到湖區(qū),開始向朋友們介紹他從小就熟悉的山脈,湖泊和河流。威廉和多羅西在格拉斯米爾小鎮(zhèn)找到一處房子,一年的租金只需8英鎊,從此開始了她作為一名信心鼓勵者、靈感激發(fā)者兼私人秘書的漫長的生涯。雖然后來這里被稱為鴿舍,但是威廉和多羅西從來沒用過這個名字,原來這里是個小酒館,名字是鴿子和橄欖樹枝。兄妹兩人非常高興,有時候他們的哥哥約翰也會過來住,而追隨威廉而來的柯勒律治住在附近,他經(jīng)常周末過來。
鴿舍的小樓不大,小院不寬,小門窄窄的,石片薄薄的,院墻也是矮矮的,一切都是那么謙恭,那么安靜,那么和諧。1799年,搬到鴿舍幾個月之后,威廉寫道,多羅西非常滿意這房子,她已經(jīng)開始設(shè)想在斜坡的上面再建一所夏天的避暑房子了。在斜坡上他們種了蕨類,塊莖植物和在散步過程中采集的或者當(dāng)?shù)厝怂徒o他們的野花。他們修葺了臺階,種了些能夠食用的蔬菜,可能是他們從科克茅斯的花園里就熟悉的豌豆,大豆,胡蘿卜和白蘿卜。沿著圍墻種了金銀花和玫瑰。
在這里威廉成了那個著名的桂冠詩人。對于他的崇拜者和追隨者來說,鴿舍代表了他創(chuàng)造力最旺盛的時期。在開始的幾年中,多羅西照顧哥哥的飲食起居,讓他能夠投身寫作和漫游。他們一起劈柴,一起挖地掘土,相互訴說,并且朗讀詩歌給對方聽。在鴿舍,華茲華斯寫了他最有名的有關(guān)花朵和自然的詩歌,比如膾炙人口的:我獨(dú)自漫游,猶如一朵云。
威廉華茲華斯范文第3篇
關(guān)鍵詞:華茲華斯 詩歌 回歸自然
華茲華斯是19世紀(jì)英國浪漫主義文學(xué)思潮的杰出代表,他的詩大多是描寫農(nóng)村的自然風(fēng)光,風(fēng)土人情。《孤獨(dú)的割麥女》是他的代表作,詩歌分三節(jié),以孤獨(dú)的收割人的歌聲為線索,以歌聲結(jié)合質(zhì)樸遼闊的畫面,表現(xiàn)了割麥女內(nèi)心豐富的世界。
詩人從自己獨(dú)特的心理感受出發(fā)來體察勞動者的歌聲,從而烘托出歌聲的優(yōu)美迷人。詩歌第一節(jié)描寫年輕姑娘一邊勞動一邊歌唱的景象,詩人經(jīng)過蘇格蘭高地,看到一個獨(dú)自一人的姑娘,一邊在廣闊的田野中勞作,一邊唱著凄婉的歌曲。詩人以過路人的身份提醒讀者,“請你站住,或者悄悄走過”,無聲無息,不動聲色,別打攪了沉醉在勞動和歌唱當(dāng)中的割麥姑娘。“你看你聽”的提醒,或站或行的靜觀默察,這些獨(dú)特心理感受無一不烘托出姑娘歌聲的感人肺腑,沁人心脾。畫面的背景由遠(yuǎn)及近,依次呈現(xiàn)。遠(yuǎn)處是高原峽谷,中間是遼闊的田野,麥浪翻滾,金黃燦爛,近處是一個年輕有力的姑娘,站在原野上,一邊勞動,一邊歌唱。空曠寬闊的高原田野,高遠(yuǎn)清爽天空,遍地金黃的風(fēng)舞麥浪,巧妙地烘托出歌聲的高亢悠揚(yáng),給人以空谷傳音,哀轉(zhuǎn)久絕之感。靜止的自然,勞作的人,凄婉動人的歌聲,三者和諧統(tǒng)一,構(gòu)成了一種獨(dú)特清幽的美,而詩人的心也在這美的境界中如醉如癡,流連忘返。
在第二節(jié)里,詩人提到“夜鶯”(nightingale)和“杜鵑”(cuckoo bird)這兩種鳥。它們都是吉祥鳥,夜鶯常象征希望(hope)、喜悅(happiness)。對于古往今來心細(xì)敏感的詩人們來說,它的啼叫常常能把夢幻與現(xiàn)實(shí),痛苦與歡樂聯(lián)系在一起;杜鵑是春天的寵兒,杜鵑聲聲打破了沉寂,代表寒冬逝去,賦予人們希望與喜悅,也代表詩人對大自然的一種愛戀和呼喚,盼望大地回春,萬物重生。詩人說“杜鵑聲聲”也不如這歌聲動人心腸,也反襯出勞動者歌聲能 夠打動人心,具有感染力的特點(diǎn)。在這首詩中,詩人就把割麥女的歌聲比作沙漠里的夜鶯和杜鵑的啼叫聲。但是在沙漠里行走的旅人是不可能聽到這兩種鳥叫的。詩人在這里是想借鳥鳴來襯托割麥女的歌聲。對世人來說,鳥類的嗚叫沒有特殊涵義,人類很少去留意。我們知道鳥叫是無止無盡的,這點(diǎn)卻與刈麥女的歌聲有相似之處。詩人認(rèn)為,它們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自然之聲,而不是塵世俗音。女孩獨(dú)自一人,身處曠野之中,她仿佛與自然連成一體。詩人用反襯的手法,突出了姑娘的歌聲遠(yuǎn)比夜鶯嗚聲、杜鵑啼聲動人心魄。割麥女的歌聲,不知涵義,也無聽眾,但無止無盡。“我凝神屏息地聽著,聽著”、“那樂聲雖早已在耳邊消失,卻仍長久地留在我的心上”。詩人聚精會神地聽,漫不經(jīng)心地走,完全沉浸在勞動者的憂郁凄美的歌聲里,不知不覺已登上了高高的山崗。當(dāng)他意識到姑娘已從他的視野中消失,歌聲已從他的耳際消逝時,他的心還長久地沉浸在歌聲美妙動人的世界里。
“誰能告訴我她在唱些什么?/也許她在為過去哀傷,/唱的是渺遠(yuǎn)的不幸的往事,/和那很久以前的戰(zhàn)場?/也許她唱的是普通的曲子,/當(dāng)今的生活習(xí)以為常?/她唱生活中的憂傷和痛苦,/從前發(fā)生過,今后也這樣?/不論姑娘在唱些什么吧,/歌聲好像永無盡頭一樣。”一個不期而遇的普通勞動者,一個孤獨(dú)的收割人習(xí)以為常的歌唱,華茲華斯能保持一份平等與關(guān)愛,一份真摯和善良,一份設(shè)身處地的理解體察,這正是華茲華斯人道主義高尚情操的體現(xiàn)。他聽,他猜想:姑娘也許在為過去哀傷,為不幸悲嘆,為戰(zhàn)爭垂淚;也許是為司空見慣的生活而歌唱。也許她在歌唱過去,或者她在歌唱未來,歌唱勞動,歌唱自然,她歌唱痛苦和憂傷,或許她又在歌唱幸福和希望……“不論姑娘在唱些什么吧,歌聲好像永無盡頭一樣”,她就是這樣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勞動者,像腳下的大地一樣質(zhì)樸、沉實(shí),像田野麥穗一樣充實(shí)、坦蕩,像深秋高空一樣寬容、忍耐。她用歌聲來歌唱生活,她用勞動來維護(hù)尊嚴(yán),她用胸懷來擁抱自然,擁抱生活,她是一位非常堅忍頑強(qiáng)、樸實(shí)樂觀的勞動者,一位可敬可贊的好姑娘。一個簡單質(zhì)樸的勞動人民能與自然如此和諧的相處,那么當(dāng)今的我們呢?詩人對她的歌聲所包含的內(nèi)容作出種種猜測感悟,引領(lǐng)我們在歌聲和想象中去了解一個勞動者的內(nèi)心世界。善解人意的理解,豐富的內(nèi)容,巧妙地烘托出姑娘歌聲的感情,讓我們透過歌聲,了解到一個勞動者的高貴的靈魂。我們心間有孤獨(dú)的收割人作伴,我們并不孤獨(dú)。
從整體上看,整首詩歌從詩人經(jīng)過麥田,見一少女放聲高歌,描寫歌聲蘊(yùn)涵,又不乏少女的向往和歡樂。詩人的情感與麥田的畫面少女的歌聲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共鳴,之后回想,仍念念不忘。這是全詩最重要的一個意境,也是它的精華所在。此意境創(chuàng)造了所謂“天人和一”的崇高境界,也成功地體現(xiàn)了華茲華斯自然抒情詩的原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詩歌的語言樸實(shí)、自然、簡單,華茲華斯的《孤獨(dú)的割麥女》用平實(shí)的描述去贊美自然,詩人呼吁人們回歸自然,他崇拜自然,在自然中尋求安慰,主張人類應(yīng)回歸自然以拯救人類的心靈,他欣賞大自然之美,在自然中尋求精神的安慰,以此來凈化被污染的心靈。在當(dāng)今工業(yè)社會,破壞自然破壞生態(tài),自然環(huán)境日趨惡化的形勢下,華茲華斯這位田園詩人的這種崇尚自然、親近自然的精神追求,現(xiàn)實(shí)意義尤為重大,也深深影響了在當(dāng)今社會的我們。(作者單位:貴州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
參考文獻(xiàn):
威廉華茲華斯范文第4篇
【關(guān)鍵詞】 杰弗里·哈特曼 華茲華斯 浪漫主義 文學(xué)印象
杰弗里·哈特曼作為學(xué)者,他筆耕不輟,發(fā)表著作頗豐,其中有一些引起西方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及好評的作品是我們得以窺探他的學(xué)術(shù)思想如何發(fā)展的重要研究資料,我們透過他的學(xué)術(shù)著作可以大概了解哈特曼的文學(xué)批評思想淵源和內(nèi)容。我們主要研究他在浪漫主義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所取得的學(xué)術(shù)成果。
一、杰弗里·哈特曼于浪漫主義解讀
哈特曼認(rèn)為,文學(xué)不是單純用來安慰或放松人們的心靈,實(shí)際上它的終極目的和遠(yuǎn)大志向是培養(yǎng)人們的一種理智的情感,即清除各種紛繁復(fù)雜的現(xiàn)象而獲得一種超越而神圣的美感。這種美感已經(jīng)徹底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機(jī)制的束縛,正是浪漫主義詩歌喚醒了審美主體的美感——一種對象化或意向性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就是哈特曼所謂的“理智的情感”。
哈特曼之所以進(jìn)行浪漫派詩人的詩歌研究,主要是因?yàn)楹芏喱F(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家對他們作品的文學(xué)價值評價不高,甚至批評浪漫派詩歌過于天真幼稚、矯揉造作和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浪漫主義文學(xué)在西方文學(xué)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時英美學(xué)界對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輕蔑態(tài)度激起了哈特曼的不滿和反抗。對浪漫主義詩人的再發(fā)現(xiàn),重新肯定他們在文學(xué)史的重要地位,也順應(yīng)了當(dāng)時美國社會的發(fā)展?fàn)顩r。
二、杰弗里·哈特曼對華茲華斯的解構(gòu)
1964年,哈特曼的第二部以華茲華斯及其他浪漫派詩人為研究對象的學(xué)術(shù)著作《華茲華斯的詩》,他在1971年再版《華茲華斯的詩》一書的序言中說:“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問題是華茲華斯‘意識的意識’,其他所有方面——包括心理學(xué)、知識論、宗教觀念、政治——都處于次要地位。”
1、想象之解構(gòu)。哈特曼反駁傳統(tǒng)學(xué)者將華茲華斯的詩歌視為只有通過殺害或者自然而創(chuàng)造出的充滿幻想或幻覺的詩歌,他在《回顧》中說:“我的觀點(diǎn)恰恰相反:由于對彌爾頓式的幻想詩歌的厭倦,華茲華斯預(yù)示了一種嶄新的對自然深感滿意的意識,或者至少這種意識在想象中不會侵犯自然。”哈特曼認(rèn)為,華茲華斯在面對自然時陷入一種對于幻覺或幻想的恐懼之中,他盡力在意識到來之前控制它的生成和發(fā)展,防范它與自然產(chǎn)生對立和沖突。哈特曼在華茲華斯的《孤獨(dú)的割麥人》、《邁克爾》、《露西》等詩歌的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了這個秘密,他強(qiáng)調(diào)詩人在審美欣賞和創(chuàng)作活動中的自我意識與想象的關(guān)系,尤其是“人格化”的想象這一概念,而非像其他研究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傳統(tǒng)學(xué)者那樣,僅從想象的創(chuàng)造性和社會性入手探討浪漫主義文學(xué)中想象這一范疇。
2、宗教觀之解構(gòu)。華茲華斯早期詩歌創(chuàng)作以自然泛神論為,他相信自然界的山川草木都是絕對而神圣的存在,同時他也認(rèn)為自然的人性像自然界一樣是另一種神圣而絕對的存在。在哈特曼看來,華茲華斯的是一種以自然泛神論為思想底色,用哲學(xué)和藝術(shù)相調(diào)和、相混融的顏料描畫自己所體驗(yàn)及所想象的情意化或人格化的自然,難怪華茲華斯自稱為“哲理詩人”。這種“哲理詩人”便是哲學(xué)、藝術(shù)和“純凈宗教”三者相結(jié)合的統(tǒng)一體,所謂“純凈宗教”則是既有“生活氣息”又有“高尚的思想”,“它的元素是無限,它的終極信仰是對自然事物的崇拜,它為自己劃定邊界的同時也與世俗達(dá)到了和解。”華茲華斯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意向性的自然在想象的引導(dǎo)下,超越了客觀的自然世界,生發(fā)出神圣而神秘的宗教情感,并且由此升華至天啟的審美境界,這樣詩人便獲得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意志”。
3、情感觀之解構(gòu)。要想達(dá)到天啟式的審美境界必須依靠感覺、想象和情感合力推動,這也是審美主體被賦予的自由意志。華茲華斯在《不朽的啟示》中表明了自己的觀點(diǎn):“幸虧我們借以生存的心靈,幸虧它的仁慈,它的喜悅和它的憂思,對我來說,就算是最卑微的鮮花也能引發(fā)超越眼淚的深沉的思想。”華茲華斯對自然與人的愛不僅賦予它們美妙的形式——“情感的存在”,同時還使之成為一種亙古不變的價值存在。哈特曼認(rèn)為:“詩人首先由客體元素組合而成的自然景觀出發(fā),也就是由客觀化的自我感覺出發(fā),在自我意識中以一種美好的印象呈現(xiàn)出來。再由感覺到精神暗示著某種向內(nèi)的轉(zhuǎn)向,尤其是“未經(jīng)到訪的景象”只存在于詩人想象世界里,詩人不再執(zhí)著于引起想象的客觀原因,即他忽略了認(rèn)知性和審美性相統(tǒng)一的感覺或感知。哈特曼認(rèn)為,詩人的人生具有二元性的特征,也就是內(nèi)在與外在、積極與消極、主體與客體相結(jié)合的人生,這種二元對立與統(tǒng)一的狀態(tài)就像潮汐一樣跌蕩起伏。華茲華斯不僅沒有忽視由自然現(xiàn)象生發(fā)的審美感覺和審美感知,而且更加重視由感覺向想象的過渡和轉(zhuǎn)化,以及感覺和想象之間的關(guān)系。
三、杰弗里·哈特曼于浪漫主義文學(xué)中自我意識的形成
一種被稱為“治療的智力”的術(shù)語深受哈特曼的關(guān)注,它可以補(bǔ)救和治愈趨向毀滅的自我心理分析和自我意識,而且它與某種傳統(tǒng)的受到宗教控制的智力不同,它是一種誕生及成長于浪漫主義時期的特殊的精神療愈措施。哈特曼認(rèn)為華茲華斯也經(jīng)歷過一段時間內(nèi)他遭受到自我意識和自我心理分析的一場斗爭。這種常見的人生現(xiàn)象通常發(fā)生在詩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前期,它會影響詩人前期創(chuàng)作思想的成熟,但是很多浪漫主義詩人仍然不畏艱辛躬身探索這危險的成熟之路。
哈特曼強(qiáng)調(diào)那些深埋在過去的非自我意識狀態(tài)里的內(nèi)容,這種隱藏在非理性的潛意識中的“力量”在創(chuàng)作活動的某一時刻綻放成曇花一現(xiàn)的靈感和頓悟,它比后天累積的知識更加珍貴難得。自我意識從混沌的非自我意識或者意識的整體里分離出來之后,對自我的存在方式做出深刻的反思,從而形成所謂的“第二個自我”,也就是竭盡全力征服和超越原來的自我意識,并且在更高的層面上以否定而辯證的方式達(dá)到復(fù)歸“存在的整體”的存在狀態(tài)。這樣的過程無疑是為了“喚醒深埋在過去的非自我意識狀態(tài)里的內(nèi)容”,也是為了還原那個“整體的人”。只有如此,才能成為最終與自然合而為一的“整體的人”,也才能獲得創(chuàng)造浪漫主義神話的想象、情感和信仰。
參考文獻(xiàn)
[1] Geoffrey H. Hartman, Wordsworth’s Poetry, 1787-18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2] Geoffrey H. Hartman, The Unremarkable Wordsworth, London: Methuen, 1987
[3] [英]拉曼·賽爾登編:《文學(xué)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xiàn)在》,劉象愚、陳永固等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版
[4] [美]林塞·沃特斯,《美學(xué)權(quán)威這樣批判》,昂智慧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
威廉華茲華斯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華茲華斯不僅是英國19世紀(jì)杰出的抒情詩人,也是有著自己獨(dú)立詩歌觀念的詩歌理論家。華茲華斯主張詩歌的情感、題材、語言和創(chuàng)作目的都要以“快樂”為起點(diǎn)和終點(diǎn),“快樂”成為其詩學(xué)中的核心理念,這就構(gòu)筑了他獨(dú)具個性與魅力的“快樂”詩學(xué)。在這種詩學(xué)觀念的指導(dǎo)下,華茲華斯的詩歌充滿了一種崇高的自然與人間之愛及其獨(dú)到的倫理內(nèi)涵,成就了其詩歌在英國乃至世界詩歌史上的地位,并對當(dāng)今世界的詩歌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是橫跨兩個世紀(jì)的英國大詩人,其詩歌藝術(shù)和詩學(xué)理論是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普遍關(guān)注的一個熱點(diǎn)。從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來看,在研究對象方面,“已有的研究涵蓋了他的自然觀、社會觀、民主觀、主題性復(fù)歸、時間性修飾、意象意境、詩歌語言、詩歌題材等眾多領(lǐng)域”…;在方法論方面,已經(jīng)有心理學(xué)研究、新歷史學(xué)主義批評、文本批評、性別批評、西方批評、解構(gòu)主義批評,這說明國內(nèi)外的華茲華斯詩歌研究成果頗為豐碩。然而,我們深以為憾的是,人們忽略了華茲華斯對“快樂”的理解與闡釋,以及其背后豐厚的詩學(xué)意義和倫理價值。而從華茲華斯的詩學(xué)理論和詩歌藝術(shù)綜合來考察,“快樂”無疑是其基本要素之一;無論從其詩學(xué)觀念還是詩歌藝術(shù)實(shí)踐來看,它都有著潛在的深層內(nèi)涵,并且維系著其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和邏輯性。可以這樣說,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xué),在當(dāng)時英國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對詩學(xué)理論起著拓展作用,對當(dāng)今世界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歌理論也富有相當(dāng)?shù)膯⒌弦饬x。
一、
統(tǒng)一性與邏輯性: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xué)
華茲華斯的詩學(xué)理論,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抒情歌謠集”1800年版序言》和《“抒情歌謠集”18l5年版序言》這兩篇長文中。從總體上來說,其關(guān)于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理論,主要包括對“情感”、“題材”、“語言”、“創(chuàng)作目的”等幾個方面的理解與認(rèn)識。無論從華茲華斯自己所撰寫的兩篇序言來看,還是從其詩歌藝術(shù)經(jīng)營來看,“快樂”始終都是其中隱伏的一條主要線索和一個重要的詩學(xué)主旨。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xué)具有豐富而獨(dú)到的內(nèi)涵,主要體現(xiàn)在:
首先,詩歌中的情感應(yīng)當(dāng)是一種以快樂為主的情感。華茲華斯認(rèn)為:“詩是強(qiáng)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詩人沉思這種情感直到一種反應(yīng)使平靜消失,就有一種與詩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漸發(fā)生,確實(shí)存在于詩人的心中。……然而不管是一種什么情緒,不管這種情緒達(dá)到一種什么程度,它既然從各種原因產(chǎn)生,總帶有各種的愉快;所以我們不管描寫什么情緒,只要我們自愿地描寫,我們的心靈總是在一種享受的狀態(tài)中。”這是一段常常為人所引用的話,不過,引用者多半是以此來說明詩歌情感的來源,即詩歌往往來源于詩人對于過去生活的一種回憶。其實(shí),華茲華斯在這里所表達(dá)的詩學(xué)思想遠(yuǎn)沒有那么簡單。筆者認(rèn)為,這段詩學(xué)名言中涉及到了這樣幾個問題:其一,詩歌的本質(zhì)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其二,詩歌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詩人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向詩歌逐漸遷移并流人詩中的過程;其三,詩歌創(chuàng)作是在一種自愿并且自然的情況下完成的,強(qiáng)調(diào)詩歌藝術(shù)的自主性與自由度;其四,詩人的情感是愉快的,而詩歌中的情感是詩人情感的流入,可以推斷也是愉快的,并且,詩人在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中是一種享受的狀態(tài),自然也是一種愉快的狀態(tài)。在這四個方面的詩學(xué)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快樂”詩學(xué)思想。我們也許應(yīng)當(dāng)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詩人能夠回憶起來的情感是從哪里來的?其邏輯起點(diǎn)是什么?華茲華斯在《頌詩——憶幼年而悟永生(永生頌)》一詩中這樣寫道:“兒童既然是成人的父親,,我就能希望自然的敬愛/把我的一生貫穿在一塊。”詩歌對兒童的天性作了高度的贊美。在這首詩中,華茲華斯認(rèn)為:“嬰幼時,天堂展開在我們身旁!/在成長的少年眼前,這監(jiān)房的/陰影開始在他周圍閉合,/而他卻是/看到了靈光和發(fā)出靈光的地方,他見了就滿心歡樂;/青年的旅程日漸地遠(yuǎn)離東方,/可仍把大自然崇拜、頌揚(yáng),/在他的旅途上陪伴他的,/仍有那種瑰麗的想象力;/這靈光在成人眼前漸漸黯淡,/終于消失在尋常的日光中問。” “兒童是成人的父親”,其理由在于:兒童生活在天堂里,擁有著瑰麗的想象力和與大自然高度的親和力;更重要的是,兒童總是自由而快樂的,他正是由此與成人區(qū)別開來。華茲華斯要表達(dá)的真正意思,正如約翰·比爾所指出的那樣:“華茲華斯真正要寫的是,兒童出A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上帝自己;正是神圣自然中保留的這莊嚴(yán)的光輝,才將其周圍的世界變成了‘天堂’。”
“也就是說,華茲華斯認(rèn)為兒童是人間和天堂(上帝)的直接聯(lián)系者。如此說來,華茲華斯所要回憶的便是兒童時期在天堂里的感覺了,正是它為詩歌提供了一個情感的源頭。這樣的回憶性的情感同樣是快樂的,當(dāng)然,也包括無拘無束的想象力和與大自然的渾然一體。因此,從邏輯上講,從兒童時代的天堂之樂到對它的深情回憶,冉到詩人情感的進(jìn)入詩歌,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的整個過程,在華茲華斯看來都是一個享受的過程,而“快樂”則是這種感覺的根本所在。
其次,詩歌的題材就是詩人的情感,在具體的詩歌作品里情感與題材往往是一種一體化的形態(tài)。華茲華斯曾經(jīng)這樣認(rèn)識詩的題材:“題材的確非常重要!因?yàn)槿说男撵`,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夠興奮起來。”他看重的詩歌題材好像只是來源于詩人的心靈與詩人心靈的刺激與震動。當(dāng)然同時他也認(rèn)識到:“是情感給予動作和情節(jié)以重要性,而不是動作和情節(jié)給予情感以重要性。”如此看來,華茲華斯認(rèn)為只有以情感作為詩歌藝術(shù)的推動力,將題材有機(jī)地組合成為合理的動作或是情節(jié),才能創(chuàng)作出真正完美無缺的詩篇。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情感和題材的契合點(diǎn)到底在哪里?我們還是只有從華茲華斯自己的論述中來尋找。華茲華斯曾經(jīng)這樣說過:“只有愉快所激發(fā)的東西,才能引起我們的同情。”同時他還曾經(jīng)這樣強(qiáng)調(diào):“沒有一種知識,即是,沒有任何的一般原理是從思考個別事實(shí)中得來的,而只有由快樂建立起來,只是憑借快樂而存在我們心中。”而詩人所能做的是一些什么呢?詩人往往依據(jù)人自己的本性和他的日常生活來看人:“覺得到處都有事物存心中激起同情,這些同情,兇為他天性使然,都帶有極大的愉快。”我認(rèn)為,華茲華斯的論述隱含了這樣幾個問題:其一,詩人對詩歌和生活的態(tài)度是人之本性,立足點(diǎn)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其二,人(包括詩人)在不斷地與外界事物發(fā)生作用和反作用,這種相互作用的發(fā)生是情感的誘發(fā)因素;其三,由于詩人創(chuàng)作詩歌的基點(diǎn)是人之本性和日常生活,詩歌具有著與外界(包括讀者)天然的親緣關(guān)系,容易將外界事物演變?yōu)樵姼桀}材,促成詩歌藝術(shù)的誕生;其四,外界事物刺激詩人,詩人憑借詩歌與外界發(fā)生情感的交流都是由于愉快之情的誘發(fā),而讀者與詩歌發(fā)生共鳴,引發(fā)同情,其最終也是為了獲得愉快。由此可見,在華茲華斯這里,題材和情感的契合點(diǎn)確實(shí)是詩人內(nèi)心的快樂。讓我們看一看華茲華斯的名詩《我們是七個》的片斷:“‘可他們兩個都已經(jīng)死去!/靈魂已升進(jìn)了天國!’/這些話全都是白說,,/這位小姑娘還是不改嘴:/‘不,我們是七個,’她說。”按照常理來推斷,兩位親人離去本應(yīng)是很悲傷的事情,可是這位小姑娘執(zhí)拗地堅持她們七兄妹是同在的,其原因就在于那個小姑娘對生死的看法本位于快樂的原則;詩人在此淡化人間的生死,其實(shí)質(zhì)是看到了親情給人帶來永遠(yuǎn)的愉快。綜上所述,從詩歌選取題材的原則、在詩歌藝術(shù)的實(shí)踐以及詩歌客觀的藝術(shù)感染力、詩歌文本的客觀呈現(xiàn)來看,“快樂”都在其中擔(dān)負(fù)著樞紐的作用。
再次,詩歌的語言應(yīng)當(dāng)是美麗而富于趣味的。華茲華斯對于詩歌的語言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論述,他說:“這些詩的主要目的,是在選擇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節(jié),自始至終竭力采用人們真正使用的語言來加以敘述或描寫,同時在這些事件和情境上加上一種想象力的色彩,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平常的狀態(tài)下呈現(xiàn)在心靈面前·真實(shí)地并非虛浮地探索我們的天性的根本規(guī)律……使這些事件和情境顯得富有趣味。”將這段關(guān)于詩歌語言的話和他提出的選取題材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合起來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的統(tǒng)一性和相異性:其統(tǒng)一性表現(xiàn)在語言運(yùn)用的立足點(diǎn)是人之天性和日常生活情節(jié);其相異性體現(xiàn)在想象力的滲入使得詩歌的文本形式又迥異于生活的一般形式,造成詩歌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距離,從而獲得一種陌生化效果。詩人創(chuàng)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詩歌藝術(shù)對事件和情境的糅合而具有趣味性,也就是快樂的營造與獲得。如果能夠與詩歌的情感、題材吻合起來,就可以使得詩歌藝術(shù)具有一種統(tǒng)一性。在華茲華斯看來,語言的使用存在一個歷史性與現(xiàn)時性的問題。
歷史上出現(xiàn)的優(yōu)秀詩歌創(chuàng)造了優(yōu)美純粹的語言,而語言的反復(fù)使用又會使其從優(yōu)美墮為俗濫;同時,語言必須與時俱進(jìn),適合人們的Et常現(xiàn)實(shí)生活,方能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為此,華茲華斯認(rèn)為詩歌語言的使用要合情合理。他說:“我想使我的語言接近人們的語言,并且我要表達(dá)的愉快又與許多人認(rèn)為是詩的正當(dāng)目的的那種愉快十分不同,……我希望這些詩里沒有虛假的描寫,而且我表現(xiàn)思想都是使用適合于它們各自的重要性的文字。……這樣做有利于一切好詩的一個共同點(diǎn),就是合情合理。”如此看來,華茲華斯對詩歌語言提出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對人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進(jìn)行真實(shí)描寫,探索人性的根本規(guī)律,傳達(dá)詩歌應(yīng)有的愉,追求語言使用的情感性、愉、合理性、生活性的多位一體。
第四,詩歌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于使讀者能夠感到一種少有的愉快。華茲華斯說過:“詩人希望把他的情感接近他所描寫的人們的情感,并且暫時完全陷入一種幻覺,竭力把他的情感和那些人的情感混在一起,并且合而為一,因?yàn)橄氲剿拿鑼懹幸粋€特殊的目的,即使人愉快的目的。……詩人做詩只有一個限制,即是,他必須直接給一個人以愉快。”。人們之所以喜歡讀詩是為了什么?也許有的人認(rèn)為是為了了解詩人的情感,也許有的人認(rèn)為是為了尋求一種美感。華茲華斯則明確地指出人們讀詩就是為了尋求快樂。詩歌創(chuàng)作是為使人愉快的思想,也明顯地體現(xiàn)在華茲華斯的詩歌藝術(shù)實(shí)踐中。其詩作《布萊克大娘和哈里·吉爾》講述了一個地主和窮人的故事:布萊克大娘不堪嚴(yán)冬的寒冷而去偷地主哈里·吉爾的籬笆來燒火取暖,結(jié)果被哈里·吉爾捉住了,大娘向天祈禱哈里-吉爾不再感到溫暖,哈里·吉爾終于受到上帝的懲罰,而永遠(yuǎn)失去了溫暖的感覺。這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掩蓋了一個嚴(yán)肅的問題:大娘和地主之間的矛盾本是激烈的階級矛盾,大娘的悲慘遭遇和哈里·吉爾的奢華生活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詩人并沒有將沖突的解決訴諸血與火的暴力,而是極力加以淡化,借用上帝的力量來懲處人間的罪惡。這樣的處理方式的真正用意,在于以“善”感化“惡”而最終達(dá)到消泯惡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為了將情感的宣泄導(dǎo)向平靜與美善,從而促成讀者對詩歌藝術(shù)接受體驗(yàn)愉悅感的充分實(shí)現(xiàn)。
華茲華斯“快樂”詩學(xué)思想體現(xiàn)出了一種比較嚴(yán)密的邏輯性。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其一,華茲華斯把詩歌的情感來源定位于人之記憶領(lǐng)域,強(qiáng)調(diào)人之主體感受性與外在世界的交感融合,從而導(dǎo)致了某種情感因素在記憶領(lǐng)域的貯存,期待著詩歌創(chuàng)作的喚醒、重現(xiàn)以及藝術(shù)化展現(xiàn)。其二,華茲華斯利用“沉思”來實(shí)現(xiàn)情感從記憶領(lǐng)域到藝術(shù)領(lǐng)域的轉(zhuǎn)化,詩人以個體之情感來感受、體味人類普遍性情感,實(shí)現(xiàn)詩人情感由“小我”向“大我”的提升;“沉思”也體現(xiàn)為詩人尋找特定的藝術(shù)媒介,如藝術(shù)體裁、語言、韻律等,從而實(shí)現(xiàn)記憶領(lǐng)域之自然性情感向藝術(shù)情感的轉(zhuǎn)化,并尋求與詩歌藝術(shù)媒介的高度契合。
對于情感的表現(xiàn),華茲華斯用“合情合理”加以調(diào)節(jié)和控制,一方面是在反抗西方詩學(xué)史上對情的壓抑的傾向,另一方面合理地“糾正了浪漫主義詩學(xué)可能造成的濫情主義”。《我們是七個》和《布萊克大娘和哈里·吉爾》兩首詩,對于親人死去的哀痛以及階級之間殘酷的欺壓與迫害,作者對其情感的表露都維系在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較為恬淡、平和的情緒氛圍中,并且用理想化的“‘不,我們是七個,’她說”和上帝的懲戒來尋求心理的安慰與矛盾解決的良方;同時也維系了華茲華斯詩學(xué)情感的快樂色調(diào)及其藝術(shù)魅力,顯示了華茲華斯極其深厚的詩學(xué)修養(yǎng)。華茲華斯的詩學(xué)理論呈現(xiàn)出完整的流程性與邏輯性:記憶(情感的貯存)——沉思——創(chuàng)作——合情合理。整個流程顯示了華茲華斯既是詩人又是理論家的雙重身份,而從“沉思”與“合情合理”的關(guān)系來看,“合情合理”昭示了其獨(dú)立的詩歌主張,即詩歌應(yīng)該給讀者以或教益,“情”與“理”并舉;“沉思”不僅體現(xiàn)為情感與藝術(shù)媒介的契合,也是“情”與“理”沖突緩解的中介。故而“沉思”與“合情合理”維系了華茲華斯“快樂”詩學(xué)的一體性以及創(chuàng)作上的可行性,共同鑄就了其“快樂”詩學(xué)的美學(xué)魅力。
總的來說,華茲華斯“快樂”詩學(xué)的基本內(nèi)涵,就是強(qiáng)調(diào)作為詩之基本要素的情感、題材、語言、創(chuàng)作目的,都要有“愉快”的因素,認(rèn)為“愉快”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起點(diǎn)也是終點(diǎn),它維系著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的統(tǒng)一性、協(xié)調(diào)性、邏輯性;其詩歌藝術(shù)文本給人一種清新淡雅的愉快之美,完美地演繹了其詩學(xué)主張。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詩歌藝術(shù)實(shí)踐上講,華茲華斯終其一生都在極力構(gòu)建一種具有重大意義與價值的“快樂”詩學(xué)。
二、去庸俗化:“快樂”詩學(xué)的倫理內(nèi)涵
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xué)涉及到了詩人、詩歌藝術(shù)、讀者三者的內(nèi)在關(guān)系,而其立足點(diǎn)則是人性之本與日常生活,也就是如何看待生命本身和生命如何存在與怎樣發(fā)展的問題,即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人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問題。華茲華斯對此發(fā)表了極為重要的意見,這種詩學(xué)思想以及在其中蘊(yùn)涵的深厚的倫理內(nèi)涵,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首先,華茲華斯認(rèn)為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才會有生命的趣味產(chǎn)生。他曾經(jīng)這樣指出:“他(詩人)以為人與自然根本互相適應(yīng),人的心靈能照映出自然中最美最有趣味的東西”,同時“詩是人和自然的表象”。這不僅道出了人與自然的真實(shí)關(guān)系,并且也確認(rèn)了詩歌作為一種藝術(shù)體式同人與自然都具有一種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華茲華斯認(rèn)為自己被大自然賦予了一種成功和藝術(shù)評論家必須擁有的品質(zhì),而他也因這一言論而“名聲大噪”l7l720如此看來,自然給人以感化與啟迪,人也能感應(yīng)自然界中美和趣味的東西,二者互相適應(yīng),具有一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交感性,而詩歌正是二者交感的藝術(shù)表征。
從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來講,自然無疑是藝術(shù)來源的給養(yǎng);從倫理上講,自然往往給人的心靈以凈化,使人的靈魂得以超升,擺脫功利的約束而進(jìn)入自由之境。華茲華斯在《寫在早春的詩行》中這樣寫道:“大自然使我軀體中的靈魂/同大自然美好的作品結(jié)合;/我呀,想起了那問題就心疼:/人把人變成了什么?/……/IN下伸展的帶嫩芽的枝梢/扇子般地招引輕柔的風(fēng)兒;/任我怎么樣,我不由得想道:/那中間也有著歡樂。”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其一,大自然具有凈化人類靈魂的力量,也具有一種與人類靈魂親和的質(zhì)性;其二,人類離開了大自然面臨的只是靈魂的異化,人類脫離了正常人性發(fā)展的軌道,就會遠(yuǎn)離生命的本真形態(tài);其三,在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快樂的,那里才是美好的天堂、人間的樂土,人類應(yīng)該學(xué)會像大自然中的生命共同體那樣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總之,華茲華斯通過人與大自然的關(guān)系給讀者留下的倫理學(xué)啟示是:大自然中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人類相處的理想模式,人類理應(yīng)接受大自然的浸染、熏陶,讓生命與生命之間和諧相處,抵制功利對靈魂的蒙蔽與異化,從而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快樂。
其次,人與社會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人只有在一定的社會中才能生存與發(fā)展,社會的發(fā)展也離不開人的個性、氣質(zhì)與風(fēng)采。華茲華斯認(rèn)為人是社會的構(gòu)建因子,社會是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人的個性在社會中得以彰顯,同時又要受到社會性的制約。而華茲華斯常常把人和社會的關(guān)系上升到整個宇宙的高度,從而在一個人、自然、社會乃至整個宇宙的宏大場閾下來確立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guān)系,“華茲華斯意在拓展我們對一個非個人的宇宙之偉大性的激賞,直到我們學(xué)會將我們自身界定為所有無數(shù)生命中不可分離的一份子,離開了它們,我們將無從存在”。而在這個宏大的場閾關(guān)系網(wǎng)中,人以獲得愉快為其立身之本,愉快的獲得演變?yōu)槿伺c人之間的愛和崇高的熱情。華茲華斯在《詩行:記重游葳河沿岸之行》這首詩中多次提到“歡樂”:“而在城鎮(zhèn)和都市的喧鬧聲里,/在我困乏地獨(dú)處屋中的時候,這些景致會給我甜美的感覺,/會使我血脈和順又心頭舒暢;/它們進(jìn)人我心靈深處,使那些/沉睡著的往日歡樂感情開始”,“歡樂具有的神威使我們目光/沉靜,看清事物的生命/……/我在精神上多少次求助于你!/……靈上的圖景再次蘇醒過來;/我站在這兒,體會現(xiàn)時的快樂,/也高興地想到在這個時候還將/給未來歲月增添生氣和精神/食糧/……/自然也就是我的一切”。這首詩里所表達(dá)的思想是極其深刻的:人、自然界、社會構(gòu)成一個宏大的宇宙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中介。因此,人從自然界吸取精神食糧,向深處能夠體味人性與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價值,向廣處能夠反省社會的現(xiàn)時狀態(tài)。詩人認(rèn)為都市和城鎮(zhèn)的喧鬧不適合生命的詩意棲居,而只有向自然朝拜,從那里激發(fā)人性之圣潔的愛,從而整合現(xiàn)時的社會矛盾,理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從情感上講,只有這樣人才能獲得歡樂;從倫理上講,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真誠而合理。正是人與自然、社會構(gòu)成了華茲華斯認(rèn)識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主線:大自然——人(歡樂)——認(rèn)識人性、激發(fā)圣潔之愛——反觀社會、從而構(gòu)建合理社會,而“歡樂”正是這條主線的情感本體,社會倫理道德則是其潛在的衍生。
再次,人與詩歌及藝術(shù)的關(guān)系是一種共生共存的關(guān)系,人能夠從詩歌與藝術(shù)作品里獲得啟示與真理。華茲華斯曾經(jīng)這樣說過:“詩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詩人唱的歌全人類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覺高興”,“詩是一切知識的菁華”,“詩人是捍衛(wèi)人性的磐石,是隨處都帶著友誼和愛情的支持者和保護(hù)者”,“詩是一切知識的起源和終結(jié),——它像人的心靈一樣不朽”在這里,華茲華斯確立了詩人和詩歌的崇高地位,也就間接地確立了人與詩歌藝術(shù)的關(guān)系:人要接受詩歌藝術(shù)的陶冶,從中獲得啟示、知識、真理,并且也能認(rèn)識人性,作一個詩歌藝術(shù)的追隨者和合唱者。華茲華斯在早期的一首詩中曾經(jīng)這樣歌唱:“詩人給我們崇高的愛和關(guān)心,/愿他們永遠(yuǎn)受到祝福和稱頌,/他們神圣的歌使世上的我們/生活在真理和純真的歡樂中。”從這里可以看出,華茲華斯給詩歌與藝術(shù)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僅是藝術(shù)上的要求,并且是倫理上的要求。他認(rèn)為讀者要從詩歌藝術(shù)中獲得真理和崇高的愛,從而構(gòu)建個人靈魂的底蘊(yùn),再以此升華開去,使得整個社會都統(tǒng)籌在真理、愛和關(guān)心之中,如此,個人、詩歌藝術(shù)、社會都將為歡樂所充滿,并且獲得理想的發(fā)展模式。
- 威廉·福克納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受獎演說
熱門文章排行更多
相關(guān)期刊更多
南大商學(xué)評論
CSSCI南大期刊 審核時間1-3個月
南京大學(xué)長江三角洲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學(xué)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和發(fā)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學(xué)商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