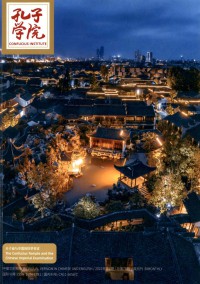孔子刪詩說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孔子刪詩說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孔子刪詩說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孔子 樂教 樂得其道 述而不作 禮樂交錯
中圖分類號:G71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08-0009-02
當前,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的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為了適應信息科技的變革,學界提出了E-learning,C-learning,U-learning等學習方式的創新,更有甚者,為了突出信息文明對工業文明“三中心”教育方式的超越,提出了系統的G-learning變革理念。G-learning作為一種倡導“綠色學習”的觀念,強調信息文明境遇下科技與人文的融合,倡導回歸到人類軸心時代古典的人文智慧。
我作為一個普通的音樂教育者,正是立足于信息時代綠色教育的視野,深入探討孔子的樂教思想,力圖為當前音樂教育傳承古典樂教智慧提供參考。下面,本文具體從“樂得其道:樂教之宗旨”“述而不作:樂教之傳承”“禮樂交錯:樂教之實踐”三個方面展開分析,系統回答孔子樂教的宗旨、傳承以及具體實踐方法等問題。
一、樂得其道:樂教之宗旨
其一,樂教的審美本質是一種中和之美。《樂記?樂本》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人的內在心靈本來應該是安靜不動的,這是本性;但由于人與外物交往,內心有所感動,隨之產生了情,音樂正是表達情感的重要載體。但過于沉迷音樂,甚至被一些不良的音樂所熏陶、引導,并會出現“樂之失,奢”的流弊。因此,一方面肯定音樂在表達情感方面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音樂的不良影響,導向儒家“仁義之道”,所以,孔子樂教中強調的是一種“樂而不,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這種對中和之美的追求,也契合了孔子人生中庸之境的追求。
其二,君子成人教育的重要環節。孔子十分注重學習對于成就君子的重要作用,他在《論語?陽貨》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在孔子的六經君子成人教育中,樂教既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同時,在次第上,又代表了君子成人教育的最后一個環節,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這就是說,兒童的教育,應該隨順自然,通過詩,興起其美好的情感,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應該通過禮的社會規范來對情感進行理性的約束,從而適應社會秩序對人的要求,最終,教育的完成還需要實施樂教,讓理性回歸到情感,實現情理的和諧交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君子人格的實現也是快樂人生的達成,所謂“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禮記?樂記》)。
其三,理想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樂記?樂施篇》云:“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在《論語?陽貨》篇,還專門講述了一個孔子和弟子子游討論樂教治理社會的故事:“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菀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二、述而不作:樂教之傳承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為老彭”。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對此做了很好的詮釋,他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從司馬遷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一,孔子視野中的“樂”與“詩”“禮”是相互配合的一個整體,詩配上了音樂,并合上一定的禮數,從而,可以運用于祭祀、朝會、宴享等場合。孔子的此種樂教觀念是對更久遠的歌樂舞一體的聲教傳統的傳承,它是巫師通過自己的語音符號(歌)、身體動作(舞),再合上一定的音樂符號(樂)用以溝通神人的方式。《尚書?舜典》中也對此一體化的聲教傳統做了記載:“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二,孔子在刪詩正樂的過程中,盡管從形式上的一體化以及內容的采編上延續了傳統,述而不作,但在具體的“刪”“采”的過程中,也通過自身言傳身教的闡釋,凸顯了自身推舉的仁義之道,所謂“《雅》《頌》各得其所”,這樣,傳統文化獲得了新的生命,同時,孔子的仁義之道也能立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獲得教育的公共平臺,具有了強大的現實文教功能。
孔子不僅刪詩正樂,自身也是一個音樂發燒友,十分喜愛音樂,據《論語?述而》記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因此,孔子樂教對傳統的傳承就不僅體現在以上孔子刪詩正樂的工作中,還體現在他對古典音樂的具體修習實踐中,在《論語》中,就有多次這樣的記載,試舉幾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孔子在這里通過抒發對《韶》樂、《武》樂的欣賞感言,道出了美和善的關系,突出了儒家樂教之教人向善的旨歸。
子曰:“師摯之始,《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這里,生動地敘述了孔子從音樂開始到結束的審美體驗,體現了孔子對音樂的喜愛。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韶》樂是當時貴族中流行的古樂,孔子這段話不僅說明了其對古代音樂的癡迷,同時,也說明了孔子具有很高的音樂古典素養。
孔子自身對傳統音樂的修習以及刪詩正樂的文化整理工作,延續了古典的樂教傳統,充實了傳統樂教的仁義生命。
三、禮樂交錯:樂教之實踐
孔子刪詩說范文第2篇
“一句‘述而不作’,成為孔子一生治學特點的權威概括,也演化為某種扎實、不尚空言卻也帶有保守、無創新意向的學術風格”,后來卻影響了中國文化幾千年。根據孔子的記述,殷朝時代就已經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們根據歷史記載和《論語》中的相關言語,還是能有一個相當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時期乃至后世,人們一向都不太重視立言,人們所關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轉·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與范宣子的一段對話,穆叔對范宣子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沒有辦法的最后選擇,人們首先選擇的是要向古圣賢學習,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為圣人們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讓后代的人覺得他們的言語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時候廣招門徒,史書記載孔門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藝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來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編撰教材來傳授弟子,他所編寫的《詩》、《書》、《禮》、《樂》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獨創,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的,《詩》本來有三千多首,經他刪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詩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作為一個博學多識的人,為什么自己不獨創呢?因為在他看來,先王之道已經很完備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論傳達出來就行了,只是當時世道混亂,“禮壞樂崩”,本來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們忘記了,因此他才會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來教授弟子,好傳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貢曾經有過一段對話,“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說,只是為了教授弟子才去說那么多話。在孔子生前,他并沒有自己的專著,《論語》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為其編撰的。
孔子不注重言還與他的教學思想有關。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學成后對社會有所貢獻,他更多地是從修身即道德方面來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他看來,只要道德修好了,學不學文都無關緊要,只是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才去學文。從他對學《詩》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這一思想。“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學《詩》的目的是要為政治服務的,“興、觀、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還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更可以看出他“學以致用”的態度,如果一個人學那么多的詩而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應用,學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傳子夏傳經,曾子作《大學》,子思作《中庸》,都是來傳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樣郁郁不得志的情況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幾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蘭陵著書立說,他對為什么要學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經無所不包,只要學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說荀子的思想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脈相承的。
孔子刪詩說范文第3篇
關鍵詞:《關雎》 思無邪
《詩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前11世紀至前6世紀)。關于《詩經》的形成,說法不一。有“王官采詩說”,有“孔子刪詩說”。按照后一說法,《詩經》是孔子從先秦三千多首詩歌中刪減編撰出來的。我倒是愿意相信后一說法。這似乎為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找到某種邏輯。孔子在《論語 為政》里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謂“思無邪”,就是說詩歌的思想要純正,也就是沒有邪念、沒有雜念。孔子究竟是在什么語境里說出了這番話,我們無法知曉了。按照“孔子刪詩說”,我們不妨做如下推測。孔子的學生問孔子:老師,“詩三百”是怎么刪減出來的?孔子回答:以思想純正為標準,“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也就是說,“思無邪”是孔子刪詩的標準。符合這個標準的就被收錄進了《詩經》,不符合的不予收錄。如果這個推理成立的話,孔子把它放在《詩經》篇首的用意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關雎》是“思無邪”的最好例證,那么,《關雎》是怎樣體現“思無邪”呢?
我們先來重溫這首兩、三千年前的愛情詩,看看它是怎樣體現“思無邪”的。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不用懷疑,這是一首愛情詩。但卻不是愛情當事人寫的愛情詩,而是作為第三人的詩人記錄下的一對男女青年的求愛場景,如同一位高明的攝影師拍下的一組“鳳求凰”的動人場景。
首先,詩歌開篇就創造了一個熱烈激昂而又溫馨純美的意象,為詩歌主旨的表達做了一個很好的藝術鋪墊。整個故事都是在“雎鳩”的愛情奏鳴曲中拉開序幕的。象大雁、天鵝一樣,雎鳩也是一種愛情鳥。自然界中似乎只有鳥類的愛情符合人類愛情觀。那就是兩情相悅、彼此愛慕、終生廝守。白居易在《長恨歌》里寫到: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為什么他不在地面上找一種動物來象征愛情呢?因為在鳥類之外,他實在找不到另外的動物可以用來表征人類的愛情。獅子老虎行嗎?顯然不行。老虎是獨行俠,遇上誰就是誰,露水之歡,事后不負責任。獅子是群居動物,實行一夫多妻制,而人類的愛情是排他的。“老鼠愛大米”?更加不行。因為人類的愛情是“兩情相悅”,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占有。老鼠啃大米的聲音與雎鳩的“關關”情歌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關雎》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起興,即為人類愛情故事的展開作了藝術鋪墊,也為整個作品的風格定了基調。不難想見,春和景明,岸芷汀蘭,草木繁茂,清流婉轉。進入了戀愛季節的鳥兒們春心勃發,悅耳的鳴叫聲此起彼伏。就在鳥兒們的愛情奏鳴曲中,人類的愛情故事拉開了大幕。展現在我們面前的該是一個怎樣的愛情場景呢?
其次,詩歌展現了至純至美的愛情場景。《關雎》所表達的愛情卻是至純至美的。愛情這個主題既簡單又復雜。說它簡單,因為它表達的是男女之間的愛慕之情。對此,人人都懂。說它復雜,是因為它極易受到“污染”而喪失其純潔性。如果你是個億萬富翁,你很難判斷人家是看上了你還是看上了你的財富;如果你位高權重,你很難判斷人家是看上了你的權力地位還是看上了你。當今社會,當一個人的權力越來越大或財富越來越多時,女人離他越來越近,但愛情離他越來越遠。因愛而愛的愛情才是純潔的,因欲望驅動、陰謀驅動的愛情則是不純潔、甚至是邪惡的。即便在遙遠的上古時代,財富、社會地位同樣在左右著愛情和婚姻。如《詩經 鵲巢》正是反映了富、社會地位對愛情婚姻的干預。《詩經 鵲巢》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情感上原本另有所屬的,是“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造成了“鵲巢鳩占”的現實,這讓愛情的當事人該是怎樣的黯然神傷。在《關雎》展示的場景里,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沒有權力的威脅、物質的誘惑。我們沒有聽到“君子”在說“我爸是李剛”,也沒有聽見“君子”在炫耀自己的財富。有的只是心靈的碰撞和對知音的尋覓。我們看到的是“君子”對愛情的真誠、耐心與執著,是對“窈窕淑女”的人格尊重。
從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看,《關雎》對愛情場景的展現也是美輪美奐的。詩歌的作者如同一個高明的電影導演,在雎鳩的愛情奏鳴曲聲中,巧妙地運用鏡頭在“窈窕淑女”和“君子”之間進行畫面的反復切換。一會兒是楚楚動人的“窈窕淑女”,一會兒是“寤寐思服”的君子;一會兒是“窈窕淑女”的“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參差荇菜,左右d之”,一會兒是君子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在這些畫面的反復轉換過程中,我們雖看不到女主人公的面部表情,聽不到她的只言片語,但我們從詩人反復詠嘆的“參差荇菜”里不難體會出女主人公的心境。荇菜的參差不齊不正隱喻了她此刻心潮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心理狀態?哪個女子不懷春。面對這樣一個多情君子的真誠表白,姑娘早已是春心激蕩,不能自已。只是姑娘家的害羞和矜持讓她一時還不能對君子的追求做出回應。這反倒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此時無聲勝有聲。同時,男主人公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更讓我們仿佛從《動物世界》里看到鳥兒們為了愛情時而展示華麗的羽毛,時而放開美妙的歌喉,時而交頸高歌,時而凌波起舞的動人場景。真是真摯熱烈、美不勝收。
其三,詩歌的場景展現和情感表達尺度適中。正如孔子在《論語?八佾》里所說的:“《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這符合儒家倡導的“中庸之道”。
我們先看詩歌的情感表達。喜怒哀樂,人之常情。但情緒的表達要適中。儒家的先賢們曾以人的情緒變化為例來闡述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見,就個人的修養而言,情緒的控制是多么重要。情緒極端,乃小人之舉;情緒適度,才是君子之風。《關雎》中的君子乃真君子也。盡管他的求愛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窈窕淑女”的積極回應,盡管愛情的烈火使他“輾轉反側”、“寤寐思服”,但他獨自承受著愛的煎熬,而沒有因愛生恨,更沒有情緒的極端表現。對他人,沒有惡語相向、拳腳相加;對自己,也沒有痛不欲生、尋死覓活。相反,他對淑女的追求表現得極有分寸:熱烈而不犯粗魯,執著而不失理性。他“哀而不傷”,今天的追求沒有結果,明天依然去 “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相比我們所熟知的古往今來種種“因愛生恨”、“尋死覓活”的愛情悲劇,《關雎》所表現的對愛情的尊重,實在是可以為萬世垂范。
再看看《關雎》的場景表達。不用說,《關雎》是一首描寫男女情愛的詩。男歡女愛,天經地義。但是,對情愛描寫尺度的把握,既涉及到不同社會階段的倫理規范,又涉及文學作品的審美格調。孔子說“食色性也”。但這個論斷還沒有將人類與動物區分開來。動物窮其一生都在忙乎兩件事:食與性。前者是為了維護生命個體的存在,后者則是為了種群的延續。但動物有性無愛、有慈無孝。人類的愛情則不同。它基于性而高于性。《詩經》中有大量描寫愛情、婚姻的詩篇。這些作品對情愛的表達雖遠沒有達到現代文學作品中“豐乳肥臀”的直白程度,但也到了接近“”的邊緣了。如《野有死麇》描寫是男女青年的野合,“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兮”。這樣情愛場景的展示幾近現代電影中的“”了。《桑中》描寫的是男主人公從多名美女處漁色后的自鳴得意:她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似乎,美色是他的戰利品。這就顯得格調不高了。《坑忻貳訪櫳吹氖橋主人公孤獨的思春哀鳴。她連具體的戀愛對象都還沒有,但面對樹上成熟的梅子被人采走、越來越少(寓意著她的同齡伙伴一個個被人迎娶),眼看著自己就要成為“剩女”,她焦慮地呼號著“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謂兮”。少女懷春,無可厚非。但這種“傻大姐”似的嚎叫也實在缺乏審美價值。品讀《關雎》,我們既看不到“君子”伺機漁色的企圖,更體會不出任何寬衣解帶的暗示。在它所展現的愛情場景中,女主人公矜持而含蓄,男主人公熱烈而有度。它讓讀者的情感隨著“君子”時而低徊舒緩、時而激越奔放的琴瑟鐘鼓聲超越了物欲的羈絆。不論她的社會地位如何,一個能被音樂征服的女性該是怎樣的高貴?盡管直至詩歌的結束,這場真摯而熱烈的求愛都沒有明確的結果,但正因為如此,兩千多年來,《關雎》給它的讀者留下了無限廣闊而美好的想象空間。
孔子刪詩說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教學札記 《〈論語〉選讀》 師德理論 研究領會
林語堂先生說:“孔子對教育的看法,其見解、觀點是非常現代的”。作為中國教育史上一位影響至深至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創私學,刪經訂禮,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至今仍不失其光輝的一面。尤其是孔子教育思想中關于師德的論述,更受后人推崇,以致孔子被后世尊為“萬世師表”、“至圣先師”。他的影響“江漢已之,秋陽以曝之,皓皓乎不可尚也”。這主要是由于孔子高尚的師德,崇高的“人品聲望使人仰慕”(林語堂語)。但近年來,對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師德理論的研究和評估仍顯不足。研習和領會它,對教育工作者不無裨益。我在指導學生選修《〈論語〉選讀》時,偶有得,輒記之,以饗同仁。
作為一個唯道德論者,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綱領是相通的,認識論和倫理觀是統一的。孔子說:“六藝治于一也”(《史記•滑稽列傳》),即說明了這一問題。為實現同一目標,建立一個德化的大同世界,政治、道德、知識的教育是融為一體的。其中道德教育處于至尊地位。孔子一方面寓政治、道德教育于知識教育中;另一方面又通過知識教育以提高政治、道德的認識。教育思想是其政治“仁愛”綱領的內容之一。從“仁愛”的總原則出發,孔子對師的要求嚴格地統一在“修己安人”這個政治綱領之中。“修己”是人內在的道德修養和情操,是求仁獲仁,實現政治綱領的途徑;“安人”是外在的規范原則,是行仁。“修己”是“安人”的前提和基礎,“修己”的目的是奉著一顆“仁愛”之心去“安人”、“安百姓”。“安人”是“修己”的終極目的,體現在教師的道德觀念上,就是要求教師通過“不厭”的學,進行“修己”、“正己”,加強自身的文化素質和內在情操,從而奉著“不倦”的“誨人”精神去“正人”、“安人”。一方面通過知識的傳授“安人”;另一方面以自身的言行舉止、道德情操感化學生,即所謂“風行草偃”、“潤物無聲”,達到“安人”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提倡的言傳身教。后儒將孔子的這一思想闡發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八目。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正確認識孔子的有關教師的思想,是不能與其政治思想割裂的。以政治倫理為前提和向導的孔子的師德觀念,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
1.樂道敬業,誨人不倦
孔子大半生致力于教育事業,是非常看重樂道敬業的。在他看來,這是對教師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要求。他認為,教師,應不為名利所動,因此極力反對教師追名逐利,隨波逐流。要求為師者要“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要“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他非常擔心“道之不行”,說“吾道,一以貫之”,極力贊譽樂業精神。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爾。”“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也。”對顏淵執著的樂道精神他大加推崇,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最能體現孔子志道樂業精神的是這一句:“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贊揚了一個人堅持理想,恪守志向,不為邪惡名利動搖的高風亮節。孔子本人就是一個樂道敬業的典范。
奉著高度的樂道精神和對學生負責的態度,孔子要求教師以“不倦”的精神“誨人”――教育學生。他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他的學生子貢對他的這種負責精神贊揚不已,慨然道:“教不倦,仁也!”孔子的這種以“仁愛”為實施基礎,以學生為出發點的“不倦”的“誨人”精神主要表現在熱愛學生上。
首先,孔子對“自行束以上者,皆能誨之”。并通過“聽其言,觀其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廣泛地了解學生的個性、特長、志向、品行和知識水平等情況,對每個學生了如指掌。如他說:“師也過,商也不及”,“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唁”等等。由于對學生的情況了解得全面,因此孔子在教學中能針對不同的學生,做到對癥下藥,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學、思”,“學、習”,“學、行”的結合,提高他們的知識,培養他們的能力;啟發誘導學生的求知欲,做到“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同時孔子針對學生不同的個性和愛好,進行分析教學,并就同一問題針對不同學生作不同的回答,鼓勵學生多問、敢問,養成多問的學習習慣。
其次,孔子的“誨人”還表現在“無隱”上。孔子將自己所知、所學毫不保留地傳授給學生。“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這段表白,充分體現了一個師者應具備的風范。《論語》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載:陳亢問于伯魚:“子亦有異問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其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趨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趨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由此可見,孔子確實是本著愛人之心育人的,對學生“無隱”,對其獨子孔鯉也無“異聞”,視其子與其他弟子同。當然,“無隱”并非只將自己所知所學平等地傳授給每個學生,應“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在傳授知識時,應有所選擇和鑒別。以“立己”之道“立人”,“達己”之道“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孔子“無隱”思想的基礎,也是“不倦”、“誨人”的突出表現。
再者,孔子教導學生要有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并富于挑戰精神,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認為“人皆有過”,只要“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若“過而不改,是為過也”,學生應當如此,為師者更應注意,以此作為基礎,學習要擇善而從,不善而改4,要有分析,有鑒別地學習別人的長處或優點,汲取別人的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對為師者不應一味篤奉,惟命是從。要“當仁,不讓于師”,面對真理,要敢于懷疑一切,富于挑戰精神。
最后,孔子也強調教師要注意加強自身內在的道德修養和情操,教育學生要“直”面人生。從孔子為政的思想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反對體罰學生的,主張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避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等等。
樂道敬業,誨人不倦,是孔子師德觀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是為師者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的歸宿。這是孔子師德觀念的精髓所在。
2.學而不厭,教學相長
學,在孔子看來,不僅僅是學生的事,也是教師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他反對為師者不學無術,胸無點墨。主張為師者應“敏而好學”,以防“六蔽”。因此孔子在各種場合都十分強調“學”的重要性。另外還要求教師通過“不厭”的學,才能“博學多能”,而不能像器皿那樣,只有一種用途或只被當作擺設,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孔子認為,“學而不厭,博學多能”是為師者應具備的重要條件,是“誨人不倦”的力量源泉,是教書育人的先覺因素。孔子畢生勤學不輟,“誨人不倦”,堪稱“師表”。他說:“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益。不如學也”。正是由于認識到了“學”對“修己”和“誨人”雙方面的重要性,孔子自十五歲就“志于學”,他自認為“非生而知之者”,因此“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入大廟,每事問”,通過“時習”、“自省”、“無常師”、“不恥下問”等途徑不懈學習。即使到了晚年也不放過學習的機會。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孔子對自己不輟致學精神的高度概括的表白。孔子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教育學生的。他還要求“學”要持之以恒且有進取精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他慨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因此學要積極進取。他對弟子顏淵的進取精神贊譽不已,說:“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他深刻地認識到,要想“善其事”,“致其道”,只有學才能“利其器”,因此他時刻警惕“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致其道”,“善其事”是孔子“學而不厭”的根本動機。
在長期的教學過程中,孔子意識到“學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因此他主張教師向學生學習,接受來自學生的啟發,提出了原始的教學相長思想。他說的“起予者,商也”,“回也,非助我也”,“當仁,不讓于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肯定“后生可畏”,都是這一思想的具體表達。
3.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孔子在講“學”“思”的同時,亦十分注重“行”,即要求教師要以自己的行動感化學生,也就是孔子提倡的身教原則。在《論語》中,這方面的言論大多數是針對從政者講的,但其精神則更須從教者領會和貫徹。孔子的身教原則,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認識。
3.1 以“行”立人。孔子認為,不論是為學者還是從教者,其行為的表率作用至關重要。他說:“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要求教師應以行立之以榜樣,樹之以表率。告誡學生從師當“聽其言,觀其行”,“恥其言,過其行”,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在孔子的這種教育下,學生中形成一股“躬行君子”的風氣。
3.2 以德感人。要求教師通過對學生施行心理的影響,從而收到潛移默化的效果。他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一次,季康子告訴孔子國內盜匪橫行,他深以為憂。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多種場合,孔子都采取了“欲無言”的態度。子貢不解就問:“子如不言?”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此,只要為師者“身正”,則又有“何言哉”,否則“則為之也難”。同時,孔子要求教師能“自訟”“內省”“躬自厚而薄責人”,凡事多從自身找原因,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多做自我批評,應“求諸己,不求諸人。”
3.3 以形塑人。要求教師應注意自身的外表儀態,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必過分講求“猛”,這樣也可以達到“正人”、“安人”的目的。
孔子的身教原則要求教師的內在情感與外在儀態應是統一的,二者不可偏廢。“繪事后素”,“文質彬彬”就是這個意思,只要教師“逮之躬”,“躬于行”,“道之以德”,塑之以形,則學生亦“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勵”,照樣可以使“其事善”。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身教的目的,才真正能稱其為師表,真正發揮教師的表率作用。
4.群而不黨,周而不比
孔子刪詩說范文第5篇
儒家經書,最初只有“六經”,也叫“六藝”。到后來,《樂》亡佚了,只剩下“五經”。《樂經》可能是曲調曲譜,或者依附“詩”,因為古人唱詩,一定有音樂配合。無論“禮樂”的“樂”,或者“詩樂”的“樂”,到了戰國,都屬于“古樂”一類,已經不時興了。《孟子?梁惠王下》載有齊宣王的話,說:“我并不是愛好古代音樂,只是愛好一般流行樂曲罷了。”春秋末期,諸侯國的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訪問,已經不用“詩”來表達情意或使命。戰國時期,若引用詩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書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時代用“詩”來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詩”的樂曲樂譜自然可能廢棄不用。而且根據目前已知的戰國文獻,西周以至春秋那種繁文縟節的“禮”也長時期不用,依附于“禮”的“樂”也可能失掉用場。“樂”的亡佚,或許是時代潮流的自然淘汰。《樂經》的失傳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漢書?藝文志》沒有《樂經》。至于東漢末年曹操從荊州得到雅樂郎杜夔,他還能記出《詩經》中四篇樂譜,而杜夔所記出的《詩》的四篇樂譜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樂譜。
“六經”的次序,據《莊子?天運》和《天下》、《徐無鬼》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淮南子?秦族訓》、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禮記?經解篇》、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都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唯《荀子》和《商君書》沒談到《易》)。但到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六經的次序改為《易》、《書》、《詩》、《禮》、《樂》、《春秋》。以后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以至現在的《十三經》都把《易》改在第一。為什么到后漢時把“經書”的次序移動了呢?很可能他們認為“經書”的編著年代有早有晚,應該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據說開始于伏羲畫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書》中有《堯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詩》有《商頌》,或許是殷商的作品罷,列在第三。《禮》和《樂》相傳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為魯史詩經過孔子刪定,列在第六。
無論《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好,《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好,統稱為“六經”,《樂經》亡失,變為“五經”。《后漢書?趙典傳》和《三國志?蜀志?秦宓傳》都有“七經”之名,卻未舉“七經”是哪幾種,后人卻有3種不同說法:1.“六經”加《論語》;2.東漢為《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3.“五經”加《周禮》、《儀禮》。這3種說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種說法正確。唐朝有“九經”之名,但也有不同說法:1.《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2.《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b梁傳》。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唐太和(唐文宗年號,公元827―835年)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轂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宋代,理學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和《論語》、《孟子》相配,稱為《四書》,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進入“經”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經”。這便是《十三經》成立的大致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