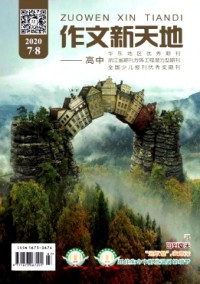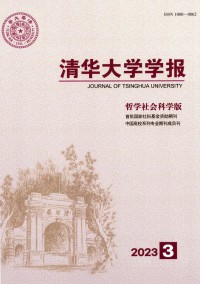韓愈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韓愈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韓愈范文第1篇
唐憲宗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導下國內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規模的迎佛骨活動,修路蓋廟,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勞民傷財,一場鬧劇。韓愈對這件事有看法,用奏折一遞,就惹來了大禍。于是,憲宗大喝一聲把他趕出了京城,貶到八千里外的海邊潮州去當地方小官。
韓愈這一貶,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趕出長安,年僅12歲的小女兒也慘死在驛道旁。韓愈自己覺得活得實在沒有什么意思了。他在過藍關時寫了那首著名的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是給前來看他的侄兒寫的,其心境之冷可見一斑。但是,當他到了潮州后,發現當地的情況比他的心境還要壞。就氣候與水土而言,這里條件不壞,但由于地處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習極多極重,農耕方式原始,鄉村學校不興。當時北方早已告別了奴隸制,唐律明確規定不準沒良為奴,這里卻還在買賣人口,有錢人養奴成風。其習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藥,殺雞殺狗,求神顯靈,人們長年在渾渾噩噩中生活。
見此情景,韓愈大吃一驚,比之于北方的先進文明,這里簡直就是茹毛飲血,同為大唐圣土,同為大唐子民,何忍遺此一隅,視而不救呢?按照當時的規矩,貶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實實磨時間,等機會便是,決不會主動參政。但韓愈還是忍不住,他覺得自己的知識、能力還能為地方百姓做點事,覺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這點冤、這點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連續干了四件事。一是驅除鱷魚。當時鱷魚為害甚烈,當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韓愈“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興修水利,推廣北方先進耕作技術。三是贖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錢抵債,錢債相抵就給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錢贖,以后不得蓄奴。四是興辦教育,請先生,建學校,甚至還“以正音為潮人語”,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推廣普通話。不可想象,從他貶潮州到再離潮而貶袁州,八個月就干了這四件事。我們且不說這事的大小,只說他那片誠心。
當我手扶韓祠石欄時,我就想,憲宗佞佛,滿朝文武,只有韓愈敢出來說話,如果有人在韓愈之前上書直諫呢?如果在韓愈被貶時有人出來為之抗爭呢?歷史會怎樣改寫?還有,在韓愈到來之前,潮州買賣人口、教育荒廢等四個問題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馬燈似的換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職超過八個月的也大有人在,為什么沒有誰去解決呢?如果有人在韓愈之前解決了這些問題,歷史又將怎樣改寫?但是沒有,什么都沒有。長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鉤曉月下靜靜地等待,秦嶺驛道上的風雪、南海叢林中的霧瘴在悄悄地徘徊。歷史終于等來了一個衰朽的書生,他長須弓背,雙手托著一封奏折,一步一顫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單人瘦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李淵父子雖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沒有聽說哪山哪河易姓為李,倒是韓愈一個罪臣,在海邊的一塊蠻夷之地施政八月,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歷朝歷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廟建祠,但哪一塊碑哪一座廟能大過高山,永如江河呢?這是人民對辦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紀念。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當他與百姓利益、與社會進步連在一起時就價值無窮,就被社會所承認。我遍讀祠內憑吊之作,詩、詞、文、聯,上自唐宋,下迄當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約不下百十來件。1300多年了,各種人物在這里將韓公不知讀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漸漸泛起這樣的四句詩:
韓愈范文第2篇
【關鍵詞】韓愈人道人性人倫
中唐時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藩鎮割據,權臣傾軋之狀況有增無減.安史之亂以后帶來的影響沉重,生產力破壞,物質缺乏,物價飛漲.朝廷昏庸,宦官專權,社會政治腐敗.改革變新難以進行.另一方面,佛教道教勢力日益蔓延,尤其信佛佞僧風氣猶為奇重.韓愈一生經歷了安史之亂后中唐五朝皇帝,這一時期的背景和韓愈自己的人生經歷感覺到要結合現實社會,真正求圣人之志為己任,“冀行道以拯生靈”關心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用“先王之道”來拯救當時混亂的政治和頹廢的民風.韓愈認為必須要重新振興儒學,強化儒學的正統地位,拒斥魏晉以來流傳于廣的佛道思潮,必須給人道仁義“定名”賦予儒家圣教內容,韓愈首創“道統”學說,倡導古文運動。而這一切他是為了解決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從思想上鞏固中央集權制度,保證全國范圍內實現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避免政治政局的動蕩。韓愈敏銳的察覺到佛道的思想有著不事君父、不擔賦稅給社會帶來了經濟損失和離心傾向的消極面,而這些消極面在藩鎮割據和動亂中已經充分暴露。韓愈認為應該要大大調整儒釋道三者關系,必須大大提高儒學的正統地位。
韓愈在人道仁義方面,認為儒家道德乃是以仁義為具體內容,著重以仁義規定道德,以仁義充實道德,注重“定名”。他明確了儒家道德的涵義和重要標志,并把道德賦予了儒家社會規范的性質,以用來拯救頹廢的民風,恢復社會“仁義禮智信”的儒家信仰。
在人性方面,韓愈提出了“性情之品有三”的學說,從人性分析出發,通過分析人性,來解決對人民教化問題,從人性上尋找拯救社會的本質依據。以因此來反對佛道二教的性情之論,弘揚儒家行為規范。
在人倫社會方面,韓愈最關心的如何改變社會的現狀,解決佛道二教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現實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問題。他認為首先要正位綱紀,整合社會。他在批判佛教的清靜寂滅的同時也構造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模式。在這社會模式注重“正位”,從人生人文人倫等方面賦予儒家憧憬“大同小康”的模式。
韓愈的人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儒家人學思想的延續、繼承和拓展,也是針對當時儒釋道的爭斗和社會危機所提出的社會思想。他的人道仁義思想還是人性理論的提出,都是力圖解決社會當時的危機和政治昏朽,試圖維護自己所處的朝代的政治制度的集權和復興儒學思想中社會規范。可以說在他的人學思想也是繼承了儒家文化的內涵:以倫理價值為中心、以社會國家為本位、以義務至上為準則、以民本主義為依據、以完美人格為理想以及以世界大同為歸宿。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人學思想呈現出三重性,表現出對人道的追求、對人性的透析和對人倫的關注。
一、人道仁義的定名倡導先王之道
韓愈自述一生口不絕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絕.對儒學“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進學解》)。史家贊揚他“深深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撥衰反正”、“可謂學道君子也”。韓愈在茫茫迷霧的儒學里,所“旁搜”和“遠紹”的“墜緒”和所“推尋”、“深探”的“本元“正是中國傳統儒學的先王之道,就是孔孟的仁義道德的人道定名。[1]
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樣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等等[2],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則在人道中被賦予了充實的內容。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
這里韓愈給仁、義、道、德下了定義,仁義二者有其特定的內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義比較寬泛,哪一個學派都可以用,對“仁”韓愈用“博愛”釋之(與孔子“仁者愛人”相通),意即對人充滿關懷和熱愛,始于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進而推及于任何人“泛愛眾”;這種“博愛”的心情必須通過行為表現出來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如得體適宜,即是“義”(與孔子“克己復禮”相通)。所以仁、義二者,一表現為內心修養,一表現為行動。按照仁義的標準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幫助和安慰,切實具備仁義,達到自得自樂的地步,即是“德”。韓愈在這里是用“仁義”來限制“道德”,用“仁義”來充實“道德”。[3]“道德”是以仁義為具體內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能夠達于四海,通于萬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體現“仁義”原則的是“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的“圣人”。韓愈弘揚仁義,給仁義道德寓于“定名”作為儒家總綱,其理論完整表現在韓愈以《大學》為綱領的儒學思想體系中,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原則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系在一起,用“將以有為也”的仁義道德,貫通內外兩個方面,融二者于一體。
韓愈對歷史上儒學受到多次挫折表現了極度的感慨。為了倡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給仁義道德寓于“定名”。他創造了對后世儒學發展頗有影響的“道統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以此“道統”為理論依據,力圖恢復儒學在社會中的正統地位,同時以“道統”為人道價值標準,定名仁義道德,倡導先王之道,以存于內的“仁”到見于行的“義“來核實人道之本。
二、人性的三品規范善惡標準
韓愈十分注重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系問題,分析如何依靠倫理道德力量協調人際關系。他認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解決途徑不在于外在的禮法綱常,而是靠內在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心。那么,人的內心是否能夠具有約束自己行為的素質和能力以及人的本性如何,對此,韓愈主要針對佛教的人性論,提出了“性之三品,情之三品”的學說,用之衡量人心善惡標準,推進儒學仁義道德教化之過程。
韓愈認為人有性有情。“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他認為性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種倫理道德。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個品級。他認為五種倫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這樣,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時,他把情也分成三個品級,而高下取決于每個人對自己的情感表現不同。韓愈之所以認為如此,主要他認為情由性生決定,人的情感意志與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倫理,但又因為情感的表現和人的稟賦能力的不同,而分為上中下。那么在現實社會倫理關系中通過情的“動而處其中”,來體現人的道德本性,人們的社會行為只有以儒家的社會規范作為標準,才能近善而遠惡。
韓愈的“性情三品”之論是為了反對佛道二教的人性思想所發的,由于佛教主張無為、出世,宣傳滅情,忽視社會規范和生活倫理。韓愈主張人不僅有“仁義”的本性,而且還有,和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情之三品是性之三品的表現,性之三品是情之三品的發動。一方面人性有仁義道德的本性,有被教化向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的發動不同,導致人性的高下,有教化的必要性。“性情三品”之論是為了規范善惡標準,以為儒家先王之道的弘揚在人性上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人倫社會的正位宣揚理想樂園
韓愈一生弘揚儒學,倡導先王之道,他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佛教和道教盛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現實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問題.在他看來,當時社會佛道二教的盛行給社會生產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佛教思想對于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沖擊和破壞深為嚴重,以及由此造成了人們行為方式的變亂,導致社會”傷風敗俗”,”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人際關系錯綜,人與人之間充滿虛偽、欺騙和卑鄙,人情疏薄,人際不和諧。韓愈對此情形,他力圖抑邪興正,辨時俗之惑,正位人倫,弘揚儒學之社會倫理。他認為,整合社會的關鍵所在,是社會人倫正位之問題,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孔孟之道立綱紀,正名分,盡本分。
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他認為首先要明確君臣父子社會之名分,理清君民關系。君臣民各守職責“在其位,謀其政”。把儒學的仁義之道,向下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注重分清群體社會中的各自地位和具體責任[4]。“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在正位人倫的同時,韓愈進而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樂園:“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韓愈用先王之道的仁義道德來規范人們倫理生活,在這個理想社會中,名分綱紀正位,仁義道德定名,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們生活無憂,人人都有仁義道德之心,都自覺恪守個中社會規范,“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使自己的欲望、理想得到滿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人際關系和諧,人情通達;“以之為天下國家”,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整個社會生活秩序“無所處而不當”,呈現和諧安定的局面。
在韓愈的思想中,唯有弘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先王之道,才能向內里通自身生命,“修身正心誠意”,完善人格修養,達到“體安而氣平”;向外則通天下國家,“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于小康,融天下國家于大同,“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外在的社會政治和內在的自身生命共融于仁義道德之中,彼此融通,彼此通達,彼此成就,達到“成己成物”的“合內外之道”,從而達到“萬物得其宜”的理想境界。
四、人道、人性、人倫的統一及其意義
韓愈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一直致志于弘揚儒學,以復興儒學為己任,隨時隨地倡導先王之道,攘斥佛道,捍衛中國文化正統。面對當時社會動蕩,人心虛偽,道德淪喪之局面,其人生經歷也多為坎坷。但韓愈卻始終具有“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的積極心態,有著關注人世、關切人生、關懷人事的胸懷。在其思想中,對人生、人倫、人道、人文等探索極其豐富。
韓愈在人道上是極度弘揚孔孟之道,發揚儒家仁義道德,想以儒家文化來拯救當時“不父其父、不君其君”倫理盡失的局面,把仁義道德落實到政治倫理日用生活之中;同時,他闡發傳統的儒家的先王之道,用仁義來充實道德,推崇《大學》為綱領的理論體系,將“治心”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外貫通,為了能夠“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于天下,使仁義道德于眾人,他又在人性思想上,提出“性之三品,情之三品”之說,為貫通仁義之道提供內在根據,一方面承認人性的道德本性,認為,任何人都是具有道德理性,它是“與生俱生”的;另一方面又承認在具體的生活中,人實現人性的稟賦能力和達到的境界是有差別的。這樣,既指出依照儒家仁義道德標準來完善人性的可能性;同時又提供按照儒家先王之道原則對人民進行教化的內在必要性。而先王之人道,性情之三品之人性都是最終回歸于人倫社會之中。
在韓愈看來,社會乃至整個宇宙本來是為“和諧”,人與人之間也是“和”的關系,社會規范的調整應該以儒家先王之道進行建構,對人民的教化應以仁義道德給予推行,社會名分得以確立,日常倫理得以正名,人道之仁義道德于內外貫通,人性去惡存善、改惡為善,人倫之社會和諧安定,三者統一以“無所而不當“。
【參考文獻】
1《中國儒學史》:趙吉惠趙馥潔/等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國儒學史·隋唐卷》:許凌云/著,廣東教育出版社
3《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冊):王處輝/著,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中國人學思想史》:李中華/主編,北京出版社
5《新編中國哲學史》(中冊):馮友蘭/著,人民出版社
6《韓愈〈原道〉之解讀》:蘇文帥/撰,載于《孔子》(2000)
【注釋】
[1]趙吉惠趙馥潔:《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第476頁
[2]李中華:《中國人學思想史》北京出版社第353頁
韓愈范文第3篇
關鍵詞:韓愈;道統;道統論;儒學復興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
一、韓愈的道統論的基本內涵
韓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區別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統對抗佛家法統,建構了道統論。因而,我們可以從“道”與“統”兩方面理解道統。“道”主要是理論與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與普遍性的特征;“統”主要是歷史因素,具有時間性與連續性的特征。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蔫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①“道”也稱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來,“道”首先是作為儒家思想本質和理論硬核的仁義道德,其實質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即以仁義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體知識特別是異端思想,處于優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根據與本源。“道”不僅是以仁義為核心的精神價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會階層與分工、倫理秩序、社會風俗,“這實際是韓愈所了解的整個儒家文化——社會秩序”。就經驗層面而言,道體現于社會各個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就超驗層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貫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傳承有一歷史過程,這便是統。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蔫。”②圣與道合一,所謂的道統就是儒家思想的歷史傳承譜系。韓愈的道統說據陳寅恪先生講,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啟發,二是由禪宗祖統說摹襲得來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單純確立一種人物的外在譜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內在傳承,通過道統的構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連續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從而能夠凌駕一切異端思想,成為絕對真理與唯一權威而重現占據思想文化領域的主流,最終實現儒學的復興。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解讀韓愈的道統論。
首先,我們看韓愈的儒家文化立場。韓愈辨名析理著力闡述孔孟之道體現著他理智上對于儒家思想及精神價值的理解,他虛構歷史,以圣人史觀盛贊先王之教,體現著他情感上對古圣先賢的景仰,合而論之即是對儒家文化認同與堅守。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的長期壓力與道教的興盛,加上儒學的長期衰落,士人階層與普通民眾發生了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以至于出現這種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后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③對文化思想界的這種混亂狀況,韓愈挺身而出撥亂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確規定其內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學,堅定了儒學文化立場,明確了士人階層與普通階層的文化歸屬。
其次,我們看韓愈的正統觀念。正統觀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內部存在多個學派時,某些儒者特別是具有道統觀念者認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傳,視自己為儒門正統,而把其他學派視為旁門乃至異端。因而道統首先意味著對儒學本質的理解和對其內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學內部起著劃分學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說道統保證了儒學學脈的“純正”與一以貫之。正統觀念是儒家文化立場的內在要求與進一步延伸。荀子與楊雄“擇蔫而不精,語蔫而不詳” ,既沒有正確把握孔孟之道的實質,也沒有充分闡釋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統。韓愈自命:“天下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再者,我們看韓愈的衛道精神。反擊佛老與捍衛、弘揚孔孟之道是一事的兩面,但后者更為根本。韓愈在《原道》中歷數佛老對政治經濟造成的嚴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臨嚴重威脅——“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③的激進措施,期望通過這些措施打擊并禁絕佛老的異端思想。韓愈一生以積極排佛而著稱,為此差點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使其道由愈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限”④,是儒家真正的衛道勇士。
最后,我們看韓愈的弘道精神。衛道精神與弘道精神相輔相存,同構成儒者的現實生命。韓愈具有強烈的擔當意識,以傳承道統弘揚儒學為自己義不容辭的文化使命與歷史責任,為此不遺余力、不惜代價。孔子說:“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說,拒行,放詞” ⑤,積極弘揚先王之道極有功于圣門。在佛老盛行,儒學衰微之際,韓愈積極弘揚孔孟之道,是對傳統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繼承與努力實踐。
道統的四個方面緊密相連,相互融通。韓愈的道統論通過這四個方面完成了對儒家仁義道德的形而上學論證,使道最終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價值,道統傳承譜系為儒學的重建與復興提供了重要內容。
二、道統論的歷史依據與理論根據
農耕時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國古代一直重視歷史,同時,中國古典哲學又具有解釋學的傳統,新思想往往借助詮釋傳統而開出。想要重新確立思想的地位和權威一般而言必須從歷史深處尋求歷史淵源的支持和經典文本特別是儒學經典的依據,否則,其合理性與合法性將會面臨巨大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⑥。道統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根據即來源于對歷史的重構與對儒家經典與精神重新詮釋。
韓愈說:“轉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現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⑦一方面他將儒家之道的修心詮釋為有為以駁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記社會責任的空寂無為思想,在注重實用理性、強調經世觀念的古代中國很容易得到認可與支持;重要要的是從中所挖掘出來的歷史資源提供了一個溝通內在心靈培養與外在國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內的思維路徑被整個變成由內而外的理性自覺,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據由“宇宙天地”轉向“心靈性情” 。這種轉向意味著中國哲學開始由宇宙論轉向形上學、心性論,正是這種轉向,修心與治世溝通了,內圣與外王統一起來。同樣,韓愈對孟子的推崇也與此相關。從學理上看孟子主張向內反求諸己,由內在心性培養外在政治推衍④,這與《大學》運思途徑一致,可以為道統論提供理論依據。同時,孟子在《盡心下》中的類似的道統觀念啟發了韓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統論的歷史淵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義”,與韓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實質相同。孟子積極拒斥異端與韓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韓愈看來,只有孟子真正繼承了孔子“仁”的思想與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傳、儒門正宗。通過排列古圣先賢譜系,將孟子列入道統,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傳蔫”便將歷史接續到當下,確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為在古代中國,一種新思想必須同時具有古老經典的依據與思想歷史的傳承譜系 ,超時空的道必須在時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獲得普遍認同。
三、道統論與儒學復興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道教一直處于興盛狀態,而長期處于意識形態主流的儒學卻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際的儒學衰落遠勝于魏晉之際,儒學危機是不爭的事實。儒學復興運動作為危機的產物是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發展總的趨勢,而新儒學是其最重要結果。韓愈作為先驅人物以道統論掀開了儒學復興運動的序幕。
儒學復興首先要與佛老異端思想劃分界限,明確并強化儒家文化認同,道統論發揮了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發展有其內在與外在的邏輯與時代課題,新儒學作為復興運動的產物,其形態和特質是思想的內部淵源與外部挑戰的相應性②。韓愈在積極應對異端挑戰時既努力挖掘歷史資源又盡量吸收當下的東西,在道統構建上他沿襲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與策略。在大漢族中心主義影響下,尊王攘夷的觀念在士人階層與普通民眾心理中根深蒂固,華夷之辯是士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再加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異族對于中原長期統治與殘酷蹂躪,特別是安史之亂距韓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歷史記憶在大眾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亂后,由于安史為西胡雜種,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間抬頭”③,此時,韓愈將佛老思想斥為狄夷之法,反對“狄夷之法加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與大眾心理上獲得普遍認同與廣泛支持。
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道統論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儒學思想,另一方面作為儒家復興先驅之作,道統論直接開啟了宋明理學。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前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⑤總體而言,韓愈以仁義為核心,比較正確地理解并繼承了儒學的核心思想與精神實質。他通過《原道》等著作從世界觀、人性論、倫理學、歷史觀等對儒學理論的多方面探究構成他繼承并復興儒學的重要內容,而最顯著的便是道統論。他立道統排佛老興儒學,為儒學復興樹立起了鮮明的標志,并結合孔孟的仁義與《大學》的修齊治平的思想予以論證,尤其是對《大學》的重視,對后來宋明新儒學的意義十分重大。今天,現代新儒學依然在試圖重建道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論是韓愈所處的時代還是宋明之時,乃至今天,一個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學復興,而道統論是儒學復興的一面大旗幟⑥。
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了韓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統證明傳統之淵源”、“直指人倫章句之繁瑣”、“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功效”、“獎掖后進期望學說之流傳” 六個方面。陳先生這種儒學本位主義的評價曾受到過嚴厲批判,但是如果我們認同自身的傳統,以理智的心態面對歷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對韓愈及其道統論,那么我們會承認,韓愈建立儒家道統勇敢地捍衛儒學、積極地弘揚儒學,在民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統與發揚上厥功至偉,宋明時期儒學的復興是其直接的明證。
韓愈已經遠去一千多年,那個時代的一切成為一種歷史的沉積與記憶。我們發現,韓愈所為也是那一個時代士人共同的行為選擇與價值趨向,道
韓愈范文第4篇
1、這是一首寫晚春景物的詩。
2、第一句賞析:用擬人的手法描述花朵像是知道春天不久就要歸去,于是尤為珍惜這美好的時光,便各逞姿色,爭芳斗艷,盡情舒展生命的機能。
3、第二句賞析:用擬人化的手法描繪了晚春的繁麗景色,描述全無才思的楊花榆莢,在春風中紛紛飄落,只曉得如雪花那樣,毫無目的地漫天飛舞。,同時還寄寓著人們應該乘時而進,抓緊時機去創造有價值的東西這一層意思。
(來源:文章屋網 )
韓愈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白居易; 韓愈; 詩風; 影響
中圖分類號: T2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2)(11-12)-0066-01
中唐以來,世風與文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人的精神風貌、為人處世和道德操守的都有變化。總的來說,更加貼近現實,更加不避俚俗,其表達方式也更加坦率直露。白居易、韓愈,他們的志向和理想的實現途徑,己經不是像盛唐文人那樣,或佯狂傲世,或走終南捷徑,以高人仙客的面目聞名于世,而是有一個實際的操作程序(連應試時的干謁、請托,及第后的入幕等都是如此)。但宦途坎坷,世風險惡,正是在現實生活的磨礪中,在社會角色的轉換中,他們的思想和創作逐步成熟起來。淺俗文風流行于文壇,成為主流。白居易的通俗、韓愈的奇崛,都從不同的側面體現了這種文風的變化。無論如何,這種風格都與盛唐的典雅、中正大相徑庭了。如韓愈以四言體寫的《元和圣德詩》,為達到所謂“警動百姓耳目”的目的,刻意追求一種逼真的警示效果,和雅詩的一般作法和風格形成鮮明的對照。韓愈古文寫作的目的,與白居易諷喻詩的創作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清除實用文體或公文體的不良影響,把脫離現實生活和日常語言的詩賦文章等扭轉到貼近生活、反映世道人心,體現普通人思想、感情和欲望的道路上去。中唐文人的個性往往十分突出,導致了文學創作的個性化發展。
韓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壇兩大宗主,其創作、開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觀念的影響。總的說來,韓愈是較為純粹的儒家,從內到外,一生未變;而白居易則是以儒家思想為補用,以老子思想來謀身,以莊禪思想來娛心。韓愈的政治觀全部出自儒家,白居易除了儒家之外,還有老子和法家思想。韓愈有意識以醇儒自任,以承繼儒家道統自居,重在理論建設;而白居易則是從現實出發,重在解決眼前問題。理論可以是純粹的,而現實則是復雜的。中唐以來,戰亂不已,民生多艱,需要大一統,也需要與民休息。韓愈看重前者,白居易二者兼顧,因此白居易政洽觀中有老子思想又是很正常的。這就是白居易詩中多反映民生疾苦之作而韓愈卻極少見的原因。在看待生的意義上,韓、白二人則呈現明顯的差異性:韓愈想做圣人,是個斗士;白居易只想做個凡人,是個閑士。但較韓孟詩派的創作方法上來看,是對儒家傳統文學價值觀的改變,聯系韓孟詩派的創作傾向看,其實質更在于對被正統詩論斥為“變風變雅”的《楚辭》“發憤以抒情”思想與實踐的繼承與光大。他們以大量詩作抒寫激憤不平心態,形成追求奇崛險怪的傾向,顯然與作為儒家詩教重要內容的“發乎情,止乎禮義”、“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原則及“溫柔敦厚”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以其與《楚辭》抒憤特質的一致構成背離儒家詩教傳統的重情詩學精神的一脈延伸。
對于韓愈的奇崛詩風,古人早有形象的概括。唐人司空圖曰:“韓吏部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扶于無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麗徇其呼吸也。”韓詩奇崛的特征,常常通過超凡的意境、以文為詩的手法以及去熟生新的語言體現出來。
首先,在意境創造上,韓詩往往以雄健之筆、凌厲之氣、神異之想,寫奇壯景、狀奇怪物、抒奇特情。比如著名大篇《南山詩》,極力摹寫層巒疊嶂的怪形異狀,四時變化的千姿百態,亦寫得南山靈異縹渺,光怪陸離。《答張徹》寫華山絕徑,懸崖奇險,更是“倚巖睨海浪,引袖拂西天。日駕此回轄,全神所司刑”,令人驚心動魄。韓詩意境奇崛并不單單表現為詩人善于把本來就奇險怪異的事物寫得活龍靈活現,出神人化,而且還表現為詩人特別善于把現實中不奇不異、平平常常的事物也寫得或雄壯宏闊,或瑰麗奇異。
其次,以文為詩手法帶來的韓詩奇崛表現在:一是詩中常有文的章法結構、賦的鋪排馳騁。如《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本為一首贈友之作,卻在結構上讓友人歌辭占了絕大篇幅。清人方東村《昭昧詹言》(卷十二)評曰:“中間以正意、苦語、重語作賓,避實法也。”就是說,欲述自己之意,偏借他人之口,正是古文“反客為主”之法。二是在詩句排列上執意像古文句子那樣尚單求散,力避律句、對句。比如強幼安《唐子西文錄》曾以韓愈五古《此日足可惜》的詩句為例說:“韓退之作古詩,有故意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三是個別篇章的文言虛宇,俯拾即是。總之,韓愈以文為詩,使其詩更加奇崛。
再次,在語言上,韓詩還務去陳熟,力出生新、或獨標異語,或故用狠語,或窮追律奇韻險,或極求詞晦字僻。為了去熟生新,他對古人成語絕少襲用,而是盡量化用,甚至反用。如《醉贈張秘書》詩,本用”鶴立雞群”語,偏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薦士》詩本用“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語,偏云“強箭射魯縞”等等,都既有來歷,又非蹈襲,可謂化腐朽為神奇。
奇崛是韓愈詩風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韓詩風格,除了多屬奇崛而外,還有不少清麗自然之作。而單就奇崛一類而言,其中雖常有險怪之作,或鬼趣兵象,或晦澀生僻,但它們畢竟不是多數,不占主流。韓愈最擅長的五古、七古,大多還都是奇崛中見豪健、見闊大、見雄直的,也是這些詩在矯正當時詩壇頹風中起了主要作用,并對后世產生了積極影響。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
蘇軾《祭柳子玉文》中稱:“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白居易寫了大量的反映日常生活的“閑適詩”來表現他的思想感情。詩人的創作活動除了達到政治功用的目的外,也同時完成了詩人的另一個人生追求,那就是能夠把自己擺在平凡人的地位上,盡可能地與世俗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接近。白居易的詩意緒淡泊、情調悠閑,語言淺切、平易。白居易所倡導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論詩則本于“六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一功利主義文學觀要求,詩歌要發揮其社會功能,產生廣泛的社會效果,就不能生澀隱奧,而要通俗易懂、明白曉暢;因此,白居易《新樂府序》說其詩“不為文而作”,采取最為簡潔曉暢的藝術形式:“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并且要求詩歌語言質樸明快、曉暢通俗,使讀者能夠容易了解、接受,因而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