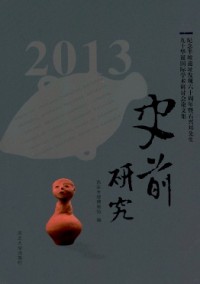后現代音樂教育學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后現代音樂教育學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后現代音樂教育學范文第1篇
所謂“后現代”就是對“現代化”進行反省的時代。從20世紀以來,由于新的藝術作品、樣式和風格的出現,從而對傳統的“藝術”的定義進行重新審視。對于“什么是藝術”,“藝術與非藝術的分界線在哪”,“誰有權賦予一件事物以‘藝術’之名”等等問題的爭論,似乎找不到科學的答案。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一個貌似科學的定義得出,藝術實踐界就能創作出超越或者說打破這個定義的“類藝術品”。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以及波普藝術等等這些自命為藝術的現代藝術是否能夠受到歷史的肯定,因時間未到也不可能有標準答案。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娛樂文化、通俗文化也逐漸成為藝術生活實踐的另類詮釋詞匯。藝術的理論研究似乎和實踐進入了一個迷宮,看不到藝術的本真面目。多元文化背景下,音樂形式的進程似乎由古典、浪漫與現代進入與文化同步的后現代。音樂的后現代審美也以多元的審美特征成為音樂文化的特殊構成。
一、關于音樂美學研究的后現代屬性
為了理解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我們不妨首先對于音樂美學的歷史藝術理論以及它在過去的兩百年內的發展情況作一番簡潔的回顧。眾所周知,美學產生于哲學,它涉及到對于“美”的判斷與品位的原理;但是在藝術史上的藝術評論則傾向于涉及美德范疇。19世紀以來圍繞美學的構成所引起的爭論:一方面是康德(1724―1804)以及他的后來繼承人諸如克萊夫,弗賴特等人所指出的美具有普遍性的“無私的”美學觀點,依據他們的看法,“美”不但具有宇宙性,而且不受時代偶然性的影響;而另外一方面,新型的美學理論家則認為“美”因受到時空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因此實際的時空環境是決定“美”概念變化的條件。席勒、康德等人將古典主義音樂美學推向,十分關注音樂性格、道德和數學形式等范疇,推崇在哲學體系內對音樂進行思考。霍夫曼( 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讓•保爾(Friedrich Richter Jean Paul 1763―1825)、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等人的浪漫主義音樂美學,他們的審美結論都是從音樂體會中來,源于“關照”而較少源于“概念”。漢斯立克試圖將音樂美學引向理性哲學的一路,他說:“有才能的作曲家,不管他更多地出于本能或者有意識地,對任何音樂要素的性質是具有實際的知識的。但科學地解釋各種音樂效果和印象時,卻需要有關這些性質的理論知識,從豐富復雜的組合到最后的可辨認的要素。” 要做到這點,必須“給音樂以哲理的基礎”。同“只有把音樂獨有的屬性歸納到一般美學范疇下,把這些一般的范疇又總結為一個最高的原則”,解釋各個和弦、節奏、音程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影響才有可能。①
20世紀的現代藝術,已經將“美”的概念重新定義,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則試圖描繪一個“消失”的智能預兆。他說“傳統的古典的藝術史”主要都把“個人”放在萬物的中心;而偏離這個中心的都是“他者”(others)和邊緣的。德里達認為,他的宇宙沒有固定的中心,也就沒有任何藝術家所處的中心地位;人人都是中心,人人也都是他者;歷史既然不再是大敘事,藝術史也就面臨死亡了。于是漢斯•貝爾丁發表了《藝術歷史的終結》(1984),福山雅治發表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個人類》等,都發展了德里達的理論。而這就是后現代主義的最為流行的歷史觀。現代主義的音樂家,是對自己的作品負責的,并是詮釋的權威,而且在音樂創作過程中,講究作品的原創性;音樂作品要具有傳統的美學的理想等。而后現代主義的藝術家,不會對于自己的作品進行詮釋,也不必爭當什么權威;創作時可以不拘形式規范;也不強調什么音樂作品的原創性;這樣藝術品可以涵蓋古典的神話、寓言、幻象、符號圖形以及所有的對于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等等的反應和批判等;這樣后現代主義就更具有自由性、隨意性、偶然性、調侃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等等。
后現代音樂教育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音樂藝術;身體認知理論;認識論哲學;音樂教育;后現代哲學;藝術教育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Music Education Back to Body
DONG Yu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身體”日益成為后現代哲學關注的重要視角,并進入了人文社科研究的話語領域。哲學的身心問題也是音樂及音樂教育的基礎性問題。對身心的不同態度,也影響著音樂及音樂教育的操作方式。我國現行的音樂教育教學范式是建立在西方認識論哲學身心二分基礎上的,音樂教育邁向系統化、規范化發展的同時也難以擺脫現代性固有的缺陷,凸顯出一系列問題。而后現代身體理論某種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界對自身學術傳統和日益膨脹的“現代性”深刻反思的成果。從而,也為我們對當前音樂教育教學范式的改進與超越,提供了新的思想參照。
一、后現代語境下的“身體”
后現代語境下的身體是一個有機整體。身體不僅是最原初意義上的物質性“肉體”存在,還包括豐富的心智結構、心靈活動和意義世界,是蘊含著豐富社會文化歷史內容的軀體。“對個人而言,它是身與心、感性與理性、意識與無意識的統一;對外界而言,它是與他者之身體相溝通、交流的支點,是主體間凝視與被凝視的相互接觸關系中的存在。”①因而,身體既是人進行自我認識的源頭,也是溝通人與社會、自然的支點和媒介。而思維作為一種生命功能,一開始便根植于身體場中,滲透于身體實踐的始終。我們正是通過整體性的身體走向世界、感知世界、體驗世界和創造世界。
后現代身體理論認為“身體在認知中的作用是不可還原或簡約的”。我們對周圍世界的感知和認識都是以自己的身體為中心的。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吃飯穿衣、讀書寫字、琴棋書畫等等都是身體思維的結果,并不存在非具身的知覺。感知就是與我們所處的世界以及所過的生活的一種生命聯系,而世界則把感知當做我們生活的熟悉場景呈現給我們。在此,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解還是通過身體完成的。為此福柯說,一個人只有通過親身體驗,才可能獲得全新的理論和認識。只有“用他的肉體、他的行為、他的感覺和熱情以及他的整個存在,才能制成一件藝術品。”②在這里,知覺的存在、身體的存在、以及經由身體所知覺到的對象和現象的存在幾乎是完全融為一體。因此,“認知實質上就是人的身體化的結果。大腦思維完全是一種整體性的身體活動,它就像能工巧匠的鬼斧神工一樣,完全是腦、眼、手、足及整個軀體的綜合性實踐。”③
由上可見,身體認知是一種與認識論哲學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認識論思維方式把“我思”確立為認識主體,外物被對象化成認識的客體。從而形成自我意識與外物間的主客二分,并在意識自身的封閉系統內,按照認知的邏輯實現二者的統一。這種認識論立場決定了人們對事物所采取的對象性的把握方式,由此決定人們對待外物的實用化和工具性態度。而身體認知思維的“知”是“體知”,即身體主體對其介入的世界所形成的具體處境的實際體驗,它既先于認知而存在,也是認知得以進行的前提,為認知活動提供了原始的情境。在此情境中,身體思維以體知為內容和活動為依據,超越了主客二分,實現了身體與外物同一,從而達到了物我交融、身心一元的思維狀態。哲學的身心問題也是音樂及音樂教育的基礎性問題。身心關系的不同態度也影響著音樂及音樂教育的方式。后現代的身體理論突破了西方認識論哲學身心二分的思維模式,這也為審視當前我國以認識論哲學為基礎的現代音樂教育范式提供了理論依據,為音樂教育研究的話語轉向提供了新的支撐點。
二、我國現代音樂教育范式中“身體”的缺席
自20世紀以來,我國音樂教育采用西方的音樂教育體系和模式,其發展是建立在西方認識論哲學基礎上的。西方傳統認識論哲學是以近代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哲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以此理論體系為基礎的音樂教育理論和實踐,有兩個基本的價值維度:技術和審美。與此相對應,作為西方工業文明音樂教育體系的移入,技術理性的音樂教育觀和審美音樂教育的哲學理念成為我國音樂教育現代范式的主要表征。在“揚心抑身”的哲學觀念統領下,現代音樂教育話語中是關于精神、靈魂、技術、知識的體系,而身體是缺席的。工具理性宰制下的現代音樂教育范式,邁向系統化、規范化發展的同時,也無法擺脫被異化的命運。
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理念,將音樂等同于音樂作品,認為靜態的音樂作品比真實的音樂過程更為重要。強調音樂的審美感知,對存在的音樂作品只能以審美的方式聆聽與欣賞,專注在像旋律、和聲、節奏等等這些為審美提供形式的音樂作品的元素和結構特征上。審美體驗的獲得源自聽者對音樂作品審美特征的完全關注,由此可以獲得超驗的、純粹的審美體驗,卻對音樂賴以產生的任何道德的、社會的、情感的、個人的等文化意義避而不談。此處隱含的假設是:“音樂作品即被認識的對象,是審美的客體,學習者則是擁有審美能力的認識主體。音樂作品與學習者的關系就是審美客體與審美主體的關系。”④由此可見,我國審美音樂教育的觀念沒有脫離西方認識論哲學二元分離的窠臼。并且受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影響,審美觀念下的音樂教學采用“刺激-反應”模式,這種模式把人的心里活動視為人腦對客體音樂的反射活動,音樂體驗只發生在個體頭腦的心理表征中。
音樂學習就是通過音樂的刺激引導學生對音樂諸要素做出反應,并培養以此為基礎的音樂表演、音樂審美等音樂行為能力。此種音樂教學模式讓人與音樂之間只是一種單純的聽賞關系,體現為人對音樂“物”的消費。當我們從主體反應或者從對蘊含意義的客體覺察的角度來理解和學習音樂時,也就是從沉默的聽眾而不是參與者的角度來理解學習過程的。作為音樂旁觀者的學習方式,獲得的音樂體驗只能是一種靜態化、平面化的意識體驗。于是,當“思”無“身”時,音樂就被界定為“聽覺藝術”,培養欣賞音樂的“優秀”的耳朵成為音樂教學的目標,主觀思考和想象構成了音樂體驗和理解的關鍵,而不是對現實世界中各種音樂過程的真實描述。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當前音樂教學過程中身體參與和體驗的缺乏,音樂學習與真實生活的隔離,也必然造成了在這種關系的學習中重結果輕過程、重現成輕生成的傾向,音樂教育忽略了音樂制作的本質及其重要性,無法向真正的音樂意義敞開。
技術理性的音樂教育觀念也與認知論哲學息息相關。我國的近現代音樂教育基本上是以西方音樂教育體系為模板的,而西方的音樂教育體系又是建立在“自然科學”(物理聲學概念)和“理性主義”基礎上的技術理性的教學體系,這也成為我國音樂教育的基礎。尤其是近代工業社會以來,隨著理性和知識在社會發展中價值的突顯,知識教育日益成為現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知識論的教育起點觀其實是理性主義的教育起點觀。理性主義的教育觀把理性視為人性的本質,求知則是人的理性能力表現。所以這種教育追求的是培養人的理性,知識的傳遞與獲得成為教育的唯一目標,教學就是一種認知活動。由此音樂教育也成為一種技術知識的教育。
音樂教學的認知模式也將音樂看做實體性存在,追求的僅僅是學習者音樂認知能力的提高。音樂教育的內容淪為單純對音樂本體知識的追求、工具性的識譜、讀譜、技能訓練注重的是音樂的邏輯結構的認知,強調“我思”而忽略“我能”,對身體的訓練不包括在內。音樂教學的認知模式呈現出目的-結果傾向,是一種以知識傳授為中心的單向的、機械的知識灌輸和規訓過程,音樂工藝層面的學習成為教學追求的最終目的而不是手段。片面強調“知”的精神的音樂教學導致了語言和邏輯成為音樂教學的唯一方式,而忽略了身體體悟對于音樂經驗的重要意義。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存在“棄我”、“忘我”的現象,本來能體驗并能制作的音樂,以人的生命及其文化為邏輯前提的音樂被分解為純粹知性探索的各種符號與知識,并與音樂理解相提并論。
音樂教育無視學生自身對音樂的行為、態度、意圖和感受的體驗,導致了知識與體驗的脫節,認知與情感的失調,忽略了對音樂知識背后生活經驗和意義的體認。然而,音樂教育的過程不同于獲知的過程,獲知的過程靠認識,是把握物性的過程,而音樂是有生命意味的形式,是一種參與其中才能生成的存在。
因此,音樂教育的過程靠理解,只有個體親歷其中才能真正的實現。而建立在認識論身心二元基礎上的理性認知模式,雖能讓學生一些掌握固化的音樂知識和技能,卻切斷了音樂活生生的體驗之流。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講,這樣的教育只關注人的技術的認知,而不關注人的旨趣。音樂淪為一門知識和技藝,喪失了把握人之整體生存狀態的功能和價值,音樂教育失去“育人”的真正意義。
三、回歸“身體”的音樂教育
“當‘思’無‘身’時,知識也就被從生活中剝離出來,失去了其鮮活性。”⑤這也是當前我國現代音樂教育范式異化的病灶所在。音樂教育“即心言心”的言說路徑導致了音樂教育靈魂與肉體的分裂,切斷了音樂與生命和生活的血肉關聯。而后現代語境下的身體認知讓“我思”沉浸到身體里,成為一種整體性和生成性的身體行為,也是一種主客未分狀態下人以其整體性把握世界的生命活動。真正能進入靈魂深處的知識,只有經過自身的身體體悟才能獲得,身體認知所要表達的正是實在與意義的統一體本身。因此,對于追求人文意義,促進生命發展的音樂教育來說,身體理應成為音樂教育的基本存在狀態。
音樂教育回歸身體,就是要回歸到以身體為核心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驗之中,在身體的參與中將音樂和人鮮活的生命融為一體,體驗物我交融的整體性音樂經驗,獲得真正的音樂理解。回歸身體的音樂教育讓身體成為音樂學習的出發點,甚至是音樂學習的發生地點,并參與到學習過程中的各個階段。“身體親歷學習不是傳統認知層面上的脫離實體的‘心理’的轉換與進步,而是生理與情感的雙重結合,是感覺意識與深入思考的雙重升華。”⑥身體在音樂教育中的回歸是從傳統認知方式的身心分離走向身心合一的狀態,強調在音樂語境中行動而不是思考。這種以學生對自己身體的直接操作為特征的認知方式在發展學生的認識能力和認識世界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就像邁特赫斯說的,“身體親歷學習是認知‘是什么’和‘做什么’之經驗或體驗的具體體現”。
對于這一點,東方音樂及音樂教育方式可以給我們重要的啟示。實際上,就心身一元的觀念而言,東方古老的身體觀念與西方后現代哲學的身體論在對待人與世界的認識態度上是相一致的。像中國、印度、非洲等東方傳統的身體觀中,身體是指一個心身融構的活絡整體,而不僅限于形軀之身。東方哲學的身心合一觀念形成了東方音樂觀念以及創作、傳承、教學方法的整體性。西方音樂觀念認為客體樂音與主體人心是分離,而“東方音樂始終是被看做人心之動而發出的聲音,音樂與生物體的感覺是一個整體,靈與肉是不可分割的。”⑦這種哲學思想反應在音樂的學習上,不同于西方音樂的技藝訓練。用約翰斯?蘇爾茲的話說,“是一種整體性及自生性音樂訓練的方式,即協調所有的心智和體力,以便使身體達到最佳狀態。”⑧
這種方式是以生命存在直接去感受客觀世界,強調了直覺的非理性主義傾向。由此決定了東方音樂表演與創作融為一體,音樂與語境不相分離的音樂“品味”體驗模式,與西方確定性的照譜演奏演唱傳統和強調音樂“分析”的體驗模式不同。東方音樂與詩性認知相聯,只有借助身體所有感官的參與,融入音樂的過程之中,才能獲得一種整體的音樂經驗,獲得真正的音樂理解。至今,像我國少數民族、印度、非洲等地方的音樂傳承中,融入身體感覺的音樂體驗和音樂傳承是必不可少的。
音樂學習是在群體的音樂活動中不斷對別人身體律動的看、聽、觀察、模仿和嘗試中完成的,而不是通過解釋和分解復雜的音樂概念和技巧的方式進行。想象力、直覺和意識在音樂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基于身體認知的感性、生活化的音樂活動和學習方式對當前音樂教育的啟示在于:音樂是學會的,而不是教會的。學習音樂的思維方式意味著學習如何去體驗感性思維。這需要依靠身體來反復體會在音樂關系中那種細微的“恰到好處”的感覺,而不是僅僅依靠書面知識的灌輸和理論化的思考。這種生態學的、生物學的方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音樂教學。今天,我們也看到在西方音樂教育中也在重新界定和操作“音樂”,如達爾克羅茲體態律動和奧爾夫教學法,都是通過身體的律動將音樂概念內化,促進身體本質的自發性表達。因而,將音樂回歸整個身體,也可以說是在回歸音樂的東方性以及轉向音樂的后現代性。
將音樂教育回歸身體,具體在音樂教學的操作中,應將學生的感官與身體意識充分調動起來,將教材從靜態呈現轉為動態表現,讓學生在親歷的身體體驗中獲得整體性的音樂理解。在身體參與的音樂學習中,“音樂作為可聽、可感可回味的藝術,它與精神和身體結合成一個永恒不可分割的整體。”⑨音樂不再是外在于個體自身的被認知的對象,而是在自己探索、體驗與感悟的過程中與身心完全融為一體。個體與音樂間形成了一種創造性的共生關系,音樂教材就變成了與學生交流和對話的“文本”,可以由學生解釋和發展,從而形構了一個部分對象與主體,但又完全屬于個人的活生生的音樂世界。在音樂教學中強調身體參與,實現了一種教學觀念的轉變:從過去強調對音樂知識技能的學習,轉向了注重人對自身的認識,對生活意義的探討。
因而,音樂教育回歸身體實際上是回歸對人的關懷,回歸音樂教育的文化承載。音樂學習的方式從認知轉變到了生存的方式,回歸了音樂教育的本真狀態。總之,對于身體價值的彰顯,會為改變我國音樂教育技術理性化的現狀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讓音樂教育回歸到一種生態化和人本化的狀態。
四、結語
正如梅洛?龐蒂所言,真正的哲學就是重新學會看世界。后現代哲學的身體轉向不僅改變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還為我們重新認識音樂及音樂教育開啟了新的視界。當前,我國音樂教育仍處于刺激-反應這樣的現代主義教育范式中,并且在這一“中心范式”的占領下,遮蔽了本土以及其他民族的音樂教育模式。
而從身體理論的角度審視當前音樂教育的基本原理,將會重新發現包括本土在內的東方傳統音樂教育體系的價值與意義。因而,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音樂并存與交流的時代,我們應該汲取東方以及后現代音樂及音樂教育的智慧,為重構本土音樂教育體系提供新的參照。(責任編輯:帥慧芳)
① 邱昆樹、閻亞軍《教育中的身體與身體教育》,《教育學術月刊》,2010年第11期。
② 張之滄《身體認知的結構與功能分析》,《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覃江梅《音樂教育哲學的審美范式與實踐范式》,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22頁。
⑤ 閆旭蕾《教育中的肉與靈――身體社會學視角》,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38頁。
⑥ 劉瀟陽《身體親歷學習初探》,《高等函授學報》,2010年第9期。
⑦ 管建華《后現代音樂教育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90頁。
后現代音樂教育學范文第3篇
一、音樂人類學為學科基礎的世界音樂教學
音樂人類學采用文化人類學的基本方法進行研究,如整體性觀點、實地研究、比較分析等,把音樂作為一種文化來理解是其主要理念,這種理念會幫助我們“從文化上去理解人類的各種音樂行為,并理解音樂在人類生活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民族、文化、藝術、宗教、技術、自然環境等方面的關系,因此,音樂人類學突破了西方傳統音樂學理論的局限,將音樂的理論意義擴展到廣闊的全球人類生活的視野中。”①在國際音樂教育的發展進程中,把音樂當作一種文化來傳授,而非“一種普遍的共同語言”明顯不同于以往的“音樂作為國際語言”的舊式哲學。Musics作為一種獨立含義的詞匯被使用且被國際音樂教育廣泛采用,同時也意味著音樂人類學多元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已被普遍接納。在音樂人類學理念的影響下,世界各國開始關注多元文化和世界音樂的教育,以期通過邊緣來理解中心的缺失。
綜觀世界音樂教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看到音樂人類學對世界音樂的滲透。1984年,美國音樂教育者協會、威斯廉大學和西奧多普雷斯基金會共同召開了音樂教學中應用社會人類學知識的討論會,此次會議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人類學家討論世界音樂在課堂中的應用,這是“美國教育協會組織的人類學家和音樂人類學家與利用他們學術成果的教師第一次面對面的交流”。②在威斯廉專題研討會的影響下,音樂教育對音樂人類學的“文化中的音樂”和“音樂作為文化”的觀念逐漸接受并認可。于是,世界音樂教育的發展有了音樂人類學家與音樂教育者的合作,如1990年的華盛頓的多元文化研討會上,音樂人類學家、音樂教育者和本土文化專家團結起來,為課堂中的多元文化教育出謀劃策。許多音樂人類學家都熱情地投入到探討世界音樂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中,如內特爾、布萊金、梅里亞姆等。音樂人類學對世界音樂教育的滲透大大拓展了音樂教育的研究范圍。
通覽《教學》一書我們不難發現該書主要以音樂人類學家提頓和斯洛賓的“一種認識音樂世界的音樂文化模式”為基礎進行構思和寫作的。③《教學》中關于每一個國家世界音樂教學主要包括音樂的觀念、音樂的社會組織、音樂的曲庫和樂器文化及教學設計,這種寫作有助于人們從文化整體上來認知音樂。譬如,在“印度傳統音樂文化的教學”一章中,作者通過對“音樂的信仰體系:在梵天的世界里、音樂的歷史:順著濕婆的頭發流淌、音樂的語境:履行自己的達摩、音樂的美學:永恒面頰上的一滴眼淚”的描述讓讀者深深體味到印度音樂的“梵我合一”的美學思想,以及印度音樂與宗教、人生、舞蹈等方面的緊密聯系。伊朗音樂文化教學的社會組織通過“音樂的聚會――場景與目的、部族生活中的音樂文化――融入土地的音符、舞蹈文化――手背上的律動”來說明,巴布亞新幾內亞音樂通過歌舞表演、喪歌、宗教儀式等社會組織形式表現出來。
上述這種對音樂的認知模式對于引導學生從文化整體上理解世界音樂具有重要意義,它消解了形式化的音樂本體教學所帶來的弊端,即“沒有把音樂理解為是人的生存活動世界的展開或生成,只將音樂本體視作客觀的、技術為本的‘自律’或以此為專業方向的學習過程,并以此構成了有一種絕對的或‘純音樂’或音樂本體加音樂審美形式等為核心的‘客觀的形而上學’標準,放棄了音樂存在于生活世界的文化意義的學習,形成了狹窄的音樂世界觀。”④
二、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為導向的世界音樂教學
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目前是國際音樂教育研究關注的焦點,埃里奧特在《音樂的問題: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中詳盡地闡釋了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的種種論點。埃里奧特認為音樂不僅僅是產品或客體的簡單集合。根本說來,音樂是人類所創造的事物,音樂至少應包含一個四維的概念――行為者、某種做事的方式、某種做成物、行為者所作所為的整個語境,即musicer、musicing、music、context。人類聆聽音樂也包含一個四維概念――聆聽(listening)、可聆聽的(listenable)、聆聽者(listener)、語境(context)。“以音樂作為一種人類行為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原理開始,我們已經得到音樂是一個多屬性的包含兩種有意為之的人類行為――做樂(廣義的音樂創作即做樂)和聆聽音樂的兩種模式的人類現象的更詳盡的觀點。這些行為不僅僅是有聯系的,它們也是相互定義和相互補充的。我們將這個由這種互鎖關系形成的人類行為叫做音樂實踐”。⑤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音樂是一種多樣化的人類實踐活動。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超越了狹隘的音樂審美研究范式,更加注重音樂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對音樂教育的研究必須和其文化語境聯系起來。“一種音樂文化的構成被不斷地在大量的文化關聯中實踐、挑選和修正。由此看來,音樂作品之生成于音樂實踐活動與它們文化的根基是不可分離的,即與它們基本的信仰和價值體系的網絡是不可分離的。”⑥
在《教學》中我們可以看到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在其中的運用。該書在對印度、泰國、伊朗、尼日利亞、日本、韓國、巴布亞新幾內亞各國音樂觀念、音樂的社會組織、音樂的曲目、音樂的物質文化等方面的闡釋后,都對這些國家的音樂教學做了設計。在教學設計中作者首先強調的是這些國家傳統音樂文化的教育學原理,作者更多的是從文化的角度來引導人們認知和理解這些國家的音樂。以泰國傳統音樂為例,作者在泰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教學寄語中認為泰國音樂的教學“首先是引導人們關注這一國家的民族信仰并感受泰國的宗教文化內涵,其次是介紹泰國音樂的主要傳承模式――口傳心授,最后是強調泰國音樂文化與生活世界及其它文化的關系”。⑦在教學設計中,作者以“文化中的舞蹈和舞蹈中的文化”為主題進行教學設計,要求學生了解“泰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理意義,泰國的歷史、宗教、服飾、建筑、繪畫、音樂等文化內涵與風貌及其民族氣質,泰國古典舞蹈和民間舞蹈的分類”。⑧在對這些泰國文化認知的基礎上引導學生觀賞舞蹈片段及學跳泰國舞蹈的簡單動作等實踐活動。“在了解、觀賞、學跳泰國舞蹈的過程中,教師采用啟發式的方法,帶領學生以共同觀察、共同討論的形式,使學生們直觀感受并體會泰國音樂的文化意蘊。”⑨在尼日利亞的音樂教學中,作者認為課堂教學過程應注意“樹立正確的音樂文化價值觀、非洲音樂文化區的劃分、音樂文化的傳統與變遷的問題、參與創造音樂、以多學科為基礎的綜合教學”等教學實踐原則。⑩
《教學》中教學設計所注重的“文化理解”的世界音樂的認知彰顯了哲學解釋學在其中的滲透。我們知道解釋學是一種哲學,是實踐哲學。伽達默爾將哲學的存在問題與人的存在經驗聯系起來,從而把哲學解釋學與人類實踐行為和人的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于是,以理解為主題的哲學解釋就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哲學,而更具有實踐的性質和意義。從此意義出發,建構以理解為核心的世界音樂教學就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由于音樂是一種文化,只有“當音樂被置于社會和文化的背景中并作為其文化的一部分,它才能獲得最佳的理解,對一種文化理解則需要對其音樂有所理解,而欣賞一種音樂則要求對與之相聯系的文化和社會有所了解。”{11}因此,以“文化理解”為導向的教學研究范式是世界音樂教學哲學建構的前提和基礎。從當前國際教育學發展背景來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生了重要的“教育學范式”的轉換,即由尋求普遍性的教育規律轉向尋求情境化的教育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世界音樂教學的實踐哲學就表明了文化情境中理解音樂的重要性。
三、跨文化理解的世界音樂教學
音樂人類學發展中的“主位”與“客位”雙視角的提出使西方和非西方互為研究對象,這消解了主客體的二元對立,突出了以文化差異性來代替文化同一性,以文化多元性來代替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在世界音樂的教學中我們不能用某一種音樂文化作為基礎來認知和理解異質文化,“如果我們武斷地進行二元對立的分法,必然會將我們的視野囿于以西方支配性的概念來理解不同音樂文化之間的差異,如用西方的樂理、和聲等來規范和闡釋中國或印度的音樂”。{12}因此,跨文化認知、理解世界音樂就顯得異常重要。
跨文化理解的世界音樂首先應具備文化并置的思維觀念,即將異質文化(other culture)與本土文化(native culture)放置在一起相互關照。在《教學》中,作者從所要描述音樂的“文化持有者內部的眼光”出發,運用文化并置方法引導人們去理解音樂。譬如,在泰國音樂文化的教學中,作者將泰國音樂與西方音樂進行并置來說明二者的傳承方式的差異。“泰國的音樂創作,與西方音樂記譜法有著鮮明的區別,那就是他們通常不是把音樂記在一張張紙上,而是采用口頭傳承模式,通過示范、模仿、記憶等一系列口傳身教的方式,從而將泰國民族的音樂代代承襲。”{13}在尼日利亞音樂文化教學中,作者從“時間觀”、“宗教觀”、“個人與集體”、“社會規范”、“哲學觀”、“個人與自然”幾個方面的文化并置來說明非洲和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差異。{14}以此理念作者以“非洲與西方的音樂對話”為主題進行了教學實踐的設計。在伊朗音樂的“節奏中的器樂文化”教學設計中作者將伊朗、阿拉伯、中國、日本的部分樂器文化并置來說明。
其次是對世界音樂觀念的認知和理解。“音樂在不同文化、同一文化不同歷史時期、同一文化同一時期不同社會階層(或群體)不同場合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概念、行為和形態,有不同的變化或交融情況,有不同的解釋、不同的含義和意義,有不同的功能和價值的實現。”{15}《教學》別強調引導學生對音樂觀念的認知,如印度梵我合一的音樂觀、泰國傳統音樂與佛教信仰水融的音樂觀、伊朗為神而歌的音樂觀、尼日利亞生命循環圈音樂觀念等等。從音樂觀念方面引導人們對世界音樂的理解突出了音樂教學的“消解中心、突出差異”的后現代特征。這種世界音樂教學有助于引導人們樹立音樂文化差異性的理念,因為“強調音樂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是以以往強調音樂文化的共性特別是音樂的歐洲中心主義盛行為背景的,它的價值在于反對文化霸權主義,保護世界多元音樂文化資源。”{16}
結語
《教學》中只闡釋了印度、泰國、伊朗、尼日利亞、日本、韓國、巴布亞新幾內亞音樂文化的教學,這遠遠不能滿足當前我國世界音樂教學的需要,但它為我們認知和理解世界音樂文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它跳出了傳統實體性思維的本質主義的音樂認知方式的樊籬,而關注從文化整體上去理解音樂。《教學》凸顯了世界音樂課程及其教學不能脫離音樂人類學的理念以及當今國際音樂教育前沿理論的滲透,它為我國的世界音樂課程建設提供了范本,即世界音樂課程建構應從“開發范式”走向“理解范式”,而不是傳統的“音樂”拼貼“文化”的課程建構范式。我們期待《世界音樂文化的教學》的內容不斷充實和豐富,也期盼出現更多的能夠體現當今前沿的教育理念和音樂文化觀念的世界音樂教學方面的成果,從而推動我國的世界音樂教學跟上當今多元文化發展的需要。
①管建華《音樂人類學導引》,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②(美)特里斯•M•沃爾克著,田林譯《音樂教育與多元文化――基礎與原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
③提頓和斯洛賓的“一種認識音樂世界的音樂文化模式”包括音樂的觀念、音樂與信仰體系、音樂的美學、音樂的語境、音樂的社會組織、音樂的曲庫(風格、類型、文本、創作、傳承、身體運動)、音樂的物質文化,參見管建華《世紀之交中國音樂教育與世界音樂教育》,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4―61頁
④管建華主編《世界音樂文化的教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頁
⑤埃里奧特著,柳志紅譯《走向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音樂教育》,2003年3、4合刊
⑥管建華《后現代音樂教育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頁
⑦⑧⑨⑩{13}{14}管建華主編《世界音樂文化的教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3頁、215―216頁、219頁
{11}劉沛譯《國際音樂教育學會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樂政策》,《云南藝術學院學報》,1998年《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專輯》
{12}朱玉江《音樂人類學理念對世界音樂教育的啟示》,《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后現代音樂教育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審美功能 學科功能 育人功能
要培養人格完整的人,音樂教育是不可缺的,音樂在體現人的個性直覺、技巧、想象和溝通能力方面有著獨特的功用;音樂藝術是人類文明、文化的集中體現與結晶,音樂藝術自身能起到輔助經濟發展的作用,當代社會需要生機勃勃的藝術的參與和建設。
一、加強音樂育人的審美功能
我們在欣賞音樂的同時,審美與情感也會一并抒發。如古箏《戰臺風》,在悠揚寧靜的氣氛中,使學生感受到情誼綿綿的同時,還有狂風暴雨的洗禮的,同時又感受到民族樂器的魅力與神奇的表現手法,增強學生對民族音樂的理解與熱愛。貝多芬創作的《歡樂頌》,給世界人民發出號召:為了和平,為了勞苦大眾,團結起來,充分表現了為“和平、幸福,快樂而奮斗”。聽起來會讓人產生為了信仰而甘心付出一切的愿望。從《高山流水》中尋找大自然的美,再從《十面埋伏》中激烈戰爭的場面,讓學生深切地體會到要奮斗,就要從我做起,不怕困難、勇往直前,去達到自己的理想,音樂可以表達學生的情感訴求,能引起你我之間的心有靈犀,它以美妙動聽的樂音傳達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使學生的人格得以健全和發展。音樂可以帶給人無限的歡樂,它是一股甜美的泉水,是健全人格最好的一種教育方式。因此,在音樂的信息中,要讓學生在心領神會的狀態下,感受大自然的美和藝術美的融會貫通,讓音樂的功能發揮到能提升心靈感應,起到健全人格的作用。
二、提高音樂育人的德育功能
對音樂藝術而言,道德是衡量學生心靈的一種方式,其存在有其現實意義。音樂教育,不完全是培養演奏家、歌唱家,而是培養人、健全人格的一種手段。它也對大學生的德智體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在澳門回到祖國的懷抱時,《七子之歌》曾喚起全世界炎黃子孫強烈的愛國之心,就像失散多年的孤兒終于找到了母親,游子對母親的依戀,此時此刻的心情,用歌聲表達得淋漓盡致;《太行山上》那有力的旋律,仿佛讓我們又回到了戰火硝煙的年代,使學生受到一次歷史與傳統的教育。又如《命運》交響曲,給人們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激發學生的正能量,教育學生面對困難時不畏縮,培養其迎難而上的進取精神。我們要充分利用音樂創作的作品教育學生,提高他們的創新能力,讓他們在情感上與音樂作品產生共鳴,使他們的情感通過音樂的方式去表達。例如,在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國》時,讓學生用音視相結合的方法進行體驗,引導學生在現代音樂教學手段下去感受祖國的強大、人們的善良聰慧、生活在美好大自然懷抱的幸福感等,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同時在技能、技巧上有能力欣賞有高超演唱技巧的美聲女高音滿懷深情的演唱,以及對祖國的拳拳之心。
我們要不斷鞏固學生純潔的、健康的心理修養,就要不斷升華音樂教育的深度,從而使學生有一個長期而穩定深厚的情感觀。在這里,首先要從大學生基礎的情感開始,培養他們愛國、愛家、愛親人的精神,在行動上建立熱愛父母、師長、學校等實際行動,慢慢啟發大學生從個人的狹隘天地中走出來,對鄉音、鄉情觀念的熱愛之情,最后達到愛國、愛家、愛人民的大愛精神。
三、發揮音樂與其他學科合作的功能
音樂教育首先要重視大學生德智體美勞綜合素質的訓練和培養,音樂教育作為育人的重要學科,要善于和其他德育學科相互結合,發揮其特殊的學科功能,加強培養學生技能技巧的基礎能力,提高理論水平,如音高、強弱、長短規律、音色的明暗對比、對優秀作品的分析、對演奏作品的詮釋、對和聲的選擇、對配器中調試等都要很好地理解掌握,使所有因素很好地結合,達到完美演繹作品的目的。通過學習和實踐演出,使學生在舞臺與理論的結合方面有所提高,從中受益于學科功能的培養,提高對其音樂的敏感度,使音樂可以表現出追逐和偶遇、挺進與停頓、感恩與彷徨等人生哲學。音樂是在有一定的遺傳因素的基礎上來理解和詮釋作品,重要的是提高演唱能力,有較好的模仿能力,才能有好的效果。樂器表演需要有手指的顆粒狀的彈奏,首先要提高技能技巧的訓練,才能很好地完成演奏。視譜練習要在教師音階式的模唱訓練中循序漸進地學習音準,掌握三度、四度、五度的模唱技巧,需要在練習音準、節奏方面達到準確無誤,音樂欣賞在某種程度上能加強學生的記憶力、充分發揮固定音高的作用。
音樂教育的三種功能:學科功能、德育功能和審美功能,這三種功能是相輔相成的,三者缺一不可。我們必須在音樂教育學科的落實上下功夫,這樣才能促進音樂教育的和諧與發展,才能體現對教育體系的特殊貢獻――音樂的育人功能,這一獨特的教育資源。筆者希望引起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音樂教育家、音樂工作者的高度重視,以推動音樂的育人功能的健康發展。
(注:本文為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項目編號:12D060)
參考文獻:
[1]張前.音樂美學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
[2]陳越紅.音樂審美與賞析[M].香港:中國國際出版社,1998.
[3]管建華.后現代音樂人類學的思考與寫作[J].音樂藝術,2011(1).
[4]孫玄齡.關于完善語言音樂學學科的設想[J].中國音樂學,2011(2).
[5]楊懷儒.音樂的分析與創作[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
后現代音樂教育學范文第5篇
摘要: 音樂人類學理論的一個核心思想,即研究與音樂相關的各種文化現象。作為音樂人類學家的約翰·布萊金,從文化的視角出發,提出了他的有關音樂的文化分析和文化并置的教育觀念,認為音樂是不同國家和民族自身文化的體現,它們各具特色、相互平等、多元共存。這種思想對于充實和發展多元文化音樂教育體系,建構當今的實踐音樂教育范式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和重大的意義。
中圖分類號: j601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2)03038005
“世界音樂”最早倡導人之一的約翰·布萊金(1928-1990)是一位在當代音樂教育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從他在英格蘭的音樂起步,到他對南非音樂的實地考察,從音樂人類學的視角提出了一系列有關音樂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念的創見,呼吁并倡導將世界音樂納入學校課堂。對此,音樂人類學家布魯諾·內特爾在布萊金《音樂、文化和體驗》一書的《前言》中曾高度評價,認為他“創造了許多改變和擴展學術研究發展方向的思想,同時廣泛且極大地影響到音樂研究的領域”[1]。筆者在邊譯邊學布萊金音樂論著的過程中,深深感到他的音樂教育理論的深刻和精辟。他關于音樂概念的人類學視野及文化內涵,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并置”音樂教育思想,可以說不僅奠定了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理論基礎,而且豐富和建構了不同于傳統音樂教育的音樂人類學的后現代哲學體系,從而宣告了西方音樂基礎主義永恒性的終結,乃是音樂教育的一個重要革新。
文達人音樂的啟示:約翰·布萊金對音樂文化分析法的構建
可以說,有關“音樂與文化”的研究,乃是音樂人類學家們長期以來探討的一個經典性的研究論題。他們認為:“音樂是一種文化的普遍現象,所有文化都擁有它們的音樂。每個社會都有一種與其社會相聯系的音樂體系,社會的其他文化,社會的多階層、各種年齡群體和其他社會支系,也擁有它們支系的音樂。”[2]35在每個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用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化符號體系得以溝通、綿延和傳續。因此,“音樂人類學”理論既研究音樂的聲音、概念、行為,也研究與音樂相關的各種文化現象。
在音樂與文化關系的思考中,學界尤為重視美國學者梅里亞姆的研究成果。據海倫·邁爾斯《民族音樂學導論》所言,梅里亞姆于1960年先是提出了“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音樂在文化中的研究”),由于當時人們的認識普遍停留在“音樂非文化”(音樂≠文化)的階段,所以他提倡將音樂安置于文化中去研究。隨著研究的進展,他認識到越來越多的音樂現象與文化的內在聯系,于是,在1973年修正為“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音樂作為文化研究”),提出應將音樂視作為文化(音樂≈文化)來認識。至1975年,他進而更正并強調“music is culture”(“音樂本身就是文化”)(音樂=文化),認為沒有任何一種音樂可以脫離其生存的文化環境。
伴隨著“人的音樂性”問題思考的還有一個重要音樂人,這就是約翰·布萊金。早在20世紀50年代,布萊金在具有非洲特點的德蘭士瓦地區的文達人中進行田野考察。通過將近兩年的實地調查和對文達人的生活習俗、社會文化的深入體驗與研究,他不僅感受到了文達人音樂獨特的文化特征,而且由此使他“更深刻的理解了他‘自己的’音樂”。1955年美國成立音樂人類學協會時,布萊金強調了音樂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將音樂人類學定義為研究“文化中的音樂”。布萊金認識到所有的音樂都要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來傳遞與表達意義,而“對不同音樂風格和技巧表面復雜性的區分并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有關表達的目的、音樂的力量以及有關創作中的智力組織方面有用的東西”。[3]序24音樂的意義是由不同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自然環境以及個人經歷所決定的。正是由于對文達地區的實地調查研究,使布萊金看到了“文化”在“音樂”體驗中的獨特作用,進一步證實了“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等音樂人類學的主題,回答了文化屬性在“人的音樂性”中的地位。對此,他在《文達孩子的歌》一書結尾中寫道:
我對文達兒童歌曲的細致分析可以證明:對人類組織的音響的文化背景的分析能夠告訴我們許多有關文化不同方面的內在相互關系以及人類的思想狀況,尤其是人類創作音樂過程中的思想。[4] 198
布萊金為此曾
過案例分析,立足文化語境,從內容、功能構成等角度考察文達人的音樂性質。如,通過對文達幼童在搖籃哺育期的哼唱歌謠以及女童啟蒙教育的歌舞程式等調研,他就發現文達人的民族文化、習俗在兒童音樂(歌唱、演奏、舞蹈)及其成長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文達兒童來說,歌唱和舞蹈并不是為了表演、炫技,而是他們自身的一種生存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文達兒童自幼年到成年,在許多場合中,往往就以歌舞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欲望,以及聯絡和溝通與成人和同伴之間的人際交往,歌唱與舞蹈與他們的生命成長的每一天幾乎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由此,布萊金進一步認識并建構了他的“音樂文化分析法”:也就是要求著重深入研究、分析與比較某一音樂作品其創作過程中的、有關民族、地域及其文化傳統與風俗習慣,以及個人與群體等諸多主客觀因素對音樂的作品形成、內容形式乃至發音原理與方法等的關聯、作用和影響。
在實地調查之初,布萊金心中亦存有將非洲音樂視作“他者”的偏見。對此,他在《人的音樂性·前言》中真實地記錄了他走向音樂文化分析的心靈過程:
是南非的文達人首先打破了我的一些偏見。他們介紹我進入了一個新的音樂體驗的世界,并使我對“自己的”音樂有了一個更深刻的理解。我一直將音樂理解為一種有序音響的體系,它是由一套積累的規則和一系列不斷增加的經許可的音響模式范圍所構成,并由被認為是擁有特殊音樂能力的歐洲人所發明并研制出來的。通過將不同的“聲波對象”與不同的個人體驗相聯系,通過不斷聆聽和演奏某個被認可的作曲家的音樂,以及通過選擇性的加強被認為是與階級利益無關的客觀審美性體驗,我獲得了一套表演的曲目和創作的技巧,同時音樂的價值如所預料的也正是社會和文化環境的結果。[3]23 他提出:“我們應該在人類的結構模式之間、在有組織的相互作用下而產生的音響模式之間,去尋找它們的關系。”[3]26他不無感慨地說:“在文達人中將近兩年的田野調查的主要結果以及試圖通過對12年來我的數據的分析,使我確認我開始明白了文達的體系。我不再如過去一樣清晰的理解歐洲‘藝術’音樂的歷史和結構;并且除了將它們當作商業標簽之外,我看不出對‘民間的’和‘藝術的’音樂術語之間進行區分有什么用。”[3]序24他由此真正確切地認識到了:人類各種文化、社會和民族,沒有價值上的差別,只是觀念、行為和由此產生的具體產品的不同;不同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屬性影響音樂的形式和內容,不同的音樂行為方式體現了不同的社會結構和屬性,也就是說,音樂中體現了文化,文化中包含了音樂。
如今,眾多的音樂學者都已普遍認同了音樂是一種具有象征性、社會性的文化種類,并把音樂作為文化體系的分支來進行研究。而這一音樂人類學所強調的對“音樂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音樂”進行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正是由于布萊金等一批音樂人類學家們研究并堅持的結果。當然,它也構成了布萊金不朽的音樂人類學遺產的主要部分。
從歐洲到世界:約翰·布萊金的音樂教育“文化并置”觀
從古代的“托勒密的世界模型”認為世界本由三個洲(歐洲、亞洲、非洲)、一個中心(希臘和羅馬)組成說開始,到近代出現的“西方民族中心主義”(以歐洲為文化中心),反映了歐洲近代以來隨著經濟與科技發展起來的對自己近代文化的自傲和推崇。“歐洲文化中心主義”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先進的文化”,其他文化也必須同化和走向這種“標準的文化”,并以此要求甚至強迫他種文化服從自己。在音樂學界和音樂教育界,受這種思潮的影響,自19世紀以來,所謂“音樂先進論”、“音樂進化論”即以歐洲音樂為高級、為楷模的“歐洲音樂中心論”。他們錯誤地認為,“音樂是從‘簡單’發展到‘復雜’的進化”[5]158,“無文字的民族的‘簡單’音樂,是音樂集體的產物而不是作曲家和創作表演者個體的作品”[5]前言x;“歐洲音樂的發展及其藝術體系高于其他音樂體系之上”[5]13。近代以來,隨著大量的歐洲音樂作品通過表演、音樂教育和經濟與殖民的擴張,更是進一步擴張到了世界各個地方。因而在音樂教育中普遍以“歐洲音樂”為標準,而忽視自身的存在,乃至以“歐洲音樂”替代了自身的民族音樂。
受文達人音樂啟示后的布萊金始終都在致力于對這種傳統音樂教育的觀點和理論的否定和批判。他認為,社會的
發展和技術的進化,并不能被看做是人類智力潛能的象征或普遍文化進化水平的象征。非洲的民間創作的音樂未必就低于西方交響音樂家的智力水平,那些“單純音響”的產生也同樣有它自身獨特的發生原理。對此,他說:“經過實地的科學調查,‘民間’音樂中的不規則節奏不是粗俗表演的結果,而是音樂思想的有意表達。”[5]53在某種意義上,“民間”音樂比“藝術”音樂的創作更貼近自然,它們不規則節奏乃至認真的重復(并不是所謂‘簡單的重復’)乃是一種文化的、習俗化的行為。[5]54由此,通過細致比較邊緣文化音樂與歐洲音樂,布萊金進一步認識到了“邊緣文化”的意義,逐漸形成一種去除中心的“文化并置”的音樂觀念。
布萊金提出世界文化是多元共存的,在音樂教育中,應當樹立多元的、開放的教育觀念。正如他在《對所有音樂的常識性觀察》書中所論述的那樣:對英國音樂教育來說,“既然當今英國社會從形成至今兩百年間的本質是一個多文化社會,那么,將世界音樂進入學校教育正是一個顯示英國音樂教育特色的事情:它將承認多種起源的音樂并且多種生活方式并存,同時通過共同探索音樂發展的志向激發英國民族的整體情結。”[5]133在傳授世界音樂的措施與政策上,他認為實施世界多元化音樂教育,不僅包括發揚本國民族成員的文化遺產,同時還要向外看,走出去,努力探索與接觸本土之外的沒有包含在本國范圍內的其它地域和民族的音樂精華。[5]149傳授世界的多元音樂同保持國家傳統音樂的一體性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應該說,布萊金將這種“文化并置”理念運用于音樂教育,以“邊緣文化”的價值觀批判與否定了傳統的歐洲“中心文化”教育觀念,從而使音樂教育從歐洲音樂的視野,轉向全球性視野,乃是對音樂教育的傳統模式的一個重大革新與突破。
音樂人類學家內特爾在他的《中心的游覽:音樂學院的音樂人類學反思》(1995年)一書的前言部分,就曾談到了他對這一觀念的認識與肯定,并較深刻地談到他對“文化并置”音樂教育的實踐中的認識與體會。他說為什么音樂人類學能夠吸引他四十多年,是因為:一是使他有機會聽到了完全陌生的、意想不到的音樂音響和感受到完全不熟悉的音樂觀念;其二,使他學會了如何看待世界各種文化以及聆聽各種音樂,而沒有任何現成的價值判斷;其三,學到了把握一種音樂文化的切入點,如何綜合的完整的理解一種音樂文化;其四 ,用一種圈外人的觀察來重新認識和評價自己的音樂文化。[6]246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已開始進入了各國音樂教育學術界的研究視野。在音樂人類學的視野下,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開始將不同的音樂文化并置,將它們看作是價值平等的不同的音樂表現形式。各國的音樂教育也開始從歐洲音樂轉向世界音樂;從單一文化的、單純的音樂觀念的學習轉向對音樂多元文化的、綜合的理解和學習;從以知識技能教學為主的“音樂工藝模式”轉向以文化理解與交流為主的“音樂文化模式”。
由審美到實踐:約翰·布萊金對音樂教學范式變革的貢獻
建立在18世紀美學基礎上的審美音樂教育哲學,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展起來的。這一范式主要認為音樂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情感的激發與培育,要求教師在教學中,通過音樂作品,使學生獲得情感上的美的感受與體驗。但是,這種范式僅局限于音樂作品本身而忽略了音樂創造的本質和重要性。特別是只看到了音樂作品而忽視了音樂作品創造的過程——具體的人的創造行為與具體的作品的創造的語境,即社會、民族、地域、文化、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對音樂作品產生的影響。 ,音樂人類學者較早提出了質疑。如梅里亞姆曾對音樂的功能進行了梳理和歸納,他認為音樂在人類社會中有十種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即情緒表達、娛樂、交流、審美欣賞、符號象征、身體感知、適應社會規范、維護社會機構與宗教儀式的權威、延續文化以及增強社會凝聚力等。很顯然,音樂的審美功能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布萊金在《人的音樂性》中亦指出,音樂是“人類組織的音響”,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之中,并沒有世界 “統一性”的、理解所有音樂都普遍有效的音樂審美觀念。安東尼·西格在《蘇雅人為什么要歌唱》中也指出:蘇雅人首先是為了他們的文化傳承而歌唱,而并非是將“審美”作為首位的或核心的功能。
既然審美功能只是音樂的其中一種功能,那么,我們的音樂教育有必要將“審
美”功能列為我們音樂教育的核心地位嗎?而且,“審美”和“音樂”的概念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中也具有不同的含義。比如,中國、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等國家都有著他們自己對音樂的界定和相關的哲學美學體系。因此,“審美”也就不可能替代人類整體的音樂經驗。
正是在梅里亞姆、布萊金等人的倡導下,才使音樂教育從長期以來以審美為核心和主流的教育范式轉向實踐的音樂教育范式,導致了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崛起。綜觀當今的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簡要概括,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1)音樂是一種多樣化的人類實踐
實踐音樂教育哲學認為,“音樂是一種多樣化的人類實踐”。音樂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次進行解讀:music,music和music(“音樂”、“樂”和“音”)。music指包含了許多種不同的音樂實踐(musics)的多樣化的人類實踐的本質和意義。每種音樂實踐則包含兩種相對應的、相互強化的活動:音樂制作和音樂聽賞。music(在更低的層次上)指的則是可訴諸聽覺的聲音事件、作品,或來自于特殊實踐語境中音樂實踐者創作出的可令人聽到的音樂成果[7]37,42。由此,音樂不僅僅是聲音,從事音樂的實踐者、實踐者的行動、結果、以及實踐的整個語境,都會對音樂的意義產生影響。因此,對音樂的理解不再限于技巧和形式的理解,對音樂的解讀和分析也不僅僅限于音樂結構、形式本身。
(2)世界音樂文化是一種包含多元價值的共同體
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強調世界上各種不同音樂文化的多元價值,認為每種音樂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無法取代的價值。只有承認和面向當代多元音樂文化,才能為音樂教育奠定課程設置、教學實踐的出發點。對此,布萊金在《對所有音樂的一種常識性觀察》中就談到:在人類這個多元化的音樂世界中的各種不同體制與形態的音樂,它們乃是相互聯系又各不相同的人類音樂財富,它們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其中并不存在所謂的什么“高級”、“低級”的等級關系,也不存在什么“復雜”、“簡單”的價值差別。
當今音樂教育面臨著多元挑戰。就學生而言,他們的民族、宗教、年齡、性別、種族、語言、階層、家庭環境、音樂能力等都是各不相同、多元化的,因此,音樂教育必須重視學生這種文化上的多元化。而由于音樂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情境性的、政治性的,因此,音樂教育也不能脫離社會環境去孤立的進行分析,也就應當進行多元的分析。另外,就音樂教育外部的社會文化而言,社會上也存在著傳統的主流文化和支流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多元的音樂文化正是共同存在于這樣的價值共同體之中。
(3)音樂教育應同時重視身體的體驗
實踐音樂教育哲學認為音樂本身就是一門表演的藝術,也應當重視表演。對此,布萊金在《對所有音樂的常識性觀察》中指出:“演奏和聆聽是音樂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5]133,認為學習和理解音樂,需要通過演奏(唱)和聆聽,強調身體的體驗在音樂體驗中的重要作用。
1984年8月在美國召開了威斯廉研討會。此次會議以“音樂教與學的社會人類學視野”為主題,得到了包括約翰·布萊金、布魯諾·內特爾、提姆·賴斯、麥克阿勒斯特、杰拉德·約翰遜、安妮·坎貝爾等專家學者的積極響應。這些專家學者通過自己的實踐和論證對傳統的審美范式提出了挑戰,認為尊重和認識文化的多樣性才是音樂教育的真正價值所在。與會者一致達成新的共識,即將“音樂作為文化”作為教授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觀念。這次會議,堪稱音樂人類學史上“第一次以文化傳播方式為重心,尋求其他音樂經歷、思想和世界范圍內信息的會議”。[8]1211996年,美國《國家藝術教育標準》的頒布,通過國家立法強調了音樂教育的六個方面的重要意義,更是充分體現了實踐哲學所倡導的“多元文化教育觀”:學習音樂是學習人類交流的一種基本形式;學習音樂是學習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學習音樂是學會學習的過程;學習音樂是學會想象力和自我表現力;學習音樂是學習的基礎;(6)學習音樂是學習藝術。[9]
21世紀的今天,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歷史新時期。約翰·布萊金等音樂人類學家的音樂教育思想,對于反思我們自己的音樂教育,有著不容忽視的學習和借鑒的意義。試想,在我們的音樂教學乃至一些專業音樂教學中,為何仍處于“歐洲音樂中心”的狀態?我們對于南亞、東南亞、阿拉伯、
亞、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音樂為何知之甚少?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我們不應僅僅局限于學習歐洲古典音樂,也還應注意學習和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世界各國的音樂。我們必須實施世界多元文化音樂的教學,這不僅將進一步擴展對我們自身音樂和我們民族文化的理解,更好地弘揚我國民族音樂傳統,同時也將進一步促進世界各國民族音樂文化相互的交流、借鑒,從而更好的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byron r.music,culture,and experience[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國際音樂教育學會.“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樂政策”[j]. 劉沛,譯.云南藝術學院學報:特刊,1998:63-64.
[3]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m]. 馬英珺,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
[4]blacking j.venda children ''s songs: an ethnomusicological analysis[m].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1967.
[5]blacking j. a commonsense view of all music[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管建華.后現代音樂教育學[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7]戴維·埃利奧特.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m].齊雪,賴達富,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