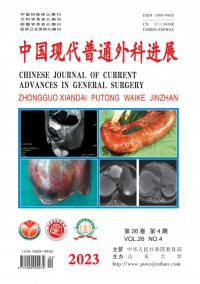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 法條競合 獨(dú)立競合 包容競合 特別法條
作者簡介:梁志,北京市通州區(qū)人民檢察院。
法條競合,又稱法規(guī)競合, 是指某一種行為同時符合了不同的法律條文所規(guī)定的犯罪構(gòu)成,但從法律條文本身的關(guān)系上來,當(dāng)然且排他的只能適用其中一個法律條文。換而言之,法條競合之所以存在是因?yàn)榉蓷l文所規(guī)定的某種行為或者現(xiàn)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現(xiàn)實(shí)生活確又千變?nèi)f化、無窮無盡,簡練而又高度概括的某個法條本身可能難以描述全部的行為。在此種情況下,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某一種犯罪行為可能既符合這個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也符合那個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難以絕對的割裂或者對立。遇到此種情形,不僅需要我們在立法層面不斷改進(jìn)立法技術(shù),減少法條競合的現(xiàn)象;更需要我們在司法實(shí)踐中學(xué)會合理適用相應(yīng)的原則處理法條競合的情況。法條競合是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當(dāng)中重要的理論,大陸法系國家普遍在刑法競合或罪數(shù)理論當(dāng)中對其進(jìn)行闡述。
一、 德日刑法學(xué)中的法條競合理論
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對法條競合的研究較為深入,目前我國法條競合的概念主要來自于德日刑法學(xué)。 以德國為例,其刑法學(xué)界以行為的單復(fù)數(shù)為出發(fā)點(diǎn), 將刑法競合分為想像競合、實(shí)質(zhì)競合與法條競合:
1.想像競合,指一行為數(shù)次違反同一刑法法規(guī)或者數(shù)次觸犯同一刑法法規(guī)的情形。
2.實(shí)質(zhì)競合,指行為人實(shí)施了數(shù)個獨(dú)立的將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受審判的犯罪情形。
3.法條競合,是指表面上數(shù)個刑法條文之間有競合,但實(shí)質(zhì)上只能適用其中的一個條文而當(dāng)然地排除其他競合條文的適用。雖然德國的刑法典中沒有關(guān)于法條競合的明確規(guī)定,但其理論界卻有著相對深入的探討,認(rèn)為法條競合其本質(zhì)上是犯罪單數(shù)。
要理解日本刑法學(xué)界對于法條競合的研究,首先需要明晰該國關(guān)于罪數(shù)形態(tài)的相關(guān)理論。在日本刑法學(xué)界,通常分為以下三類 :
1.本來的一罪,按其字面的意思理解,實(shí)質(zhì)上一個行為只符合一個構(gòu)成要件。常見的情況有一行為可能觸犯了數(shù)個法益,但該數(shù)個法益均在同一構(gòu)成要件之下;再如集合犯、連續(xù)犯、結(jié)合犯等;同時,法條競合也包括在本來的一罪中。
2.科刑上的一罪,即一個行為或者數(shù)個行為符合數(shù)個構(gòu)成要件,但并不以數(shù)罪論處,在科刑上只做一罪處理。最典型的有想象競合犯,即一個行為符合數(shù)個構(gòu)成要件,但根據(jù)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的原則,禁止重復(fù)評價,一行為只評價一次。再如牽連犯,即作為犯罪手段的行為或者結(jié)果的行為觸犯其他的罪名,并不按數(shù)罪處罰,而是擇一重罪處罰。
3.并合罪,即按照行為的不同分別定罪,數(shù)罪并罰。由此可見,在日本刑法中法條競合屬于本來的一罪。
二、 我國刑法關(guān)于法條競合的理論
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刑法上對犯罪分類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較為清楚,主要以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為主。宏觀上可以分為侵犯公民個人權(quán)益的犯罪、侵犯法律所保護(hù)的社會法益的犯罪以及危害國家利益的犯罪;在微觀上以行為特征為標(biāo)準(zhǔn),分為各種具體的犯罪,故而犯罪的重復(fù)出現(xiàn)比較少見。與此不同,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gòu)成采用四要件論。因此,雖然目前我國刑法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主要以犯罪行為侵犯的客體為主,但犯罪主體、犯罪的客觀方面也被作為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而這三種劃分標(biāo)準(zhǔn)的同時存在,必然導(dǎo)致我國刑法上對于犯罪的規(guī)定較為錯綜復(fù)雜,在適用刑法條文時出現(xiàn)大量法條競合的現(xiàn)象。如一些常見的職務(wù)犯罪以犯罪主體作為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貪污罪、職務(wù)侵占罪和侵占罪,這三個罪名在犯罪的客觀方面具有相似之處,但因?yàn)榉缸镏黧w的身份不同,導(dǎo)致最終適用罪名的不同。
在我國刑法理論中,法條競合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
(一)獨(dú)立競合
所謂獨(dú)立競合,亦被稱為特別關(guān)系,是指一個犯罪行為同時符合兩個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但該兩個法律條文中一個為一般性的規(guī)定,一個為針對特定犯罪的特別規(guī)定。在此種情況下處理法條競合的規(guī)則應(yīng)該是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即“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適用” 的原則。如我國《刑法》第266條規(guī)定的詐騙罪與第224條規(guī)定的合同詐騙罪即為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在一般情況下適用266條的規(guī)定,但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詐騙的,則適用224條之規(guī)定。因此,也可以理解為相對于普通法的規(guī)定而言,正是由于特別規(guī)定的存在,使其從普通法規(guī)定中分離出來。
(二)包容競合
包容競合,是指“一個罪名概念的外延是另一罪名概念的外延的一部分,但犯罪構(gòu)成的內(nèi)容已經(jīng)超過外延窄的罪名概念的情形”。此種情況下處理法條競合的方式是全部法優(yōu)于部分法。 一般而言,該類型的法條競合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被稱為吸收關(guān)系,日本學(xué)者則視其為法條完全與不完全的競合。相較于其他大陸法系國家而言,我國刑法中的包容競合情形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過多的設(shè)置加重構(gòu)成,將他罪作為本罪的加重構(gòu)成;另一方面,我國刑法中按犯罪所侵犯的客體為標(biāo)準(zhǔn)對犯罪進(jìn)行分類,從而導(dǎo)致罪名之間發(fā)生重合。
(三)交互競合
交互競合,是指刑法條文規(guī)定的兩個罪名之間具有部分的重合,在處理此種法條競合時應(yīng)當(dāng)適用的方法是重法優(yōu)于輕法。在德國刑法學(xué)界將這種情況稱之為法條競合的擇一關(guān)系,學(xué)者認(rèn)為擇一關(guān)系存在的前提是構(gòu)成要件行為的部分重疊,這也是有別于包容競合的關(guān)鍵。但日本刑法學(xué)界有學(xué)者持有不同觀點(diǎn),認(rèn)為擇一關(guān)系并不屬于法條競合,而是針對具體的犯罪事實(shí)進(jìn)行判斷,而后再選擇適用的法律,實(shí)質(zhì)上屬于對事實(shí)的判定,而非法條競合本身的問題。 (四)偏一競合
偏一競合,是指兩個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具有交叉重合之處,但是犯罪行為卻已經(jīng)超出了交叉重合的規(guī)定。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偏一競合又稱為補(bǔ)充關(guān)系,對于該類法條競合處理的方式是基本法優(yōu)于補(bǔ)充法 。在我國刑法中最典型的偏一競合的例子是《刑法》第114條與《刑法》第115條的規(guī)定,普遍認(rèn)為《刑法》第115條的規(guī)定是基本法,第114條為特殊法。當(dāng)行為人實(shí)施了放火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又尚未造成嚴(yán)重后時,雖然其行為符合了第115條規(guī)定的部分要件,但因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而不能適用第115條之規(guī)定,只能適用第114條之規(guī)定。
三、 我國法條競合理論存在的問題
(一)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與重法優(yōu)于輕法的沖突問題
在處理法條競合的特殊關(guān)系時,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被廣泛運(yùn)用,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卻會出現(xiàn)特殊法輕而普通法重的情形,對此應(yīng)該如何處理,理論界存在不同的觀點(diǎn)。
有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特別法應(yīng)當(dāng)絕對優(yōu)于普通法,除法律明確規(guī)定外,任何人都不得違背法律作出個人的價值判斷 ,從而適用作為普通法的重法而排除適用作為特別法的輕法。同時,也有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當(dāng)法律明確規(guī)定優(yōu)先用重法或者法無明文禁止適用作為重法的普通法時,可以按照重法優(yōu)于輕法的原則處理此類法條競合問題。
筆者也較為贊同第二種觀點(diǎn)。雖然一般情況下,立法者之所以在設(shè)立普通法之外還要專門設(shè)立特別法,本身就是因?yàn)槟撤N犯罪具有特殊或者突出的特點(diǎn),必須針對這些特點(diǎn)予以懲罰,所以在行為符合特別法的規(guī)定時應(yīng)該按特別法處理。然而,當(dāng)法律明文規(guī)定按重罪定罪量刑或法律雖沒明文規(guī)定,但如果按特別法處罰明顯不符合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時,則可以按照具體情況適用重法優(yōu)于輕法原則。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刑法中的法規(guī)競合關(guān)系尤為復(fù)雜,優(yōu)、劣位法條在立法的層面上互相補(bǔ)充,因只能擇一適用在司法的層面上又互相排斥。優(yōu)位法條的區(qū)分與適用規(guī)則的建立是法規(guī)競合研究的理論出發(fā)點(diǎn)和實(shí)踐指向。將法規(guī)競合區(qū)分為邏輯性的法條競合與評價性的法條競合,有助于合理區(qū)分并適用優(yōu)位法條;法規(guī)競合不適用“重法優(yōu)于輕法”;我國刑法分則對優(yōu)位法條“從重”或“從輕”之特別規(guī)定顯然違背現(xiàn)有的罪數(shù)理論,視其為立法的特別規(guī)定更有助于保持罪數(shù)理論的協(xié)調(diào)和內(nèi)在統(tǒng)一性。
“法律秩序的統(tǒng)一不是事實(shí)上的存在,而只是一種理想。”法律作為抽象的行為規(guī)范,一個法律規(guī)范通常調(diào)整符合一定要件的一類法律關(guān)系;由于現(xiàn)代社會法律體系的立體化結(jié)構(gòu),常常發(fā)生同一事實(shí)符合數(shù)個規(guī)范的要件,數(shù)規(guī)范皆得適用并產(chǎn)生數(shù)個法律效果的現(xiàn)象,稱為規(guī)范競合。因刑法規(guī)范受到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即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處罰,不能適用類推原則,所以刑法規(guī)范中的竟合關(guān)系更為錯綜復(fù)雜。面對具有競合關(guān)系的數(shù)法條,如何選擇并適用其中的優(yōu)位法條既是理論上需要進(jìn)一步澄清,也是司法實(shí)踐中常常面對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法條互補(bǔ)——法規(guī)何以競合?
(一)何謂法規(guī)競合?
法規(guī)競合又稱法條競合,在德國刑法理論中稱“假性競合”或“法律單數(shù)”,指數(shù)個刑法法規(guī)只是表面上相競合,但實(shí)際上是一個刑法法規(guī)排除了其他刑法法規(guī)的情況。就理論體系而言,德國學(xué)者對法規(guī)競合的研究是相對于真正競合,即想象競合犯和實(shí)質(zhì)競合展開的;而日本學(xué)者是把法規(guī)競合放在罪數(shù)理論中加以研究,代表性的觀點(diǎn)如大塚仁教授認(rèn)為:“一個行為在外表上可以認(rèn)為相當(dāng)于數(shù)個構(gòu)成要件,但是,實(shí)際上只適用其中某一個構(gòu)成要件,其他的構(gòu)成要件當(dāng)然應(yīng)該被排除的場合,稱為法規(guī)競合”。不過,何以其他的構(gòu)成要件“當(dāng)然應(yīng)該被排除”,大塚仁教授并未加以指明。
我國學(xué)者對法規(guī)競合的研究秉承了日本學(xué)者的思路,將法規(guī)競合作為罪數(shù)形態(tài)的一種加以研究;不過,對發(fā)生競合的劣位法條何以“當(dāng)然應(yīng)該被排除”未予深究,往往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是邏輯上的排除關(guān)系,因而一般采取邏輯分析的方法對發(fā)生競合之諸法條的包容或交叉關(guān)系加以研究并決定優(yōu)、劣位法條的取舍。如張明楷教授認(rèn)為,法條競合是指一個行為同時符合了數(shù)個法條規(guī)定的犯罪構(gòu)成,但隊(duì)數(shù)個法條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來看,只能適用其中一個法條,當(dāng)然排除適用其他法條的情況。陳興良教授認(rèn)為,犯罪構(gòu)成之間存在邏輯上的從屬或交叉關(guān)系是法條競合的邏輯本質(zhì)。劉士心博士認(rèn)為,法規(guī)競合犯的法規(guī)選擇,取決于數(shù)法規(guī)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理清立法中法規(guī)競合邏輯模式及其與法規(guī)競合犯類型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是科學(xué)確立法規(guī)競合犯法律適用原則的基礎(chǔ)。
問題在于,僅以邏輯分析的方法能否窮盡法條之間的關(guān)系在方法論上并非沒有疑問,如果規(guī)定不同構(gòu)成要件的法條之間都是并列關(guān)系。或許這種方法還可成立;然而,法條之間除并列關(guān)系外,還存在錯綜復(fù)雜的交錯關(guān)系。“法律中的諸多法條,其彼此并非只是單純并列,而是以多種方式相互指涉,只有透過它們的彼此交織及相互合作才能產(chǎn)生一個規(guī)整。”在刑事立法中,為嚴(yán)密法網(wǎng),立法者往往從不同的角度歸納可罰行為的類型,并規(guī)定相應(yīng)的犯罪構(gòu)成,這就使得不同罪名的犯罪構(gòu)成之間不是平面的并列關(guān)系,而是處于立體的交錯狀態(tài)。因而,大塚仁教授所稱的“當(dāng)然應(yīng)該被排除”,除了邏輯上的排除關(guān)系外,更主要的還包括規(guī)范評價上的排除關(guān)系,而后者對法規(guī)競合的研究至關(guān)重要。為盡可能描述出質(zhì)的規(guī)定性,以體現(xiàn)概念的區(qū)分功能,筆者試對法規(guī)競合界定如下:
法規(guī)競合是指行為人實(shí)施一個犯罪行為,由于觸犯具有邏輯或刑法評價上包容關(guān)系的數(shù)個罪名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表面上導(dǎo)致該數(shù)個罪名皆可適用,而依邏輯或刑法評價上的包容關(guān)系當(dāng)然適用包容法條的犯罪競合形態(tài)。
(二)優(yōu)、劣位法條何以并存?
就單一的法條而言,并無優(yōu)劣之分。不過,“在罪刑法定原則對構(gòu)成要件的明確性要求之下,描述事實(shí)的概念元素所組成的規(guī)范通常只有一個評價角度,而一個具體發(fā)生的犯罪事實(shí),卻可能同時符合數(shù)個構(gòu)成要件,因此便可能發(fā)生數(shù)個構(gòu)成要件可同時詮釋一個犯罪事實(shí)的情形”。例如,放火行為同時有公共危險和毀損兩個評價角度,只不過通常的評價是從公共危險的角度出發(fā)而已;盜竊槍支彈藥可以同時有盜竊和盜竊槍支彈藥兩個評價角度。可見,同樣一個行為,在規(guī)范評價上原本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得出不同的評價結(jié)論。當(dāng)兩個法條都可以對產(chǎn)生同一具體危害事實(shí)之一行為進(jìn)行評價,而兩法條又不能同時適用,不得不在兩法條之間“PK”擇一適用之際,就會產(chǎn)生優(yōu)、劣位法條之分。
法條之間不會無緣無故地發(fā)生競合,競合的實(shí)質(zhì)在于數(shù)個不同法條的犯罪構(gòu)成同時適用于同一具體危害事實(shí),相互之間在評價事實(shí)要素上的包容或交叉關(guān)系。在筆者看來,法條之間處于包容競合關(guān)系的構(gòu)成法規(guī)競合,處于交叉競合關(guān)系的則構(gòu)成想象競合犯。就法規(guī)競合而言,在競合的諸法條中,構(gòu)成要件對犯罪行為的評價事實(shí)要素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法條即優(yōu)位法條,其它法條即劣位法條。形象地說,如果將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各個構(gòu)成要件看作評價犯罪行為用的大小不一的容器的話,法規(guī)競合即指幾個不同的容器都可以容納某一犯罪行為,而優(yōu)位法條所規(guī)定的構(gòu)成要件是在規(guī)范評價上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容器;一旦找到這個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容器后,其余容器已無適用的余地,可棄之不用。
優(yōu)、劣位法條并存,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并非立法的疏失,反而是立法者有意而為之,旨在嚴(yán)密法網(wǎng),充分發(fā)揮刑法保護(hù)社會、打擊犯罪之功能。簡而言之,優(yōu)、劣位法條在一部法典中并存至少體現(xiàn)了如下立法指向:
1補(bǔ)充性。正如貝卡利亞所指出:“對于犯罪最強(qiáng)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yán)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各國刑法普遍增設(shè)了危險犯和持有犯的補(bǔ)充性的立法例。與實(shí)害犯相比,危險犯缺少了物質(zhì)性的犯罪結(jié)果;如果刑法沒有危險犯的規(guī)定,就不利于打擊對重要法益具有高度現(xiàn)實(shí)侵害性的行為。基于同樣的考慮,如果司法機(jī)關(guān)對犯罪行為人所持有特定物品,如的來源、去向不便查清,就很難以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罪定罪;為了加強(qiáng)對特定物品的管理,遏制相關(guān)犯罪,填補(bǔ)犯罪構(gòu)成的空隙,刑法另設(shè)了非法持有罪等持有犯,對于預(yù)防下游犯罪和打擊上游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2著重性。立法者在設(shè)定普通犯構(gòu)成要件的同時,對普通犯的某一構(gòu)成要件要素特殊強(qiáng)調(diào)又規(guī)定了相應(yīng)的特別犯,如我國刑法在第264條盜竊罪和第267條搶奪罪的普通犯之外,在第127條就犯罪對象的特殊性規(guī)定了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zhì)罪;在第364條規(guī)定的傳播物品罪的普通犯之外,基于犯罪目的的特殊性,在第363條第1款又規(guī)定了傳播物品牟利罪等等,針對這些特殊強(qiáng)調(diào)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刑法規(guī)定了更高刑度的法定刑,體現(xiàn)了著重打擊的立法態(tài)勢。另外,立法者有時還會對特別犯規(guī)定低于普通犯的法定刑,如我國刑法對職業(yè)過失犯罪規(guī)定了低于普通過失犯罪的法定刑,如第133條交通肇事罪致人死亡和第335條醫(yī)療事故罪造成就疹人死亡的法定刑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低于第233條過失致人死亡罪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二、法條互斥——優(yōu)位法條何以區(qū)分、適用?
優(yōu)、劣位法條的區(qū)分主要是從法條適用的角度而言,二者的微妙關(guān)系在于,在立法的層面上原本互相補(bǔ)充,因只能擇一適用在司法的層面上卻又互相排斥。
(一)優(yōu)、劣位法條何以不能同時適用?
前文已述,法規(guī)競合是指行為人實(shí)施一個犯罪行為,由于觸犯具有邏輯或刑法評價上包容關(guān)系的數(shù)個罪名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表面上導(dǎo)致該數(shù)個罪名皆可適用,而依邏輯或刑法評價上的包容關(guān)系當(dāng)然適用包容法條的犯罪競合形態(tài)。可見,法規(guī)競合以同一犯罪行為觸犯的數(shù)個法條之間具有邏輯或刑法評價上的包容關(guān)系為前提,如果同時適用具有包容關(guān)系的優(yōu)位法條和劣位法條,必然造成對同一行為的重復(fù)評價。如法條A的構(gòu)成要件有a、b、c、d、e五個要素,而法條B的構(gòu)成要件有a、b、c三個要素,換言之,A構(gòu)成要件擁有B構(gòu)成要件所有的要素,并且含有B不具備的要素,因而A構(gòu)成要件可以將B所有的要素都包含于內(nèi),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如果構(gòu)成A構(gòu)成要件,則必然構(gòu)成B構(gòu)成要件。如果同時適用A、B兩個構(gòu)成要件,則B的所有要素a、b、就會重復(fù)評價,顯然評價過度,違反了禁止重復(fù)評價原則,因而是不適當(dāng)?shù)摹?/p>
(二)優(yōu)位法條何以區(qū)分?
所謂優(yōu)位法條的區(qū)分,即如何從競合之?dāng)?shù)法條中找到在邏輯或刑法評價上具有包容性的法條。優(yōu)位法條區(qū)分規(guī)則的建立與法規(guī)競合的分類密切相關(guān)。如何對法規(guī)競合進(jìn)行分類是法規(guī)競合研究的重要問題,各國刑法理論有不同的分類方法,意大利刑法第15條規(guī)定:“當(dāng)不同的法律或同一刑事法律中的不同條款調(diào)整同一問題時,特別法或法律中的特別條款優(yōu)于普通法或法律中普通條款,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因而,在意大利刑法理論中只承認(rèn)特別關(guān)系的法規(guī)競合,特別條款即優(yōu)位法條。德、日刑法學(xué)在傳統(tǒng)上將法規(guī)競合分為特別關(guān)系、補(bǔ)充關(guān)系、吸收關(guān)系和擇一關(guān)系,因而規(guī)定特別條款、基本法構(gòu)成要件的條款、構(gòu)成要件更具有完全性的條款和從構(gòu)成要件的對立關(guān)系中選擇其一并適用的條款即優(yōu)位法條。不過,擇一關(guān)系和吸收關(guān)系是否構(gòu)成法規(guī)競合在理論上還有爭論,德國學(xué)者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的見解認(rèn)為法條競合只有特別和補(bǔ)充兩種類型,表明了從理論上對法規(guī)競合的成立范圍加以限縮的趨勢。
我國學(xué)者偏重于從邏輯分析的角度對法規(guī)競合提出了多種分類方法,如“兩分法”,即全包含關(guān)系的法條競合和交叉重疊關(guān)系的法條競合,或從屬關(guān)系的競合與交叉關(guān)系的競合;再如“兩類四分法”,即先將法規(guī)競合分為從屑關(guān)系的競合與交叉關(guān)系的競合,又將前者分為獨(dú)立競合、包容競合,后者分為交互競合、偏一競合等等。
在以上對法規(guī)競合分類的觀點(diǎn)中,對包含關(guān)系的主張筆者并無異議,對交叉關(guān)系的主張則難以認(rèn)同。如果行為觸犯的是兩個法條的交叉部分,無論是所謂交互競合還是偏一競合,除了法定刑的比較以外,無法建立優(yōu)位法條的區(qū)分規(guī)則;然而,法規(guī)競合是犯罪構(gòu)成的競合,而非法定刑的競合,如果以“從一重處斷”作為優(yōu)位法條的確立方法,必然引發(fā)法規(guī)競合與想象競合犯的混淆。因而,筆者主張引入規(guī)范評價的方法對競合之?dāng)?shù)刑法規(guī)范的關(guān)系加以理清,在法規(guī)競合的分類上,筆者贊同日本學(xué)者瀧川幸辰的主張,即把法條競合分為邏輯性的法條競合與評價性的法條競合。這種分類方法有助于理清法條之間錯綜復(fù)雜的交錯關(guān)系,也有助于確立優(yōu)位法條。
1邏輯性法規(guī)競合:指特別關(guān)系的法規(guī)競合,即特別法與普通法之競合。特別關(guān)系的法規(guī)競合可分為明示的特別關(guān)系與默示的特別關(guān)系。以我國刑法為例,明示的特別關(guān)系是指刑法明文規(guī)定“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規(guī)定”,因而第192條集資詐騙罪、第193條貸款詐騙罪、第194條第1款票據(jù)詐騙罪、第194條第2款金融憑證詐騙罪、第195條信用證詐騙罪、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第197條有價證券詐騙罪、第198條保險詐騙罪、第204條第1款騙取出口退稅罪、第224條合同詐騙罪等就是266條詐騙罪的特別規(guī)定,觸犯了以上特別規(guī)定,就依照特別規(guī)定定罪處刑,不再論以普通的詐騙罪。此外,刑法雖然沒有明文規(guī)定是“本法另有規(guī)定”,但實(shí)際上對某一情形另有規(guī)定的,也可以視為準(zhǔn)明示的特別關(guān)系。如第310條第1款規(guī)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1979年舊刑法沒有規(guī)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故可以認(rèn)為消滅罪跡與毀滅罪證的行為構(gòu)成包庇罪;由于1997年新刑法另設(shè)了第307條的規(guī)定,故幫助犯罪行為人湮滅罪跡和毀滅罪證的行為,應(yīng)認(rèn)定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而不再構(gòu)成包庇罪。
默示的特別關(guān)系即從邏輯角度看,普通法與特別法處于屬種關(guān)系,屬是上位概念(普通構(gòu)成要件),種是下位概念(特別構(gòu)成要件)。特別構(gòu)成要件之所以稱為特別,在于其比普通構(gòu)成要件多了一個以上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適用特別構(gòu)成要件即可完成對行為不法內(nèi)涵的完整評價。例如,雖然(種概念)也是犯罪所得的贓物(屬概念)的一種,但依照我國刑法第349條的規(guī)定,窩藏的直接定窩藏罪即可,而不必再論以第312條的窩藏罪。
以上特別關(guān)系的法規(guī)競合是邏輯性的法規(guī)競合,也是典型的法規(guī)競合。在特別關(guān)系中,實(shí)現(xiàn)特別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每一個行為,還同時實(shí)現(xiàn)一般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故規(guī)定特別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條款即優(yōu)位法條,這一點(diǎn)在理論和實(shí)踐中從無爭議。
2評價性法規(guī)競合:指主要依據(jù)刑法規(guī)范價值判斷上的包含關(guān)系確定并適用優(yōu)位法條的法條競合。在評價性法規(guī)競合中,優(yōu)位法條和劣位法條之間并沒有邏輯上的屬種關(guān)系,而是刑法評價上主要與補(bǔ)充的關(guān)系。具有補(bǔ)充關(guān)系的數(shù)法條在立法上系不同的刑法規(guī)范以不同的立法手段保護(hù)同一法益。
基于我國刑法分則的規(guī)定,基本犯構(gòu)成要件之間的法規(guī)競合比較復(fù)雜,可簡要區(qū)分為以下幾種情形:①整體法對部分法的包容性立法。主要指我國刑法中包容犯的立法,如第239條規(guī)定的綁架罪,將“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作為加重處罰事由并規(guī)定了死刑,從而使綁架罪在罪質(zhì)上包容了過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殺人罪。類似地,第115條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zhì)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263條搶劫罪等都可以包容故意殺人罪。②補(bǔ)充法對基本法的補(bǔ)充性立法。如我國刑法中第240條拐賣兒童罪與第262條拐騙兒童罪,拐賣以拐騙為前提又超出了拐騙,前者是基本法,后者是對前者的補(bǔ)充性立法。③危險犯對實(shí)害犯的補(bǔ)充性立法。危險犯是立法者針對比較重要的法益而設(shè)的提前保護(hù)的立法方式,不必等到實(shí)害結(jié)果發(fā)生后再打擊犯罪。④持有犯的補(bǔ)充性立法,
如果數(shù)個法條以不同的侵害階段來保護(hù)同一法益,則數(shù)法條之間處于補(bǔ)充關(guān)系,適用主要規(guī)范,就可以不適用補(bǔ)充規(guī)范,因?yàn)橹饕ǖ膶?shí)現(xiàn)必然會貫穿補(bǔ)充法,所以較低危險的侵害階段不被考慮在內(nèi)。在以上評價性法規(guī)競合各種情形中,優(yōu)位法條的確立關(guān)鍵在于找到包容法,即構(gòu)成要件上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法條,分別為規(guī)定整體法的法條、基本犯的法條、實(shí)害犯的法條和特定物品犯罪的法條。
(三)優(yōu)勝劣汰——優(yōu)位法條何以適用?
理清優(yōu)位法條和劣位法條之間的關(guān)系,并選擇適用其中的優(yōu)位法條(即優(yōu)勝劣汰)是法規(guī)競合法律適用的基本思路。
我國學(xué)者對優(yōu)位法條如何適用提出了種種不同的主張,如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全部法優(yōu)于部分(局部)法、復(fù)雜法優(yōu)于簡單法、重法優(yōu)于輕法、狹義法優(yōu)于廣義法、實(shí)害法優(yōu)于危險法和基本法優(yōu)于補(bǔ)充法等等。在筆者看來,除了重法優(yōu)于輕法的適用原則值得商榷外,上述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等主張均有其合理性,只不過是對同一問題不同角度的表述而已。筆者試圖用一句話來概括法規(guī)競合的法律適用原則,即“包容法優(yōu)于被包容法”,其中的包容法從邏輯或規(guī)范評價的不同角度可以理解為上述特別法、全部法、復(fù)雜法、狹義法、實(shí)害法或基本法。由于學(xué)者對上述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等原則已有較為明確的論述,故本文不再贅述。
三、優(yōu)位法條區(qū)分、適用中的疑難問題
(一)優(yōu)位法條是否要“從重”選擇并適用?
“從重”選擇并適用,即法規(guī)競合是否適用“重法優(yōu)于輕法”?所謂重法優(yōu)于輕法,即一行為觸犯的兩個刑法規(guī)范規(guī)定的刑罰有輕重之別時,適用重法而排除輕法,關(guān)于這一原則的適用范圍和性質(zhì),有學(xué)者認(rèn)為,重法優(yōu)于輕法是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的補(bǔ)充原則,一種行為形式上雖然符合特別法的規(guī)定,但由于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又符合普通法的規(guī)定,依照特別法定罪量刑顯然不能做到罪刑相適應(yīng)時,便按照處罰更重的普通法即重法定罪量刑。還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當(dāng)普通法與特別法競合時,不能從重選擇刑法規(guī)范,重法優(yōu)于輕法僅適用于法條交互競合的情況。而所謂交互競合,表現(xiàn)為兩個法條交叉競合,所競合的正是法條間交叉重合的部分。上述法規(guī)競合是否適用“重法優(yōu)于輕法”的論爭,其根源在于邏輯上具有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是否成立法規(guī)競合?這是法規(guī)競合研究中最富爭議也是理論上最為模糊的問題。實(shí)際上涉及到如何區(qū)分法規(guī)競合和想象競合犯。陳興良教授認(rèn)為:“法條競合是指行為單數(shù)而法律復(fù)數(shù)的情形”,這一界定恰好混淆了法規(guī)競合與想象競合犯的區(qū)別。法規(guī)競合必然是法律單數(shù),即在刑法評價上只適用優(yōu)位法條,劣位法條被排除出局;而想象競合犯有別于單純的法律單數(shù),稱之法律復(fù)數(shù)亦無不可,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想象的數(shù)罪、處斷的一罪,還有學(xué)者干脆主張是數(shù)罪,有些國家確實(shí)有將想象競合犯作為數(shù)罪處罰的立法例。
在筆者看來,重法優(yōu)于輕法即“從一重處斷”,這恰好是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如果以法定刑較重這一點(diǎn)來確立優(yōu)位法條的話,實(shí)際上運(yùn)用的是想象競合犯“從一重處斷”的處罰原則,而法規(guī)競合在理論上無法得出重法優(yōu)于輕法的處罰原則。簡言之,法規(guī)競合與想象競合犯的不同之處在于:其一,法規(guī)競合觸犯的數(shù)法條之間存在邏輯或評價上或優(yōu)或劣的必然競爭關(guān)系,不因個案有所改變,不必以具體的犯罪行為作為媒介;想象競合犯觸犯的數(shù)法條之間處于偶然競爭關(guān)系,隨個案有所改變,離不開具體的犯罪行為作為媒介;其二,法規(guī)競合適用優(yōu)位法條,劣位法條在定罪和量刑的過程中一般被排斥不論;對想象競合犯的處罰,筆者主張“從一重處斷”并適用結(jié)合刑原則,即適用法定刑較重的優(yōu)位法條,在量刑上不得低于規(guī)定法定刑較輕的劣位法條。其三,法規(guī)競合是本來的一罪,而想象競合犯是處斷的一罪。
(二)如何理解我國刑法分則對法規(guī)競合優(yōu)位法條“從重”或“從輕”之特別規(guī)定?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第3篇
笑顏
笑顏同志:
電子合同是在網(wǎng)絡(luò)條件下當(dāng)事人之間為了實(shí)現(xiàn)一定的目的,通過電子郵件和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明確雙方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的協(xié)議。電子勞動合同作為電子合同的一種,具有電子合同的屬性。我國《合同法》已將傳統(tǒng)的書面合同形式擴(kuò)大到數(shù)據(jù)電子形式。數(shù)據(jù)電子形式是書面合同形式的一種。《合同法》第十一條明確規(guī)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shù)據(jù)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表現(xiàn)所載內(nèi)容的形式。”其實(shí)質(zhì)上賦予了電子合同與傳統(tǒng)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
《勞動合同法》與《合同法》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guān)系,在特別法沒有規(guī)定的情況下,應(yīng)適用普通法的規(guī)定,勞動合同的書面形式應(yīng)包括數(shù)據(jù)電文形式。雙方簽訂的電子勞動合同其內(nèi)容符合《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應(yīng)同其他采用傳統(tǒng)書面形式合同書一樣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黑龍江大慶市:王景龍
遭遇工傷后,原工資福利待遇可享受多久?
半年前,我因一起職業(yè)傷害事故導(dǎo)致左手殘疾。從醫(yī)院出院后,公司即以效益不好為由只發(fā)給我基本生活費(fèi)。我認(rèn)為明顯不合情理,我應(yīng)該享受原來的工資福利待遇不變,但不知具體該享受多長時間?
讀者:李偉蒙
李偉蒙同志: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第4篇
[關(guān)鍵詞] 會計監(jiān)管 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 協(xié)調(diào)
《會計法》是會計工作的根本大法,《會計法》與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之間存在著不協(xié)調(diào)處,下面通過梳理《會計法》與上位法、同位法、下位法及自身的關(guān)系,找了不協(xié)調(diào)之處,以便進(jìn)一步完善會計監(jiān)管法律法規(guī)。
一、《會計法》與上位法的協(xié)調(diào)
《會計法》的立法依據(jù)是憲法,因此,其立法程序與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與憲法的相關(guān)條款相銜接,如表1所示。如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改革的過程中,明晰和保護(hù)產(chǎn)權(quán)問題已經(jīng)成為我國憲法制定和修改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導(dǎo)向,作為維護(hù)、保障財產(chǎn)所有者和投資者權(quán)益最具體、最具針對性的處于控制層面的法律制度的《會計法》,理應(yīng)對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理念在一般法律層次上相應(yīng)落實(shí)。因此,它應(yīng)以《憲法》為依據(jù),適時對相關(guān)提法進(jìn)行修正和補(bǔ)充,以便對其屬下相關(guān)會計法律規(guī)范的制訂與修改起到指導(dǎo)作用。
二、《會計法》與同位法之間的協(xié)調(diào)
1.《會計法》與《刑法》的協(xié)調(diào)。從法理角度看《會計法》與《刑法》之間在涉及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等執(zhí)法與司法問題及民事賠償責(zé)任的確定上,《刑法》特別法,屬優(yōu)先遵循層次;而在如何認(rèn)定是否觸犯刑法、民法及其他法律及處罰程度、賠償金額的大小等方面,這些法規(guī)必然以專業(yè)性強(qiáng)的《會計法》等相應(yīng)條款為基礎(chǔ)。如表2所示,《會計法》與《刑法》出現(xiàn)的對“單位負(fù)責(zé)人”表述不協(xié)調(diào)處,應(yīng)遵循特別法優(yōu)先于普通法的原則,對《會計法》進(jìn)行修改,使單位負(fù)責(zé)人表述與《刑法》一致。
2.《會計法》與《稅法》、《公司法》、《證券法》的協(xié)調(diào)。按照法理學(xué)中所貫徹的特殊法優(yōu)先普通法的原則,這一層級的協(xié)調(diào)主要是在具體條款的制定與問題處理上,分清普通法與特殊法的相對性問題,而其銜接則體現(xiàn)為條款應(yīng)當(dāng)相對具體與一致,《會計法》的相應(yīng)條款應(yīng)當(dāng)為同一層級關(guān)系密切的其他法律規(guī)范提供法律判斷標(biāo)準(zhǔn)方面的會計專業(yè)技術(shù)支持。如表3所示出現(xiàn)的不協(xié)調(diào)部分,應(yīng)確定會計法的母法地位,會計法為其他法律規(guī)范提供會計專業(yè)支持,使其他法律規(guī)范相關(guān)條款與《會計法》相一致。
三、同位法之間的協(xié)調(diào)
《注冊會計師法》強(qiáng)調(diào)注冊會計師的工作程序,如果程序合法,即使審計結(jié)果與事實(shí)有出入,注冊會計師也不一定要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而《公司法》則強(qiáng)調(diào)工作結(jié)果,只要審計報告與反映事實(shí)不符,出具的審計報告有重大失實(shí),造成嚴(yán)重后果,注冊會計師就應(yīng)對此承擔(dān)責(zé)任。如表4所示出現(xiàn)的不協(xié)調(diào)處,可實(shí)行責(zé)任倒置制度,即審計報告即使有重大失實(shí),但注冊會計師舉證自己無過錯的除外,可以不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
四、《會計法》與下位法的協(xié)調(diào)
《會計法》作為規(guī)范會計行為的基本法,相關(guān)條款應(yīng)當(dāng)具有全面性和原則性,但現(xiàn)行《會計法》規(guī)范的內(nèi)容基本上是局限于財務(wù)會計領(lǐng)域,沒有涉及到管理會計和其他相關(guān)會計領(lǐng)域,其所規(guī)范的“會計行為”也更多地限定于一種狹義上的單位內(nèi)部財務(wù)會計行為,較少涉及到與單位會計行為有著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會計事務(wù)管理行為。如表5、表6所示出現(xiàn)的不協(xié)調(diào)處,《會計法》作為《會計基礎(chǔ)工作規(guī)范》、《總會計師條例》的上階法律,對于一些原則性規(guī)定應(yīng)統(tǒng)一以《會計法》相關(guān)提法為主,而對于會計行為的實(shí)務(wù)操作性規(guī)定,應(yīng)統(tǒng)一用行政法規(guī)的條款來約定。
五、《會計法》與《行政處罰法》的協(xié)調(diào)
如表7所示《會計法》與《行政處罰法》的不協(xié)調(diào)處,應(yīng)建立統(tǒng)一的會計監(jiān)管標(biāo)準(zhǔn),遵循“一事不再罰”原則,協(xié)調(diào)各監(jiān)管部門的監(jiān)管規(guī)范;考慮建立會計責(zé)任解除制度,使會計監(jiān)管對象克服由于執(zhí)法行為的多元性造成的監(jiān)管成本加大問題。
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第5篇
【關(guān)鍵詞】歸責(zé);過錯責(zé)任;無過錯責(zé)任
1.歸責(zé)原則的含義
歸責(zé)也叫法律責(zé)任的歸結(jié),它是指由特定的國家機(jī)關(guān)、國家授權(quán)的機(jī)關(guān)依法對行為人的法律責(zé)任進(jìn)行判斷和確認(rèn)的活動;歸責(zé)是對法律責(zé)任的認(rèn)定和歸結(jié),具體包括判斷、認(rèn)定、追究、歸結(jié)以及減輕和免除法律責(zé)任的活動,是一個復(fù)雜的責(zé)任判斷過程。在我國,歸責(zé)的原則主要可以概括為:責(zé)任法定、公正原則、效益原則和合理性原則。但侵權(quán)行為法上的歸責(zé)原則,是指在損害事實(shí)已經(jīng)發(fā)生之后,為確定侵權(quán)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是否需要承擔(dān)民事賠償責(zé)任的原則。正如王利明教授指出的那樣:“侵權(quán)法的歸責(zé)原則,實(shí)際上是歸責(zé)的歸責(zé),它是確定行為人的侵權(quán)民事責(zé)任的根據(jù)和標(biāo)準(zhǔn),也是貫徹于整個侵權(quán)行為法之中,并對各個侵權(quán)法規(guī)范起著統(tǒng)帥作用的立法指導(dǎo)方針。一定的歸責(zé)原則直接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階級的侵權(quán)立法政策,同時又集中表現(xiàn)了侵權(quán)法的規(guī)范功能。”
2.英美法系國家的歸責(zé)原則
2.1 英國
英國關(guān)于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采取的是普通法上的過錯責(zé)任原則與機(jī)動車強(qiáng)制責(zé)任保險相結(jié)合的形式。十九世紀(jì)七八十年代,英國學(xué)者就提出,受害人或其財產(chǎn)因加害人高速公路上的行為遭到損害,如果加害人沒有過錯,那么受害人就不能獲得任何賠償。這種觀點(diǎn)的理論基礎(chǔ)是自愿風(fēng)險承擔(dān)理論,即高速公路上的人或?qū)⒇斘镏糜诟咚俟返娜司妥栽赋袚?dān)了不可避免的交通事故的風(fēng)險。雖然這種理論得到了廣泛傳播,但是該理論被很多人認(rèn)為是荒謬的。實(shí)際上,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交通事故采用了侵入理論,即原告必須承擔(dān)被告過錯的舉證責(zé)任。但是,隨著機(jī)動車的發(fā)展,在現(xiàn)代社會,對道路交通不適用無過錯責(zé)任原則的理論已經(jīng)逐步受到批評。后來試驗(yàn)表明過錯責(zé)任不足以解決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問題。強(qiáng)制責(zé)任保險制度實(shí)際上體現(xiàn)了在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中無過錯責(zé)任原則的確立。
英國的強(qiáng)制制度責(zé)任保險始于1930年。機(jī)動車保險不是基于機(jī)動車使用者的個人責(zé)任或替代責(zé)任。責(zé)任保險時機(jī)動車年度注冊的必要條件。英國1988年《道路交通法令》規(guī)定,沒有進(jìn)行責(zé)任保險的車輛不得在公路上或公共場合行駛,違反這一規(guī)定,機(jī)動車所有人可能被控告有罪;機(jī)動車保險范圍包括機(jī)動車所有人和經(jīng)其同意駕駛的人引起的事故;遭受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的機(jī)動車乘客和機(jī)動車以外的第三人都能獲得保險賠償。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國,機(jī)動車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可以就其遭受的全部責(zé)任獲得全部保險賠償。
2.2 美國
傳統(tǒng)的侵權(quán)法認(rèn)為,無過錯無責(zé)任,“責(zé)任是過失的必然結(jié)果”。這就是過錯責(zé)任的最直接表述。過錯責(zé)任是侵權(quán)法的基本原則。在美國,關(guān)于汽車事故損害賠償,采取的是普通法上的過錯原則與強(qiáng)制責(zé)任保險相結(jié)合的規(guī)范模型,逐步過渡到無過錯責(zé)任模式。
在美國,普通法上對于機(jī)動車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害必須以加害人的過錯為條件,即機(jī)動車交通事故的歸責(zé)原則是過錯責(zé)任原則。理由是,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機(jī)動車并不被認(rèn)為是危險的交通工具,它已經(jīng)受到完全的控制。事實(shí)上,傳統(tǒng)的侵權(quán)法從試圖對每一個受害的原告進(jìn)行賠償,它的主要作用是將多少有些無辜的原告的損失轉(zhuǎn)移到被告身上,因?yàn)?侵權(quán)法為了確定被告的過錯以及原告是否有權(quán)獲得賠償需要一種相當(dāng)復(fù)雜精細(xì)的司法程序。但是,一直有人主張,交通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成本應(yīng)當(dāng)由投入到此項(xiàng)活動中的所有人來承擔(dān)。許多人主張放棄把被告的過錯作為賠償原告的必要條件的做法,從而也就消除了經(jīng)過這種復(fù)雜精細(xì)的司法程序來確定被告是否存在過錯的必要。
隨著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數(shù)字直線上升,受害者得不到補(bǔ)償?shù)膯栴}空前尖銳起來。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普通法的過錯原則遠(yuǎn)遠(yuǎn)不足以保護(hù)當(dāng)事人利益,要求建立無過錯賠償機(jī)制。現(xiàn)在,美國許多州已經(jīng)采取強(qiáng)制責(zé)任保險制度作為從過錯責(zé)任到無過錯責(zé)任的一種轉(zhuǎn)變機(jī)制。
3.大陸法系國家的歸責(zé)原則
3.1 德國
德國人最早發(fā)明汽車,對于汽車所引起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可其獨(dú)特的嚴(yán)禁思維、深邃的法理思想率先立法確立無過錯責(zé)任原則,各國的無過錯責(zé)任均起源于德國的《道路交通法》。在德國的機(jī)動車損害賠償?shù)牧⒎ㄊ飞?最早由Kard Hilse教授于1899年的德國柏林提出以特別法的形式規(guī)定機(jī)動車損害賠償問題,從而強(qiáng)化機(jī)動車保有者責(zé)任。1906年有關(guān)當(dāng)局提出了《關(guān)于機(jī)動車運(yùn)行之際所生損害的責(zé)任義務(wù)的法律草案》,而成為該法律草案之基礎(chǔ)的正是有關(guān)危險的企業(yè)應(yīng)負(fù)與過失無關(guān)系的損害賠償責(zé)任的立法思想。1909年,德國公布了《汽車交通法》,1952年德國聯(lián)邦頒布了《道路交通法》,其中第7條規(guī)定:“機(jī)動車駕駛過程中有人死亡、受傷或者損害他人的健康或財物時,由機(jī)動車所有者就其損害向受害人負(fù)賠償責(zé)任,如果事故是由不可避免的事件所引起,而這種不可避免的事件既不是因機(jī)動車故障,也不是操作失靈而引起,則不負(fù)責(zé)任。”1987年,又將該法第7條修改為嚴(yán)格責(zé)任(無過錯責(zé)任),規(guī)定車輛在駕駛中致人損害,由車輛所有人負(fù)賠償責(zé)任,但因受害人或第三人或動物引起的除外。按照該條規(guī)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責(zé)任不依車輛所有人或駕駛?cè)艘环接羞^錯為要件,所有人或駕駛?cè)艘环接羞^錯為要件,所有人或駕駛?cè)艘环揭膊荒芡ㄟ^證明自己無過錯而獲免責(zé),因而屬于無過錯責(zé)任。但此無過錯責(zé)任并非結(jié)果責(zé)任,法律明文規(guī)定以“不可避免的事件”為免責(zé)事由,被告如能證明自己一方已盡高度注意義務(wù),且這樣“不可避免的事件”非車輛機(jī)能障礙或操作失靈所致,而是由受害人或第三人的過錯或動物所引起,則可以免責(zé)。
3.2 法國
法國對機(jī)動車交通事故的處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才傾向于適用無過錯責(zé)任原則的。這應(yīng)追溯到法國法院對埃伊爾案的處理。1925年4月里的一天,被告萊斯、加里公司的一名雇員駕駛卡車撞倒了一名穿插馬路的名叫莉斯?讓?愛伊爾的女孩。愛伊爾的母親以她的名義在貝爾福民事法庭。初審法院適用民法典第1384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做出判決。但是被告貝藏松上訴,法院更改了這一判決。理由是:交通工具正在被使用,原告對于這種情況必須證明駕駛員的行為有過錯,應(yīng)使用民法典1382條的規(guī)定,并作出判決。最高法院撤銷了上訴法院的裁決,認(rèn)為民法典第1384條沒有區(qū)分兩種行為造成的損害,該條文只涉及物件本身的危險性已經(jīng)對他物造成的損害并需要控制的物件。案件幾經(jīng)反復(fù),最后由最高法院做出判決。自這一判決后,民法典第1384條第一款適用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害就沒有疑問了。從此,法國的機(jī)動車交通事故領(lǐng)域的無過錯責(zé)任就確立起來了。
到了60年代,由于過失相抵歸責(zé)的廣泛運(yùn)用,受害人一方的“過失”成為減少賠償金的共同原因,從而導(dǎo)致裁判的不一致和不公正。最高上訴法院表述了有利于受害人的見解,從使用無過錯責(zé)任的訴訟中排除了過失相抵歸責(zé)。但在刑事附帶民事提起的賠償訴訟中,因適用過錯責(zé)任原則,過失相抵規(guī)則仍然有效,這就導(dǎo)致審判實(shí)踐中出現(xiàn)更大的混亂。為了消除這種不公正和嚴(yán)重混亂。1985年7月5日,議會通過了《改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地位并加速賠償程序法》。按照本法,受害人的地位得到相當(dāng)改善,其主要內(nèi)容有:(1)不可抗力事件和第三人行為不得作為免責(zé)理由;(2)如果受害人是行人和騎自行車人,不得適用過失相抵規(guī)則;(3)唯一免責(zé)事由是受害人犯了“不可原諒的過錯并構(gòu)成事故唯一原因”,如果受害人未滿16歲或在70歲以上,或持有永久性殘疾程度在80%以上的證明,即使屬于“不可原諒的過錯并構(gòu)成事故唯一原因”,也應(yīng)獲得全額賠償,除非受害人是自殺;(4)在責(zé)任成立要件中,用牽連關(guān)系取代因果關(guān)系。值得注意的是,《改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地位并加速賠償程序法》只調(diào)整真正意義的交通事故,借助于機(jī)動車輛故意加害案件不屬于正真意義上的事故。
3.3 日本
在《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制定之前,日本對機(jī)動車事故損害問題,是依照日本民法典債權(quán)關(guān)于侵權(quán)行為的一般歸責(zé)原則對本民法典債權(quán)編關(guān)于侵權(quán)行為的一般歸責(zé)原則(第709條和第715條)加以解決。20世紀(jì)以來,隨著機(jī)動車事故的普遍出現(xiàn),并且呈日益嚴(yán)重的趨勢,日本民法典關(guān)于一般侵權(quán)行為歸責(zé)原則規(guī)定,已經(jīng)不足以事先對機(jī)動車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利益的保護(hù)。為了使機(jī)動車事故的受害人獲得充分的救濟(jì),為了機(jī)動車事業(yè)的健全發(fā)展,有必要制定一部特別法對民法的一般規(guī)定加以補(bǔ)充和修正。
1955年7月,日本公布了《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對機(jī)動車人身事故的損害賠償作了如下規(guī)定:
首先,對于機(jī)動車事故,可以分為物件損害和人身損害。如果屬于單純的無物件損害,仍然依照日本民法典第709條過錯責(zé)任原則進(jìn)行賠償。對于機(jī)動車事故人身損害,根據(jù)危險責(zé)任和報償責(zé)任原理,規(guī)定了機(jī)動車人身事故的無過錯責(zé)任原則。《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3條是該法最重要的規(guī)定,該條規(guī)定了損害賠償責(zé)任主體、損害賠償責(zé)任成立要件以及免責(zé)要件等法成立的若干基礎(chǔ)性問題。依據(jù)該法,受害人要使加害人承擔(dān)機(jī)動車損失賠償原則,只需證明:(1)加害人具有機(jī)動車運(yùn)行供用人的資格;(2)損害是由于機(jī)動車運(yùn)行發(fā)生的;(3)必須是損害了“他人”的生命和身體,無須證明被告存在過錯。同時依該法,因機(jī)動車事故的所有者、使用者等對機(jī)動車的運(yùn)行有支配力因而享有運(yùn)行利益的人。如果此機(jī)動車的運(yùn)行供應(yīng)者,不能證明下述三項(xiàng)事由時將不能免責(zé);(1)自己及駕駛者對于之運(yùn)行并未怠于注意;(2)受害人或駕駛?cè)艘酝庵谌擞泄室饣蜻^失;(3)并無構(gòu)造上的缺陷或機(jī)能上的障礙。從而實(shí)現(xiàn)了舉證責(zé)任的轉(zhuǎn)換。“由于其相當(dāng)嚴(yán)格,加害人企圖通過證明自己有免責(zé)條款之情事而獲免責(zé),顯然非常困難”。
日本《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的制定,著重參考了德國的《道路交通法》,其第3條與德國《道路交通法》第7條便是一脈相承,只是在免責(zé)事由上,如本法未將動物的原因計算在內(nèi)。可見,日本法與德國法相比,責(zé)任更重,亦是一種無過錯責(zé)任。日本的運(yùn)行供用者責(zé)任的判定是從運(yùn)行支配與運(yùn)行利益兩項(xiàng)基準(zhǔn)上加以把握的,此二基準(zhǔn)的實(shí)質(zhì)是源于危險責(zé)任與報償責(zé)任。而危險責(zé)任思想及報償責(zé)任理論,正是各國對汽車事故損害賠償采取無過錯責(zé)任原則的重要根據(jù)所(下轉(zhuǎn)第56頁)(上接第51頁)在。基于以上分析可得:現(xiàn)行日本《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3條的運(yùn)行供用者責(zé)任,無論在形式上或?qū)嵸|(zhì)上均屬于無過錯責(zé)任。
其次,以法律形式制定了機(jī)動車人身事故賠償?shù)谋U洗胧?即強(qiáng)制保險和政府的損害賠償保障事業(yè)。強(qiáng)制保險制度規(guī)定,所供運(yùn)行之用的機(jī)動車均在締結(jié)責(zé)任保險合同的前提下方可使用;保險公司負(fù)有締結(jié)機(jī)動車損害賠償責(zé)任保險合同的義務(wù);政府對機(jī)動車損害賠償責(zé)任保險以60%的比例給與再保險。同時,確立了對于由于附保義務(wù)違反者、肇事后逃逸者所造成的人身損害由國家的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險保障事業(yè)予以補(bǔ)償。由此可見,日本通過國家機(jī)動車損害賠償保障事業(yè)進(jìn)一步深入實(shí)施無過錯責(zé)任原則,盡力保證每個受害者得到賠償。
4.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歸責(zé)原則之共性
人類在19世紀(jì)末發(fā)明了汽車,進(jìn)入了汽車時代,隨之發(fā)生了道路交通事故致人傷亡的嚴(yán)重社會問題。雖然英、美、日、德、法各國對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采用何種歸責(zé)原則,經(jīng)歷了不同的階段和發(fā)展過程,但是,如今各國均對其致人損害采用了無過錯責(zé)任原則。在德國等大陸法國家,由于在這些國家制定民法典之時,機(jī)動車尚未存在或者機(jī)動車事故還很少,許多民法典都未對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適用何種歸責(zé)原則做出規(guī)定。在這個時期,機(jī)動車交通事故一般被視為普通侵權(quán)行為,按照一般過程原則處理。
隨著機(jī)動車交通事故的不斷發(fā)生,各國都逐漸認(rèn)識到機(jī)動車交通事故的特殊性,也發(fā)現(xiàn)一般過程原則并不足以保護(hù)機(jī)動車受害人的利益。德國、法國和日本都先后制定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shù)奶貏e法,規(guī)定對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適用無過錯責(zé)任原則,即不論機(jī)動車所有人或者駕駛?cè)酥饔^有無過錯,只要其加害行為導(dǎo)致他人人身或財產(chǎn)遭受損害,就要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除非有法定的免責(zé)事由。在英、美、法國家,由于其傳統(tǒng)侵權(quán)理論“無過錯責(zé)任”的影響,英、美兩國至今仍然在普通法上,對機(jī)動車交通事故損害適用無過錯責(zé)任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英美法國家對機(jī)動車事故中的受害人保護(hù)力度較大陸法系國家要弱。相反,英美法國家普遍實(shí)行的機(jī)動車責(zé)任強(qiáng)制保險制定,在客觀上實(shí)現(xiàn)了無過錯責(zé)任所要達(dá)到的法律效果,受害人的利益同樣得到了有效的保護(hù)。機(jī)動車責(zé)任保險實(shí)際上是以保險制度為一種中間步驟,在道路交通事故領(lǐng)域逐漸向無過錯責(zé)任制度演變。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