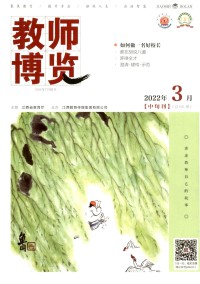教師課程改革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教師課程改革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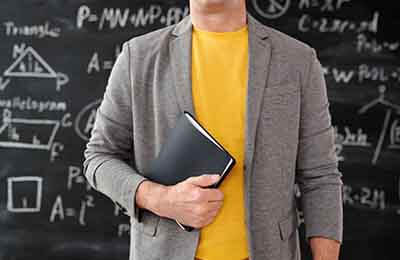
1.全社會氤氳著一種不合理的教師觀在日常生活和學術討論中,相對于教師觀,我們關注更多的是學生觀,并經過艱苦的“去蔽”過程,將學生從類似于“容器”般物的隱喻回歸到生命的本質屬性上來。事實上,教師觀也亟需一個“去蔽”的過程,甚至這一需要要比學生觀迫切百倍。因為遮蔽在教師頭上的霧氣依舊彌漫的情況下,學生的天空不可能一片晴天。也許有人會心生疑問,教師一直被社會賦予“園丁”、“蠟燭”、“春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等美譽,何談不合理的教師觀呢?在筆者看來,這些所謂的美譽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遮蔽教師本真的固見,教師已然成為家長期望子女成龍成鳳、教育主管部門完成教育規劃、學校提高升學率、專家實施教育理念的工具,充斥耳際的都是為了學生的進步、為了學校的發展、為了提高教學的有效性,要求“教師應該怎么去做”,并且教師所做的因為美譽所彰顯的“無私”、“奉獻”、“犧牲”等偉大精神而被視為理應如此,從而絕少去主動征詢教師“您認為可以怎么去做”。比如,在課程改革的浪潮中,雖然以激發教師參與課程改革內生動力為初衷舉辦了多種形式的教師培訓活動,然而很多教師培訓卻變成了“領導的訓話會”、“模式的宣講會”、“專家的成果展示會”,既沒有在培訓前對將要接受培訓的教師進行前期調研,來明晰他們教學生活中所面對的實際問題,也沒有在培訓的過程中給出一些空間來供教師表達看法,更沒有在培訓之后對培訓內容的后續影響作跟蹤式調查。教師在氤氳著“視教師為工具”的教師觀的社會里,在來自多方面的種種“指令”和“要求”下疲于應付,在自我定位上很難將自己視為課程改革的真正主體,而只是被動地去做課程改革忠實的“執行者”和“服從者”,自然對于課程改革的前因后果、理念的內蘊精神、綱要標準的內容解讀沒有探究的興趣和意愿,因為這些事情在他們看來并不是自己“份內”的事。
2.教師心懷“恐懼”地參與課程改革對于教師的恐懼,美國教育家帕克·帕爾默(ParkerJ.Palmer)曾指出,“當我們(指教師)試圖把我們自己及學科與學生相聯系時,我們會使得我們自己,還有學科,都容易受到漠視、評判、嘲諷的傷害”,“為了減少我們易受到的傷害,我們與學科分離,與學生分離,甚至與我們自己分離。”正是由于心懷恐懼,教學實踐中人與人之間構筑成一個相互防范的網絡,就此筆者曾撰文指出,“在這樣的網絡里,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無法獲取充分的空間可以真正地發揮自主性,在這個網絡里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往往也是不準確的。”回到第一部分的案例中去,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該教師在我們聽課時會選擇自己駕馭不了的組織辯論的教學方式?為什么不去講教材中的內容?為什么聽課的同事在評課時不涉及教學中所存在的任何問題?因為我們作為研究者和顯在或潛在的評價者進入教學實踐的場域之后,成為了教師的提防對象,他們認為最安全的做法是將自己真實的想法深藏,使自己的教學行為起碼在形式上符合當前流行的外在評價標準,而在意見表達時始終與集體意見保持一致。曾有一位教師敞開心扉地對筆者說,“現在家長向課堂教學要學生的成績,領導向課堂教學要改革的成績,研究者向課堂教學要理念實施的成績,于是,我們不得不準備給家長聽的課、給領導聽的課、給專家聽的課等多種課型。”在這種境況下,教師分身乏術,有時甚至顧此失彼,這也許就是帕克·帕爾默所說的“自我保護”性的自我與實踐的分裂。當教師不愿或不敢在自我的教學實踐中展現“我的教學觀”、“我的教學智慧”,而封閉自我的心靈與思維時,其參與課程改革的內生動力之火也就隨之熄滅了。
二、教師參與課程改革內生動力培育的途徑
1.以生命的視角來認識教師無論是將教師推上“神壇”成為身具美德、肩負特別責任的“圣人”,還是將教師拉下“神壇”成為實現特定目的的“工具”,都漠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教師既不是無所不能的神人,也不是只具有新陳代謝功能的軀體,他(她)是具有個性化的知識、能力、愛好、情感、價值觀以及家庭的生命的存在。全社會只有理性地去看待教師,將教師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員,教師才能夠從外部強加的種種桎梏中解脫出來,尋回本真的自我,并縫合課堂教學中的“我”與日常生活中的“我”的裂縫,敢于也愿意在課程改革中表達“我的意見”、“我的看法”。也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夠改變過去“跪著教書”的姿態,以一個整體的人的姿態站立于社會之中,心懷一份教學的信念和自我完善的追求投入到課程改革的實踐中去,而這一點是單純依靠增加財政撥款、優化教學設施、重新編制課程等措施所無法實現的。
2.以“和而不同”的方法論來推進課程改革“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國本土生長的方法論,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這里,“和”并不等于“整齊劃一”,而是一種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那種隱藏自我觀點所形成的單調的、僵化的“同”是被批判的對象。為此,“和而不同”方法論的要點在于容“不同”方能達到“和”的境界。需要指出的是,“和而不同”的方法論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并不是孤立的,它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以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等主張是相呼應的,即這里的“和”并不是通過“強施”達成的和,“不同”也不是偏執而達成的刻意的異。我們知道,課堂教學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中間充斥著教師與學生之間、教與學之間、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之間所形成的種種關系,這是任何一種所謂的“理念”和“模式”都無法按照統一的方案來解決的,它需要充分發揮教師的教學智慧來適時應對。這也意味著“理念”和“模式”所能發揮作用的層面主要在觀念引導層面,而具體的課堂教學實施層面則需要教師在內化“理念”和“模式”內蘊精神的基礎上,依據自身特點和教學實際來自主設計合適的教學方式策略,并根據實施效果對已有的“理念”和“模式”進行反思、批判以及改造。當課程改革為教師們構建不同風格的課堂教學提供充分空間的時候,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內生動力也便被激發出來,一種五彩繽紛、繁榮向上的改革局面才能夠得以實現。
3.以專業發展為目的構建教師成長共同體日本教育家佐藤學(ManabuSato)認為,“學校這樣一個場所,即便外面如何采取改革的措施,內部倘若不同時改革,也會是無動于衷的保守的場所”,“而學校內部的改革能否實現,取決于教師們能否構筑起將彼此的實踐相互公開、相互批評、合作創造的關系。”構建以專業發展為旨歸的教師成長共同體便是構筑起這一關系的重要體現。在我國的學校管理體系中,一直存在著學科教研組的組織,它為教師群體開展合作活動搭建了平臺,這些活動包括集體備課、集體聽課等,但其活動的聚焦點大多集中在某一節課怎么樣,而非教師的專業成長上。為此,活動的話語權大多為骨干教師所掌握,其他教師多為被動參與,從思想上將同事間的合作視為一種形式大于內容的活動方式。針對這一現象,佐藤學指出“如果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打開教室的大門,并且從內部徹底粉碎這種權力關系,那么,學校的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也就是說,對于學校里的課程改革來說,只有教師個體的投入是不夠的,它需要的是教師群體的全身心投入。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將教師間的合作活動由甄選意義上的結果性評價功能轉變為發展意義上的過程性評價功能,去除教師在參與合作活動時封閉自我的盔甲,使教師群體作為協同發展的成長共同體來參與學校的課程改革。總之,對于課程改革來說,能否形成有益于培育教師內生動力的土壤,并將這一動力很好地激發出來,是影響到改革成敗的關鍵。而這一點并不能僅存于認識層面,它需要全社會每一個關心課程改革的人,尤其是與之密切相關的教師、教育主管人員、家長、專家學者等群體的共同努力,并且這也將是一項長期的不僅在課堂教學中還要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落實的工作。
作者:齊軍 李文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