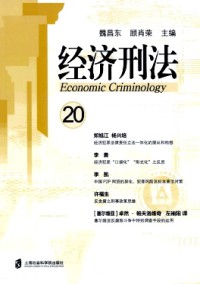刑法搶劫罪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刑法搶劫罪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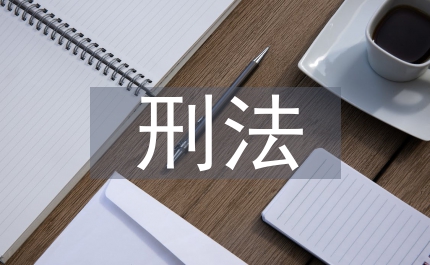
【內容提要】準搶劫罪的結構實際是一個預備性質的違法行為和搶奪行為的結合,而以搶劫罪的實質判斷,其行為結構應當是具有威脅性的行為和搶奪行為的結合,以相當性原則衡量,“攜帶兇器”盜竊、詐騙的行為也應當以搶劫罪論處,但以立法價值衡量,準搶劫罪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為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行為應當構成犯罪的觀點,既不符合無罪推定原則,又不恰當地束縛了偵查權、檢察權的行使,同時剝奪了被害人或第三人的絕對防衛權,與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也不相符;隨附暴力強度較大……
一、搶劫罪與搶奪罪之相互關系
搶劫罪和搶奪罪在司法實踐中具有相當高的發案率,是近幾年來司法機關重點打擊的對象。由于立法所固有的高度抽象性不可能一一對應實踐中搶奪犯罪的具體情形,同時有關立法也確實存在一定問題,這就為司法機關正確區分搶奪罪和搶劫罪的界限以及正確處理其他一些相關問題增加了難度。因此,認真研究這兩種犯罪的區別與聯系,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實踐價值。基于此認識,刑法學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兩罪之聯系
分析行為結構,可以發現,搶奪罪和搶劫罪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
1.準搶劫罪(注:筆者采用此概念。辛科稱之為推定的搶劫罪,肖中華等學者稱之為轉化型搶劫罪,而韓偉、劉樹德把典型的轉化型搶劫罪稱之為準搶劫罪。可見學界對轉化犯的認識尚未取得一致。)。這是指攜帶兇器搶奪的行為。其行為結構,實際上是一個預備性質的違法行為和一個搶奪行為的結合。這種預備性質的行為,實質上只是一種違法行為,即違反有關刀具管制的治安管理法律的行為。由于這一行為的存在,搶奪行為就變成了搶劫罪。
2.轉化型搶劫罪。這是指在盜竊、詐騙、搶奪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其行為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先行的搶奪行為和后續的暴力性行為(暴力以及暴力脅迫行為)的結合。其中的暴力行為,一般來說是搶劫的手段行為,在特定情況下也可能是一種同“取財”這一實行行為密不可分的行為。
3.隨附暴力強度較大的搶奪行為。比如搶奪女性耳環時撕裂被害人耳朵;搶奪女性坤包時強力拖拽倒在地上的被害人;飛車搶奪他人致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等。由于搶奪行為伴隨的暴力程度比較明顯,其行為性質究竟是搶奪還是搶劫,就有不同意見。這種爭論,反過來說明了兩種犯罪之間的聯系。
4.兩種犯罪都是財產犯罪,同類客體或者說法益一樣,直接客體也具有一致性:都侵犯公民的財產權益;犯罪目的都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變他人所有為自己所有;犯罪對象都是動產(注:也有人主張搶劫罪的對象可以是不動產。理由是:搶劫罪侵犯的是財產所有權之占有權能,不動產因具有占有權能而可能被非法占有,對不動產之非法掌握和控制可以當場實現,因此不動產可以成為搶劫罪的對象。);犯罪主體都是一般主體。
(二)兩罪之區別
泛泛而論,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性手段當場劫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搶奪罪是指乘人不備、公然奪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兩罪的區別主要是:直接客體不盡相同。搶劫罪的犯罪客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犯公民財產權,同時也侵犯公民人身權。而搶奪罪只侵犯公民財產權;犯罪主體不盡相同。搶劫的罪的主體可以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而搶奪罪的主體必須年滿16周歲(以上)。這是通說。
問題是,通說也就是從概念到犯罪構成——實質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推論。這種推論采用的邏輯演繹方法本身沒有錯誤,但產生推理前提的歸納方法本身具有難以窮盡子項的缺陷,因此,已經有學者對搶奪罪的概念提出質疑,對搶劫罪中的“其他方法”提出不同意見。
有學者認為,“乘人不備”不應當是搶奪罪的行為表現或者說必要要件,因為大量搶奪行為發生在被害人“有備之時”,比如把公文包緊緊抱在懷里,把挎包置于胸前,甚至帶保鏢護衛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實際上是“乘人有備”而實行搶奪。[1]筆者在進一步研究中發現,有的搶奪行為既不當眾進行,也不當著被害人的面(簡稱“當面”)進行,而是選擇僻靜無人的場合進行。有時是當面進行,有時是乘人不備時進行,因此,一方面,“乘人不備”不應當是搶奪罪的必要要件;另一方面,“公然”也不一定是搶奪罪的行為特征,只有聚眾哄搶罪中的搶奪行為才是“公然”進行的。因為在通說中,“公然”一詞有雙重含義,一是指當眾,即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二是指當面進行。[2](注:在王作富教授主編的書中,作者陳志軍的觀點是:除當場外,公然的含義是“被害人能當即發現”,并認為后一含義正是搶奪罪的行為特點。筆者不以為然,因為搶劫罪、盜竊罪都存在“被害人能當即發現”的情形。)在屈學武女士研究公然犯罪的專著中,“公然”指明目張膽、無所顧忌地公開其事[3]“公開其事”,可以推定其表現即公開進行或當面進行,而不是偷偷摸摸進行。不過,屈女士認為,搶奪罪等公然犯罪,“不僅有其肆無忌憚、無所顧忌地實施犯罪行為的主觀特征,還應有其公開在公共場合犯罪或直面不特定人、多數人犯罪的客觀性征。[3](P21)從這一解釋來看,她所認為的“公然”進行主要是指當眾進行。然而,從搶奪犯罪現象的發案實際來看,無論是在當眾進行時,還是在當面進行時,都可能乘人有備或者乘人不備;反過來,乘人有備或者乘人不備搶奪時,也可能不當面或不當眾進行。也就是說,搶奪罪的情形非常復雜,可以有多種排列組合:1.當眾而乘人不備;2.當眾而乘人有備;3.當眾并且當面而乘人不備;4.當眾并且當面而乘人有備;5.當面而乘人不備;6.當面而乘人有備;7.既不當眾、也不當面但乘人有備(背后下手);8.既不當眾、也不當面但乘人不備(背后下手)。這就說明,有“乘人不備”和“公然”的限制,搶奪罪的法條規定就不能涵蓋以上情形,通說關于搶奪罪的定義就犯了“子項不周延”的邏輯錯誤。反過來,邏輯上不周延,就意味著“乘人不備”和“公然”的限制的不合理。所以,筆者主張,在搶奪罪概念中,既應取消“乘人不備”的限制,也應取消“公然”的限制。事實上,刑法典第267條本身沒有這些限制,通說作出的定義,實質上構成對法律規定的限制解釋,而這種限制將不恰當地給根據法律規定已經構成犯罪的被告人帶來無罪辯解的理由和獲得無罪宣告的快樂。
那么,應該如何定義搶奪罪呢?筆者認為,搶奪行為不同于搶劫、盜竊和詐騙行為之處在于兩點:一是行為的性質是“奪取”。“奪取”行為與竊取行為相比,具有一定的野蠻屬性;與搶劫行為相比,這種野蠻性較弱,不具有強制性。二是行為表現為“突然性”,即一般來說被害人還來不及反應,搶奪行為就已實施完畢。當然,僅有“突然性”表征不足以區分搶奪和搶劫,也不足以區分搶奪和盜竊,因為有時搶劫罪或者盜竊罪的被害人也來不及反應,搶劫行為或者盜竊行為就已實施完畢。泛泛地說,在都具有“突然性”的情況下,搶奪、搶劫行為的區分,在于行為的“突然性”和“強制性”的結合。突然性的奪取而不是強制取得,屬于搶奪;突然性的強制取得而不是奪取,屬于搶劫。這一點對于區分隨附性暴力行為的性質非常重要。而搶奪、盜竊行為的區分,在于突然性奪取。突然奪取,屬于搶奪;秘密而突然取得或者說使被害人失去財物,屬于盜竊。嚴格地說,它們的“突然性”是有區別的。搶劫、搶奪行為的“突然性”是強制性行為和奪取行為本身的屬性,而盜竊行為的“突然性”不是其行為本身的屬性,而是被害人自己單純的感受;從被害人的反應來看,搶奪行為的突然性,會使被害人當即“大吃一驚”;而盜竊行為本身不具有突然性,被害人感受到的突然性是在意外發現有人正在盜竊或者財物已經不翼而飛之后,距離行為人的盜竊行為有或長或短的時間間隔。因此,搶奪罪的概念可以表述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突然奪取他人較大(以上)數額財物的行為。
一般認為,根據確立標準的“相當性”原則,搶劫罪中的“其他方法”應當是指在暴力、脅迫以外,同暴力、脅迫方法相當的、足以使被害人不敢或不能抗拒從而交出財物或者聽任行為人拿走財物的方法。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對“勸醉而取財”是否符合相當性原則,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勸醉而取財”與“灌醉而取財”不同。在“勸醉而取財”的情形中,雖然行為人具有使被勸人(被害人)醉酒的故意,但被害人自己不僅沒有人身權益遭到侵犯的感受,也沒有現實的人身侵犯以及人身侵犯的可能——僅僅是接受勸說大量飲酒而已,對自己可能的醉酒狀態持明知且放任的態度(這一點根本區別于藥物麻醉方法),行為人只是在被害人自陷于醉酒狀態的前提下實施了秘密竊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在“灌醉而取財”情形中,不僅行為人具有灌醉被害人的故意,而且被害人是在不愿意喝醉的情況下被強行灌醉的,“灌醉”已經具有“暴力”意義。因此,將“勸醉而取財”的行為歸屬于采用秘密方法的盜竊罪更為恰當。[4]這種觀點產生的背景,固然有從理論刑法角度來看不夠妥當之處——究竟是否應當把“其他方法”作為搶劫罪的手段確實值得商榷,但從應用刑法角度來看,這種觀點本身未免使人納悶:我們究竟應當站在什么角度、立場分析犯罪構成?在某些犯罪中,固然需要考慮被害人感受,比如強奸罪中被害人意志的違反問題,但一切犯罪的構成,都必須分析行為人的主觀罪過,這是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在上述情形中,行為人為什么“勸酒”,就決定著其取財行為的性質。基于活躍氣氛等善意,乘被害人醉酒而取財,當然屬于盜竊;基于取人錢財的惡意,將“勸酒”作為實施取財行為的手段,乘被害人醉酒而取財,當然屬于搶劫。不加區別地談論“勸酒”和“灌酒”的區別,難免有文字游戲的嫌疑。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說“我把某某人灌醉了”時,一般都是指勸酒過多而導致他人醉了,決不是說“我強行使他喝醉了”。
區分搶劫罪和搶奪罪,泛泛而談是不夠的。從邏輯上講,事物與事物之間有聯系就意味著有區別,正是因為有聯系,事物之間才有必要加以區別,也才有區別的可能。準搶劫罪與搶奪罪有區別嗎?這似乎是學界尚未注意的問題。如果我們堅信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性,對此問題就必然得出肯定結論。那么,它們具有什么區別呢?怎樣區別呢?筆者認為,區別二者的關鍵在于正確認定“準搶劫罪”。有人認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既然刑法典已經明確規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那么,只要行為人在搶奪時攜帶了兇器,就應當認定為搶劫。[5]這種認識明顯違背主客觀一致原則的精神,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機械理解。因此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6]現在看來,批評意見已成通說,然而通說并未被司法機關采納。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2]18號)第6條仍然規定:“攜帶兇器進行搶奪”,是指行為人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的行為。甚至把這一規定擴大解釋為“為了實施穩固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行為”。當然,筆者并不認為這種解釋是對司法解釋權的科學而正當的使用。在“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的情形中,這一行為的結構包括兩種情況:預備性質的違法行為(實質上是行政違法行為)與搶奪行為的結合;威脅行為與搶奪行為的結合。前一結構中的“預備”行為目的指向不明,可能是為了自衛,可能是為了生產、生活或者工作,也可能是為了違法犯罪,最終行為的性質,應當由實際實施的實行行為決定。既然行為人實際實施的是搶奪行為,那么就應當認定為搶奪。有學者指出:在這種情形中,如果行為人既未打算在搶奪時使用其所攜帶的兇器,被害人往往也不知道行為人隨身攜帶有兇器,那么從主客觀方面看,行為人攜帶兇器的事實談不上會對他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這就同搶劫罪既侵犯財產又侵犯人身的構成特征不盡吻合,因而不宜認定為搶劫罪。[7]這種解釋無疑是合情合理的。后一結構中的“攜帶兇器”行為,應當理解為一種消極的使用兇器行為,這種行為具有一定的威脅色彩,能構成對被害人反抗心理的抑制,本質上屬于其他強制性手段,所以這種結構中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劫罪。在“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情形中,“為了實施犯罪”本身含義不夠明確。攜帶兇器為了到甲地傷害某丙,路過乙地時順便搶奪了某丁,也是“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兇器進行搶奪”,能夠認定為搶劫罪嗎?顯然不能。聯系這句話的前后意思理解,筆者認為,這里講的“為了犯罪”,是指為了犯搶奪罪和搶劫罪,其行為結構是:1.搶奪預備行為與搶奪實行行為結合。認定這種情況下的行為為搶奪罪,應該不會引起爭議。2.搶劫預備行為與搶奪實行行為結合。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實際上實施了搶劫預備行為,但在行為發展過程中,行為人實際上是在搶奪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實行了搶奪行為,行為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變化后的主客觀要件的統一,決定了應當認定其行為性質為搶奪罪。3.搶劫預備行為和威脅性行為與搶奪實行行為的結合。即行為人攜帶兇器就是準備根據現場情況決定是否使用兇器,實際上實施的是一種不明顯的威脅行為,比如有意向被害人示意自己帶有兇器,或者有意讓被害人發現自己帶有兇器,其實質是為了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其性質屬于其他強制性手段,故應認定為搶劫罪。綜上,只有后一種結構的行為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特征。而按照司法解釋的字面含義,在上述三種結構的行為中,行為人沒有顯示所攜帶的兇器都構成搶劫罪,甚至有學者主張在以上兩種攜帶兇器的情形中,“均必須是行為人在搶奪時沒有顯示、使用其所攜帶的器械才能成立“搶劫罪”。[7]這可能離搶劫罪的構成特征有較大距離,它或許是對該司法解釋的正確解讀,但該司法解釋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懷疑了。畢竟不是為了搶奪或搶劫而攜帶所謂“兇器”的行為,僅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憑借這一事實認定行為人犯有搶劫罪,與我們所批判的“客觀歸罪”恐怕只有零的距離。
學者們分析該規定時,幾乎都以對兇器內涵與外延的分析為進路,從研究方法上講,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有的學者沒有能夠準確把握兇器和生產、生活用具之間的辯證關系,因而未能準確定義兇器的內涵甚至根本沒有作出定義。例如,有人認為,兇器是指殺傷力較大,能夠使人產生畏懼心理的器械,如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菜刀、水果刀等;[8]有的人認為:“所謂兇器,常見的有匕首、折疊刀、三棱刮刀等。”[9]少數學者正確指出:兇器,只能是指槍支、彈藥、爆炸物、管制刀具等明顯可以用以殺傷人體的器械,以及通常用途不在于人身,但行為人將其使用明顯意在作為搶奪后盾的物件,如菜刀、啤酒瓶、茶杯、小水果刀甚至鋼筆等。[10]應當肯定,兇器的外延是十分廣泛的,它們與人們的生產生活甚至學習具有密切關系,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一看見這些東西出現在犯罪現場或者犯罪嫌疑人身上,就說它們是兇器。正如王作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樣:“無論任何器具或工具,只有用于行兇時,才能叫兇器。換句話說,無論任何器具或工具,只要被人用于行兇傷人、殺人就成為兇器。”[11]在論證什么情況下,攜帶兇器進行搶奪的行為才能認定為搶劫罪時,個別學者則指出這一規定的不當性,主張廢除之。[12]廢除說的主要理由是:搶奪罪與搶劫罪的根本區別在于手段的不同,而不在于條件的不同。攜帶兇器搶奪,只要行為人沒有使用兇器實施暴力、脅迫等強制人身行為,就與一般的搶奪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刑法典第263條對搶劫罪的規定已經包含了“攜帶兇器搶奪”的內容;[10]這一規定違背了犯罪構成理論的要求,不符合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帶有類推制度的影子,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攜帶”、“兇器”含義模糊,與盜竊、詐騙行為轉化為搶劫罪的前提條件不統一——既然攜帶兇器搶奪的行為可以轉化為搶劫罪,攜帶兇器進行詐騙、盜竊的為什么又不能轉化為搶劫罪呢?[12]筆者認為廢除說是合理的。不過,我們不可能把立法的不當之處完全寄希望于立法的修改,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加以彌補和完善的,應當盡量爭取解釋的途徑。因為立法的成本是高昂的,也是有限的。筆者認為,萬變不離其宗,對于準搶劫罪的認定,應當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緊緊把握搶劫罪的實質,即不論何種手段的使用,都必須是為了使被害人不敢抗拒或者不能抗拒。如果行為人身上攜帶的兇器根本不為被害人所知,或者行為人并不是欲使身上攜帶的器具或者工具成為兇器,則不能把“攜帶兇器”搶奪的行為認定為搶劫罪。
在轉化型搶劫罪中,搶劫罪與搶奪罪的區別,同準搶劫罪與搶奪罪的區別有一個共同點,即在這兩種情形中,搶奪罪的主體是已滿16周歲的人,而搶劫罪的主體是已滿14周歲的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共同點是:構成搶奪罪有數額的限制,而準搶劫罪也好,轉化型搶劫罪也好,都沒有數額的要求,除非“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都應當作為犯罪處理。
對于隨附暴力強度較大的搶奪行為,前述司法解釋沒有明確。但對于“利用行駛的機動車輛搶奪的”情形,該解釋要求“以搶奪罪從重處罰”。筆者認為這值得進一步研究,不宜一刀切。如果行為人應當預見到自己的強力拖拽行為會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結果,但疏于預見的,對造成輕傷結果的搶奪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奪罪;對造成重傷以上結果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數罪,以結果牽連犯或者想象競合犯原理處理(注:學界對于適用何種原理尚有爭議。筆者認為結果牽連說與想象競合犯以及吸收犯難于區分,故主張牽連犯只應具有手段牽連一種形式。)。如果適用想象競合犯原理,則按其中的重罪即搶奪罪從重處罰;如果適用牽連犯原理,則按其中的重罪即搶奪罪論處。
二、暴力含義辨析
作為搶劫罪與搶奪罪相聯系、使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的橋梁,“暴力”具有突出的作用,自然也就進入了所有研究搶劫罪的學者的視野。對于暴力的含義,學界存在不同認識。
有學者立足于整個暴力犯罪的角度,主張把暴力分為三層:(一)廣義的暴力。即非法實施有形物理力的所有類型(包括威脅使用的暴力)。其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可以針對被害人本人,也可以針對在場的其他人。暴力的內容,可包括從一般的毆打、輕微傷害到最嚴重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這種最廣義的暴力,不以達到直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為判斷的標準。(二)狹義的暴力。是指對人身施加有形物理力,即不包括對物體實施的有形力;暴力的程度,也不要求對人身造成一定的傷害結果,但應具有比較強的對人身的強制性,而且不排除造成傷害、死亡的可能性。(三)最狹義的暴力。同樣是指對人身施加的有形物理力,不包括對物體實施。但暴力的程度強于狹義的暴力,通常情況下,具有達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但實際上是否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不影響犯罪的成立。該學者同時認為,搶劫罪中的暴力方法,是指對于被害人的人身實施的打擊或強制,目的是為了排除或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以便當即奪取(或者迫使其交出)財物。暴力程度的下限,不要求達到危及人身健康、生命或迫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程度。因為行為人實施暴力的意圖在于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能力和勇氣,當暴力以此為目的,并針對財物持有者的身體實施,就應當認定是本罪的暴力手段。其認定的標準不在于是否能夠對人身造成傷害或危及生命,而在于是否能夠抑制被害人保護財物實際可能。只要剝奪被害人保護自己財物的實際可能的,就應當認為屬于本罪的暴力。而暴力的上限,不應包括故意殺人手段。[13]還有學者認為,暴力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法律特征——暴力在刑法上的法律意義是指刑法分則明文規定的一種犯罪手段;(二)行為特征——暴力是指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等權利的強暴行為;(三)主觀特征——行為人實施暴力行為的時候是故意,并且具有明確的目的。[14]筆者認為,作為暴力犯罪的核心概念,暴力一詞在不同的犯罪中都應當具有一致性,不應當因罪名的不同而不同,否則罪刑法定就會搖擺不定。暴力之首要含義是強制性力量;其次是物理性強制力而不是化學性破壞力(注:利用化學物質損傷人體的結果,仍然屬于物理性結果,因此這種損傷力仍然屬于物理性強制力。)再次,這種強制力具有足以使一般被害人產生畏懼心理從而不敢抗拒或者足以使一般被害人不能抗拒的作用。如果這幾點不致于導致反對意見的話,暴力就應當是指直接作用于人體或物體的、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物理性的強制力量。問題是,何以判斷“足以抑制”?筆者認為,完全根據被害人的感受或者完全脫離被害人的感受而僅僅根據行為人的認識來建立標準,都是不夠合理的。合理的標準,應當比較全面地考慮暴力行為施加和被施加者雙方的認識,在行為的動態關系中,以行為人實施這種強制力的目的為基礎,結合一般被害人的感受來判斷。至于“一般被害人”究竟是指一般同類人還是“一般理性人”,似乎值得進一步研究。筆者之所以主張考慮行為的動態關系,是基于現實的需要:在伴隨暴力結果的搶奪案件中,比如利用行駛的機動車輛搶奪騎自行車的人車上或者身上的箱包,由于雙方都處于運動過程中,慣性力很容易導致被害人跌倒摔傷甚至造成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的后果。行為人駕駛的車輛速度越快,致傷力就越大,一概把“利用行駛的機動車”這種手段排除在“暴力”之外,或者作出相反的判斷,恐怕都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這種隨附性暴力與典型的搶劫罪中的暴力確實有幾點不同:它和取財行為合二為一成為一個整體;它直接作用的對象是財物而不是人身;行為人實施這種特殊的暴力時對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不一定是故意。如果行為人明知這種危險手段足以造成被害人摔倒甚至受傷的結果仍然實施,客觀上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以認定為搶劫罪比較合理;如果行為人在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的情況下造成了這樣的結果,以認定為搶奪罪比較合理。此外,筆者之所以主張以一般被害人的反應作為建立標準的依據,除了公平性(機會公平或者說分配公平)的考慮外,主要考慮了標準的客觀性問題。如果具體到個案中的被害人,是否“足以抑制反抗”就很難說得清楚了。且不說在典型的搶奪罪案件中有的被害人不敢抗拒,就是在一般扒竊案件中或者一般入室盜竊案件中,都有一些被害人不敢吱聲的,難道我們能把這樣的案件認定為搶劫案件嗎?
三、兩罪之間及其與正當防衛之動態關系
在轉化型搶劫罪中,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作為前提行為的搶奪或者盜竊、詐騙行為是否應當構成犯罪?對此,有人持肯定的態度,理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15]。筆者認為,這種觀點貌似符合罪刑法定,但不僅在理論上與罪刑法定原則在訴訟程序上必然要求的“無罪推定原則”沖突,而且在實踐中以極為苛刻的條件排除了被害人或第三人實施絕對的正當防衛的可能。首先,行為人有罪無罪,必須由法院裁決。在法院裁決之前,不僅被害人或第三人不能實施絕對的防衛,而且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事實上也不敢輕易指控嫌疑人觸犯了搶劫罪。特別是在行為人搶奪、詐騙、盜竊未遂的情況下,偵查、檢察機關更是束手無策,而轉化型搶劫罪恰恰主要發生在上述行為未遂的場合,這樣,刑法典的這一規定就被虛置了。其次,如果要求前提行為構成犯罪,那么,對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來說,不僅他們無權進行“絕對的防衛”,就是普通的防衛也難以采取——特別是在暴力強度不大、暴力威脅不明顯的情況下。因為刑法典第20條規定的絕對防衛,只能針對包括搶劫在內的暴力“犯罪”實行。如果前提行為無罪,就意味著轉化犯不能成立也就不構成搶劫罪,被害人或第三人不能對行為人實行絕對防衛當然就是必然的結論,既然如此,“調動社會力量打擊犯罪”的立法初衷就會落空。顯然,對于搶奪轉化為搶劫的前提行為,不能解釋為必須構成搶奪罪。立法上所作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表述,應當解釋為技術問題。同時,筆者認為,在轉化型搶劫中,在轉化事由行為(即后發的暴力或暴力威脅行為)出現前,被害人或者第三人只有普通防衛權,在轉化事由出現之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享有絕對防衛權。同理,在攜帶兇器的搶奪中,在行為人示意帶有兇器,或者被害人、第三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之前,被害人或第三人只有普通防衛權,而在行為人示意帶有兇器,或者被害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之后,被害人或第三人享有絕對防衛權,暴力或者暴力威脅以及其他強制性行為的開始時刻就是防衛的開始時刻,但暴力或者暴力威脅以及其他強制性行為的結束時刻不是防衛的結束時刻,因為已經轉化形成的搶劫行為作為一個整體并未結束,換言之,行為人還沒有逃離現場,或者被搶財物還沒有完全脫離被害人的監控范圍。
再次,搶劫罪的構成本身沒有數額要求,根據法釋2002[18]號司法解釋,搶奪500元至2000元以上財物的,才構成搶奪罪。此時,若轉化為搶劫罪處理,數額懸殊過大。從邏輯上講,搶奪也可能表現為入室搶奪,入室搶奪當然有可能轉化為入室搶劫。典型的入戶搶劫,可能行為人只搶到10元錢,但面臨的法定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轉化型的搶劫罪中的入戶搶劫,則必須在行為人搶到500—2000元時,才面臨同樣的刑罰,這是否公平?難道說轉化型搶劫罪中的暴力危害小于典型搶劫罪中的暴力,所以要“數額”來彌補嗎?難道說典型的搶劫罪的行為結構(先有暴力性手段、后有取財行為)與轉化型搶劫罪的行為結構(先有取財行為、后有暴力性手段)有所不同,就會導致行為危害程度不同從而需要其他情節來說明搶劫罪構成要件的符合性嗎?難道數額又有這樣的功能嗎?筆者認為,這兩種搶劫罪行為結構的差別,僅僅是形式的差別,其實質完全一樣,沒有什么不同,也不應當認為有什么不同,它們都是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結合,都從統一一致的主客觀方面揭示了搶劫罪既劫人錢財又侵害人身的構成特征。再其次,兩種搶劫罪的既未遂標準又該怎樣建立,也是一個問題。顯然,轉化型搶劫罪既然以數額犯為基礎,當然其既未遂的標準就應當以是否實際占有他人財物為依據,而典型搶劫罪的既未遂標準雖然在理論上有爭議,但在實踐中一般并不以占有財物與否為標準。如此一來,同樣是搶劫罪,卻作出不同的既未遂標準。這樣做,真的那么理直氣壯嗎?最后,在準搶劫罪中,在行為人示意自己帶有兇器或被害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前,是否要求其搶奪行為構成犯罪?從立法精神和司法判例來看,回答是否定的。這也說明,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行為,不應以構成犯罪為限。道理并不復雜:準搶劫罪中,由于行為人沒有采用暴力,“攜帶兇器”行為的威脅色彩也不濃厚,所以其危害明顯弱于使用了暴力或暴力威脅的轉化型搶劫罪。危害輕者尚且不必構成犯罪即可變成搶劫罪,危害重者更不必構成犯罪即可變成搶劫罪。
在準搶劫罪中,有兩個問題值得研究。其一是“攜帶兇器盜竊”的行為是否可能轉化為搶劫罪?其二是“攜帶兇器詐騙”的行為是否可能轉化為搶劫罪?對這兩個問題,司法解釋都沒有明確的規定。筆者認為,答案應當是肯定的。首先,根據“相當性原則”,暴力威脅手段與其他強制手段本身所起作用相同,盜竊和搶奪的性質相近(注:正因為如此,國外立法一般把搶奪作為盜竊罪的表現形式。)[16]其次,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在盜竊,尤其是在入室盜竊時攜帶器具(包括作案工具)的情形并不少見,這類行為的危害程度比起“攜帶兇器搶奪”行為的危害不相上下,比如,攜帶兇器搶奪的野蠻性并不見得就重于攜帶兇器入室盜竊的危險性;攜帶兇器當眾扒竊的危害也不見得輕于攜帶兇器在僻靜之處搶奪的危害。在作案金額都達不到犯罪起點的情況下,前者轉化為搶劫,后者卻不構成犯罪:對于前者,被害人或第三人可以進行絕對防衛,對于后者,他們卻只能進行普通防衛,這在道理上說不過去。合理的解釋應當是:在筆者理解的“攜帶兇器”的意義上,無論行為人攜帶兇器搶奪還是盜竊,被害人或者第三人都有權進行絕對防衛,并且這種防衛權存在于行為人“示意”帶有兇器或被害人以及第三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之時起,到整個不法侵害結束時止的整個過程。
“攜帶兇器詐騙”的行為似乎不像攜帶兇器搶奪那樣明顯具備搶劫罪的構成特征,其實不然。因為行為人攜帶兇器向詐騙行為的被害人示意或者被害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所產生的畏懼心理,同詐騙罪被害人“自愿交出錢財”的心理是矛盾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取得財物,已經不是靠被害人的自愿交付,而是被害人的被迫服從。因此,攜帶兇器詐騙的行為也應當規定為搶劫罪。但是,如果被害人發現行為人帶有所謂的“兇器”時并沒有產生畏懼心理,而是基于對行為人的信任拿出錢財,這種形式上攜帶“兇器”詐騙的行為,實質上仍然是詐騙行為,不發生向搶劫罪的轉化問題。同時,詐騙行為不具有人身侵害性,不能成為防衛的事由,但對攜帶兇器的詐騙行為能否防衛?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筆者認為,在行為人攜帶兇器向詐騙行為的被害人示意或者被害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的情形中,其行為結構是強制性行為與取財行為的結合,被害人或者第三人有權采取絕對的防衛,防衛的開始時刻,即行為人的“示意”或被害人的“發現”時刻;在其他情形中,由于被害人根本就不知道行為人帶有“兇器”,不可能進行防衛。這一點也可反過來說明其他攜帶“兇器”詐騙的情形(純粹客觀的攜帶情形)不應認定為搶劫罪。同理,除行為人向被害人示意帶有兇器或者被害人發現行為人帶有兇器的搶奪或者盜竊的情形,其他“攜帶兇器”搶奪或者盜竊的情形,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可能進行絕對防衛,反過來也可說明把這些情形認定為搶劫罪的失當。
在隨附暴力的搶奪中,應當注意隨附暴力與奪取行為的相隨相伴性,以區別于實踐中發生的用某種器物突然阻礙被害人乘騎的自行車和摩托車、然后利用被害人注意力分散的時機奪取或者竊取其財物以及當被害人倒地后抓住財物不放、行為人強力拖拽被害人的情形。在這兩種情形中,雖然取財行為表現為搶奪或盜竊,但行為人用器物突然阻礙被害人乘騎的自行車和摩托車的行為以及強力拖拽行為實質上是一種暴力行為,其行為結構仍然是暴力手段與取財這一目的行為的結合,完全符合搶劫罪的構成特征,應當認定為搶劫罪。相應地,被害人以及第三人有權進行絕對的防衛,行為人取財行為的著手之機即防衛人可以防衛的開始時刻。同時,對隨附暴力的理解,應當注意這種暴力的來源是行為人本身。如果行為人只是利用車船剛剛啟動之機產生的客觀上存在的物理性力量進行搶奪,不存在行為人自己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強制性手段的問題,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特征,故應認定為搶奪性質。相應地,被害人或者第三人只能采取普通防衛,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本人往往會喪失防衛的時機。
【參考文獻】
[1]趙秉志.談談搶奪罪的認定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7,(2).曾粵興.認定搶奪罪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J].昆明檢察,2001,(2).
[2]趙秉志.中國刑法實用[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944.王作富.刑法實務研究[M].北京:方正出版社,2001.1151.
[3]屈學武.公然犯罪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9.
[4]馮亞東,劉鳳科.論搶劫罪客體要件之意義[C].高銘暄,馬克昌.刑法熱點疑難問題探討[上][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751—752.
[5]何秉松.刑法教科書[下][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916.
[6]王作富.搶劫罪研究[J].刑事司法指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張翼昆.攜帶兇器搶奪行為的正確認定[J].云南法學,2001,(2).;逄錦溫.搶劫罪司法認定中若干問題的探討[J].法學評論,2002,(1).;夏強.搶劫罪三題探微[J].當代法學,2001,(4).;羅朝暉.論轉化型搶劫罪[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2).;肖中華.論搶劫罪適用中的幾個問題[J].法律科學,1998,(5).;金愷.對攜帶兇器進行搶奪定搶劫罪的理解[J].人民檢察,1998,(3).;汪海燕.攜帶兇器搶奪以搶劫罪論處的幾個問題[J].人民司法,1999,(2).;茹士春.論攜帶兇器[J].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1,(4).
[8]羅朝暉.論轉化型搶劫罪[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2).
[9]汪海燕.攜帶兇器搶奪以搶劫罪論處的幾個問題[J].人民司法,1999,(2)
[10]肖中華.論搶劫罪適用中的幾個問題[J].法律科學,1998,(5).
[11]王作富.搶劫罪研究[J].刑事司法指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高銘暄.刑法專論[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32.
[12]辛科.論推定的搶劫罪及其廢除[J].政法論壇,2000,(3).
[13]林亞剛.暴力犯罪的內涵與外延[J].刑法熱點疑難問題探討[上][C].2002.746—753.
[14]邢曼嬡.試論我國刑法中的暴力手段[J].刑法熱點疑難問題探討[上][C].2002.757-758.
[15]游偉.刑法理論與司法問題研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478.劉明祥.事后搶劫問題比較研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2).
[16]郭澤強.我國刑法中的搶奪罪之合理性追問[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