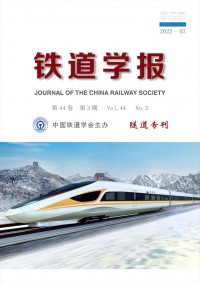道學性質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道學性質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哲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反思。人類,在其精神生活中經常遇到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有了矛盾,就有問題。其中有比較帶根本性或有比較帶普遍性的問題,就成為哲學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和體會以及解決,就是哲學的內容。其理解和體會可能有膚淺或深刻的差別,其解決可能有錯誤或正確的不同。所以哲學就分為許多“家”和“派”,這是不足為奇的。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一門科學也可以有不同的“家”和“派”,這一“家”和那一“家”,這一“派”和那一“派”有其共同之處,也有其不同之處。其共同之處在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相同的或類似的。其中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和體會,有深刻、膚淺的差別,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有正確和錯誤的不同。這些不同就是這一“家”或這一“派”的特點。道學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個最大的派別。它的特點是什么?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它的名稱是什么,應該是“道學”還是“理學”?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它的性質是什么?是哲學還是宗教?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先從第一個問題說起。道學是關于人的學問,它所要講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和自然的關系,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個人發展的前途和目的。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比較帶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問題。
中國哲學有一個很古的傳統說法:“人為萬物之靈”。這句話見于《書經·泰誓》。《泰誓》這一篇是偽古文,但是偽古文可能有所本。《禮記·禮運》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這也就是“人為萬物之靈”的意思。《禮運》出于西漢,“人為萬物之靈”的傳統說法,大概也不會晚于西漢。比較早的一位道學家周敦頤在他的《太極圖說》中,也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其秀”就是陰陽、五行之秀,“靈”就是“萬物之靈”那個“靈”。用一個“靈”字說明人類的特點,這是很中肯的。在古生物中,有的身體最大,有的力量最強。人在這些方面,跟它們比起來,相差太遠了。人的特點,就是比其余的生物都靈。靈就是聰明智力。有了聰明智力,他才能組織社會,發展科學藝術,創造自然界原來所沒有的東西。總而言之,他就能有精神生活,就能有對于精神生活的反思。這些都是靈的內容和效果。他為什么能夠這樣靈呢?就是因為他得到了陰陽、五行的秀氣。說到秀氣,似乎有點神秘。可是我們現在也說,人所以能有思想,是因為他有腦,而腦是發展到最高程度的物質。這也可以說是物質的秀氣吧。我并不是用現代唯物主義思想附會道學。多數的道學家就其整個系統說,是唯心主義的。但其是唯心主義的理由,別有所在。專就上面所引的幾句話還不能說是唯心主義的,但無論如何是說明了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和自然的關系。由此也說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中國哲學還有一個傳統的說法,就是把人和天地合稱為“三才”。《中庸》說,“可以與天地參矣”。“參”就是三,就是說人可以與天地并立而為三。我們現在知道,地和天不能相提并論,地不過是一個很渺小的天體,而人不過是地上的各種物類之一,所謂三才并立,是很可笑的。但古人認為天地是宇宙間兩個最大的東西,在天地中間,人的形體雖然很小,但是他的功用卻很大。三才并立并不是就形體方面說的,而是就精神方面說的。宋朝人有兩句詩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他這里是以仲尼為人類的代表。應該說:天若不生人,萬古長如夜。因為如果沒有人,就沒有上邊所說的那個靈,如果沒有那個靈,誰能理解自然界的規律?誰能創造自然界所本來沒有的東西?自然界就沒有自覺,這就好像在昏夜中睡覺,長此終古了。三才并立,是說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也是說明人和自然界的關系。中國古人所謂天地,就是泛指自然界。
中國哲學中還有一個傳統的說法:“究天人之際”。這個“天”,也是泛指自然界。“天人之際”,說的就是人和自然界的關系。“究天人之際”,就是說要搞清楚這個關系。天人并立,也是對于這種關系的一種說法。如果再追問下去,那就有這兩者之中的本末、輕重的問題。天人二者,哪個是本,哪個是末?哪個比較輕,哪個比較重?黑格爾認為,自然界是精神的異化。這就是以人為本,自然界為末。所謂異化,就是一個事物一分為二,自己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對立面,這個對立面是從自己分出去的,卻又成了自己的對立物(我在這里并不是注釋黑格爾,也不保證我這個說法就是黑格爾本來的意思,如果不是的,那就算我借用他的一個名詞吧)。既然是對立物,其間必有矛盾和斗爭,但畢竟是從自己分出去的,所以也必須有統一。如上面所說的,所引的那幾句話,在表面上看,是認為人是天的異化。《中庸》說,“天命之謂性”,那就是說,天是本,比較重,人是末,比較輕。還是如上邊所說的,無論說誰是誰的異化,都是要說明人和自然界的關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張載的《西銘》說的也是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由此推及人與宇宙中其他事物的關系。在這篇文章中,有兩個常見的代名詞,一個是“吾”,一個是“其”。“吾”就是我個人。“其”,就是天地或宇宙或乾坤。“吾”,是我個人,卻又不只是我個人。誰念這篇文章,那個“吾”就是他個人。無論是我還是他,如果了解了他是人類中的一個成員,也是宇宙的一個成員,他就看出來,或者感覺到,他的一舉一動都有宇宙的意義。例如,“尊高年”、“慈幼弱”,都不僅只是尊社會中的高年,慈社會中的幼弱,也不僅只是尊人類的高年,慈人類的幼弱,而簡直是尊宇宙的高年,慈宇宙的幼弱。圣人和賢人,不僅是社會中出類拔萃的人,也不僅只是人類中出類拔萃的人,而且簡直是宇宙的出類拔萃的人物。這就是那幾個“其”字的意思。照這樣推下去,個人的一舉一動,都有這樣的一層又一層的意義。宇宙是無限的,人生是有限的,一個個人如果有這樣的了解,他就是納無限于有限。有限的事總是做不完的。他活著一天,就盡力做一天的事。哪一天死了,他就可以休息。這就是《西銘》最后兩句話所說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寧,是休息。只有有上面所說的了解的人才可以覺得死是休息,因為他是納無限于有限,寓永恒于時間,死不過是休息。至于沒有這種了解的人,死了就是一切都結束了,一切都完了,說不上休息或不休息。
張載的這篇文章,講了人在宇宙間的地位,人與宇宙的關系,并把人具體到個人,由此推論到人在宇宙間應有的責任和義務,以及生死問題。一篇幾百字的文章,講了一部精神現象學。所以道學家們都極推崇這篇文章。程頤說,有了這篇文章,省了多少言語。
張載的這篇文章,也透露出了道學家所講的人的本質。所謂人的本質就是“人性”,人所以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規定性,照他們所說的,人的根本規定性是“仁”。
程顥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茍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這是二程的學生呂大臨所記的一條程顥的語錄,后來有人把它摘出來作為一篇文章,并為之加了一個題目:《識仁篇》。“渾然與物同體”,這是程顥對于宇宙、人生的理解。
道學家們認為,人和其他萬物都是從一個源頭來的。這個源頭就是“理”。從源頭上說,人和其他萬物本來都是渾然同體的。道學家們認為,學道學的人必須先知道這一點,“識得此理”,就是“識仁”。他們認為,道學并不僅只是一種知識,所以僅只“識得此理”還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實在達到這種精神境界,要真實感覺到自己實在是“與物同體”。這種境界叫做“仁”。達到這種精神境界的人叫做“仁人”,或“仁者”。
程顥比喻說:“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為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同上)既不屬己,不但空談“愛人”是假話,即使為自己的利益的目的而做些“愛人”之事,也不是真實的。程顥常說的“至誠惻怛之心”,即是真正的仁的表現,以至義、禮、智、信也都是仁的表現。
所以既“識得此理”,還要“以誠、敬存之”。“誠”是沒有虛假,用道學家的話說,就是“無妄”。“敬”就是心不分散,用道學家的話說,就是“主一”。“以誠、敬存之”,就是實實在在地注意于“渾然與物同體”這個道理。這就夠了,不需要防守自己,怕自己的行為有誤,也不需要再事追求,怕這個道理有錯。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既然“與物無對”,那就是絕對。這就是“絕對”這個名詞的確切意義。這并不是說程顥所說的“無對”與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有什么關系,只是說,這個名詞有這樣的意義。既然“我”真是覺得“渾然與物同體”了,所以“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這都是說的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的精神境界;這并不是說,自然界的現象如刮風,下雨之類,都是“我”所作所為,那就等于說“我”能呼風喚雨,顯然是不可能的。這種境界的哲學意義,就是取消主觀和客觀的界限,中國哲學稱為“合內外之道”。
照道學的要求,這個“合”不僅是知識上的事,需要反過來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有這種精神境界,是不是真正感覺到如此。如果真有這種境界,那就是“反身而誠”,那就可以有最大的快樂(“樂莫大焉”)。如其不然,僅只是在知識上認識到有這個道理,而實際上仍然覺得自己是自己,萬物是萬物,爾為爾,我為我,那么即使努力要求取消這種界限,那還只是“以己合彼,終未有之”,那也不能有樂。程顥指出,這種精神境界正是張載的《西銘》(《訂頑》)中所說的那種境界。
程顥又說:“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里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它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同上)這就是說,在源頭上說,人和萬物本來是一體的。但人既然是個人,他總得有個身體。就是所謂精神境界,也得有個身體,才能有所寄托。但是一個人,如果專顧到他的身體,那就是從軀殼上起念,那就是私。私把人的認識限制住了,所以不能認識“渾然與物同體”的道理。若要破除這個限制,需要把自己的身體,放在萬物中間,一例看待。打破了私的限制,人的眼界就擴大了,心胸就開闊了,這就何等的快活!這就可以感覺到“樂莫大焉”。
一個人如果能達到這種精神境界,那就是人性的復歸。人是從自然生出來的。他把自己局限于他自己身體的小范圍之內,成為自然的對立物,以自己的身體為內,以其他萬物為外,以自己的身體為己,以其他萬物為彼。這就是異化。如果達到上面所說的精神境界,那就是合內外,同彼己。這就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對立,取消了異化。取消了異化,就是人性的復歸。《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學講的是“率性”。這個性,不限于飲食男女等本能,但也包括這些本能。所以《中庸》下文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道學家也說,夫婦是人倫之始。道學家所講的道,是人人都能行的,而且人人都已經在行的。《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漢朝人喜歡用同音的字解釋某一個字,好像兩個字,如果音同,義也必然相同。這顯然是錯誤的,往往錯誤到很可笑的地步。但是“仁者,人也”這句話倒是有很深的意義。意思就是說,仁這種德,可以代表人的特點,作為人的規定性的主要內容,可以作為修身的標準。要行仁,就要從事親開始,因為親子的關系是最密切的,親子之愛也是最真摯的。要事親,必須要知人,這個知人,并不是一般的所謂“知人善任”那種知人,而是說對于人類必須有所了解。要想知人,必須知天,那就是說,要對于宇宙有所了解。張載的《西銘》恰好就是《中庸》這一段的發揮。這篇文章所講的,就是知天、知人、事親的道理。他又把事親的范圍擴大了,認為人的一切道德行為,都有這種擴大了的事親的意義。
道學以仁、義、禮、智為四德,而以仁為基本。看了程顥的《識仁篇》,可以知道仁為什么是最基本的。在《識仁篇》中,他也明確地說:“義、禮、智皆仁也。”后來的道學家們也都認為,分別起來看,仁是四德之一;但是合起來看,仁和義、禮、智并不是平行的。一個仁者,自然有義、禮、智,但是有義、禮、智的人,不一定就有仁,不一定就是個仁者。仁是四德的基本,而又包括了四德。仁是最基本的道德,也是最完全的人格的別名。從孔子到后來的道學家們,都是這樣說的。照上面所講的人性的復歸的道理,也就是應該這樣說。
在四德之中,義也是基本的,其重要性僅次于仁。在道學中,跟義相對立的概念是利。現在流行的了解,認為利是指物質的利益,道學重義輕利就是輕視物質利益,甚至反對物質利益。道學重義輕利,甚至反對利,這是真的,但這與物質利益沒有關系。道學注重義利之辨,這是真的,但義利之辨與物質利益沒有關系。道學認為,義利之辨就是公私之分。道學家們都是這樣說的。不管什么利益,不管它是物質的或精神的,只要你追求它是為自己個人打算,那就叫利;只要你追求它是為眾人打算,那就叫義。利之所以為利,在于私;義之所以為義,在于公。所以義利之別,在于公私之分。為公或為私,是為義或為利的惟一標準。比如說,一個資本家管理他的企業,精打細算,追求利潤,這是為利。因為他追求利潤,是為了他自己。一個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理,也要精打細算,追求利潤,但他的追求利潤,是為了增加人民的財富,這就不是為利,而是為義了。如果他不這樣做,使企業賠了錢,使人民受了損失,那就是不義。這個道理說穿了也很簡單。道學把義利之辨歸結為公私之分,只是說穿了這個簡單的道理,說了一句大實話。
道學家還反對所謂人欲,或稱為私欲。人既然是一個具體存在的人,他就必須有一個肉體。這個肉體,必須有所需要,如飲食男女之類。飲食,是肉體維持它自身存在的需要,男女是延續它的存在的需要。這些都可以稱為欲,也都是出于性。這都是無可非議的,無可反對的。但是專從自己的欲著想,就是程顥所說的專從自家軀殼上頭起意,這就成為人欲,也稱為私欲。其所以成為人欲,因為它是專從人的存在的物質基礎(軀殼)上起意;其所以稱為私欲,因為它是專從個人自己的軀殼上頭起意,所以它是私的,是應該反對的。凡是私的,都是應該反對的。比如說,人都要照例吃飯,餓的時候都想吃飯,這是無可非議的,也無可反對的。但是如果他吃的必須是山珍海味,或者只管自己吃飯而不讓別人吃飯,這就是人欲或私欲。人要結婚,這也是無可非議、無可反對的。但是如果必定要三妻六妾,那就是人欲或私欲,當然是應該非議、應當反對的。從公私之分看義利之辨,那就可以看出,義為什么是僅次于仁的基本道德。凡是大公無私的事,都是道德的事;凡是有私無公的事,都是不道德的事。
社會是人所創造的。人創造了社會,社會又成了人的對立面,特別從個人的觀點看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是人的異化。個人和社會的矛盾,都是從這種異化而起的。禮,是社會制度、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等,是對于個人的約束和限制,是個人和社會的矛盾的集中表現。
照道學家說,禮并不是對于個人的限制和束縛,而是個人的道德發展的條件,是個人完成他的完全人格的必由之路。《大學》所講的三綱領、八條目,就是個人完全人格的內容。這個內容,是以修身為主。在八條目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其目的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就是修身,是三綱領中的第一綱。但是,一個明明德的人,不能只明他自己的明德,他還要“明明德于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的內容。這在三綱領中叫親民,這是三綱領中的第二綱。就八條目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修身的作用。用道學所常用的范疇說,明德是體,親民是用。除此之外,還有什么事呢?沒有別的事了。若說有別的事,那也無非是把明德、親民推行到盡善盡美的地步,這就是至善,這是第三綱。
用另一番話說,修身是個人的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也都是個人的事。家、國和天下是社會,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社會的事。這兩種事,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是不可分離的。一個人如果只講個人的事,而不管社會的事,那就是有體無用。無用的體,不能算是完全發展的體。如果只講社會的事,不講個人的事,那就是有用無體。無體的用,等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個人的發展,必須是在社會中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必須依靠個人而發展。社會和個人融為一體,既不能分立,更不是對立。如果還用復歸那個名詞,可以說,這是社會的復歸。
由于這兩種復歸,人生中有兩種主要矛盾都克服了。沒有矛盾,就叫和。《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學家們認為這一段話只是講喜怒哀樂。其實可以不必加這樣的限制。這段話也可以理解為,借喜怒哀樂的矛盾作為宇宙間各種矛盾的一個例子。未發,就是各種矛盾的對立面還沒有發展成為沖突的那種情況。這種情況叫做中。中節,就是各種矛盾在發展中各自保持一定的限度,使之不至于與它的對立面相沖突。雖有矛盾,而其對立面都不發展到相沖突的情況,這就叫中和。中和、中節,能使宇宙間各種事物各得到它們應該有的地位而共同發展。《中庸》對于中和作了具體的說明,它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智,不是別的,就是對于仁、義、禮的理解和自覺。凡是一種道德,都是要在自覺中進行的。如果沒有一種與之相應的自覺,那就是本能,本能是各種動物都有的,而自覺是人這種動物才能有的,所以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特征。道學的中和的思想,是不現實的,特別對于社會來說是如此。社會中的主要矛盾都是有階級
根源的。人類社會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一個社會一分為二,分為剝削的統治的階級和被剝削的被統治的階級。這兩種階級的對立,是為各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的,不是人的主觀意識所能轉移的。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用代表全社會的名義,統治、剝削與之相對立的階級,形成了社會是人的異化的現象。社會的異化還是人造成的。像道學家所講的,社會和個人融為一體的思想,適足為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進行它的牧師的職能。道學之所以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其原因也是在于此。照它所講的,個人好像是社會的主人,其實是使他更深陷于奴隸的地位;好像是取消異化,其實是更加深了異化。
只有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沒有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中,個人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社會的復歸才能實現。道學家所說的那種中和,只是矛盾的均衡,均衡終究是要破裂的,和是不能靠中來維持的,就好像兩個超級大國的均衡,是不能靠限制武器來維持的,世界的永久和平也是不能靠這種均衡來達到的。
道學的基本特點大致如此。以下談第二個問題。
近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志中,有人認為道學這個名詞是“不科學的”,應該稱為理學。他們認為,道學這個名詞,出于《宋史·道學傳》,元朝修《宋史》的寫作班子,是脫脫領導的,他是一個武人,妄自制造道學這個名詞,不足為訓。事實是,《宋史》是元朝的一部官書并不是一部個人著作,像《史記》、《漢書》那樣。歷代的官書,都有一個編寫班子,班子的頭頭照例是一個朝廷大臣。這只是一個掛名的差使,書的編寫并不需要他親自指導,更不用說親自拿筆寫了。他是武人或不是武人,跟那部書并沒有關系,更重要的是,道學這個名稱,是宋朝本來就有的,修《宋史》的人不過是采用當時流行的名稱作《道學傳》,并不是他們自己妄自制造名目,立《道學傳》。現在且舉出幾條證據。
一、程頤說:“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志銘,且備異日史氏采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敘其事跡、述其道學者甚眾。”(《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載《程氏文集》卷十一)
二、程頤說:“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祭李端伯文》,同上)
三、程頤說:“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往,使予踽踽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祭朱公脄文》,同上)
四、朱熹說:“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然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論語集注·八佾》“管仲之器”章注引)
五、朱熹說:“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后,可謂盛矣。”(《程氏遺書》目錄跋)
六、陳亮說:“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學者也。”(《甲辰秋與朱元晦秘書(熹)書》,載《陳亮集》,第280頁,中華書局)
七、《慶元黨禁》說:“先是熙寧間,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丑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丑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為異,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叢書集成》本,第14頁,商務印書館)
八、《慶元黨禁》說:“慶元四年戊午(1198)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幸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愿下明詔,布告天下。’”(同上書,第17頁)
第一、二、三條可以證明,程氏弟兄已經自稱他們的學問為道學。第一條“其道學”的那個“其”字,指程顥。所以程顥死后,程頤他們私謚程顥為“明道先生”。這個“明道”之“道”即“道學”之“道”。第四條所說的楊氏,即楊時,是二程的大弟子,是把道學首先傳到南方的人。這一條可以證明,程氏的門人稱他們所學的是道學。朱熹在《論語集注》引楊時這一段話,可見他也是贊同道學這個名稱的。第一、二、三、四條證明,在北宋時期,道學這個名稱就有了,而且還是開創道學的幾個人自己用這個名稱的。第五條進一步證明,朱熹稱這派學問為道學。第六條證明,當時反對這派學問的人也稱之為道學。朱熹和陳亮都是南宋的人,這兩條可見在南宋時期這個名稱繼續流行。第七、八條出于《慶元黨禁》,這是一本于南宋淳五年(1245)寫成的書,可以證明,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政界,不僅私人,而且在官方,都使用道學這個名稱。
有同志說,在北宋時期,在上邊所引的那些史料中,所謂道學,應該是“道和學”,并不是一個學派的名稱。也許是這樣。上面所舉的那些證據中,第一條中的“道學”可能是道和學,“其道學”可能是指程顥的道和程顥的學。但其余各條中的道學,這樣理解似乎勉強。例如第二條說:“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似乎不好說是“我們兄弟倡明我們的道和我們的學”。這一點還可以進一步地討論,不過無論如何,道學這個名稱,至晚在南宋就已流行。這是沒有問題的。
再從哲學史的發展看,道學這個名稱有其歷史的淵源,韓愈作《原道》,提出了儒家的一個道統,照他的說法,儒家的道發源于堯舜,經過孔子傳于孟子,孟子死后這個道就失傳了。韓愈很客氣,沒有說他自己就是這個道統的繼承人。二程則毫不客氣地說,他們就是這個道統的繼承人。程頤說:“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明道先生墓表》,載《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就是繼承韓愈的說法,而自封為孟軻的繼承人。道學這個道,就是韓愈《原道》的那個道。從這點看,道學這個名稱可以說明一些哲學史發展的跡象。至于說到科學或不科學,一部寫出來的歷史書,只要跟歷史的真相相符合,那就是科學的,除此以外,無所謂科學不科學。至于《宋史·道學傳》中所收的人物有不少去取失當之處,那是由于編寫這個傳的人的門戶之見,與這個名稱沒有直接的關系。
近來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志們,有用理學這個名稱代替道學這個名稱的趨勢。理學這個名稱出現比較晚,大概出現在南宋。我們作歷史工作的人,要用一個名稱,最好是用出現最早的、當時的人習慣用的名稱。照這個標準說,還是用道學這個名稱比較合適。這也就是“名從主人”。而且用理學這個名稱還使人誤以為就是與心學相對的那種理學,引起混亂,不容易分別道學中的程朱和陸王兩派的同異。只有用道學才能概括理學和心學。
道學本來是一個學派的名稱,一個時代思潮的名稱,并不等于唯心主義。近來有一種趨勢,認為道學就是唯心主義的同義語。魏晉玄學,本來也是一個學派或一種思潮的名稱。也有一種趨勢,認為玄學就是唯心主義的同義語。我覺得這都是不適當的。道學家和玄學家中大部分都是唯心主義者,但不能認為道學和玄學就是唯心主義的同義語。這種認為,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辯論,可謂節外生枝。
自從清朝以來,道學和理學這兩個名稱,是互相通用的。現在還可以互相通用。研究哲學史的人可以各從其便,不必強求統一,但如果說道學這個名稱,是《宋史》的編造,不科學的,不能用的,這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了。
上面所說的道學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任繼愈同志的標準看,那就恰好證明,道學是一種宗教了(參看任繼愈同志的《儒家與儒教》,載《中國哲學》第3輯)。我認為任繼愈同志的標準以及他所用的論證,是值得商榷的。以下就轉入本文的第三個問題,即儒家是不是一個宗教。中國本來有儒。釋、道顯然是宗教,與之并駕齊驅、鼎立而三的儒家,似乎也一定是宗教了。這個論證,顯然是值得商榷的。中國本來所謂三教的那個教,指的是三種可以指導人生的思想體系,這個教字,與宗教這個名詞的意義不同。宗教這個名詞,是個譯文,有其自己的意義,不能在中文中看見一個有教字的東西就認為是宗教。如果那樣,教育豈不就等于宗教化了嗎?教育也是一個譯文,有其自己的意義,不能因為宗教和教育都有一個教字,就把它們等而同之。實際上也沒有人這樣做。
在封建社會中,宗教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說儒家是宗教。因為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筑,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是,上層建筑也分為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各有自己的特點,不能說上層建筑的一個部門,只因為它是上層建筑,就與其他部門沒有分別。
任繼愈同志倒也列舉出了一些宗教的特點,他說:“宗教都主張有一個精神世界或稱為天國、西方凈土;宗教都有教主、教義、教規、經典。隨著宗教的發展形成教派,在宗教內部還會產生橫逸旁出的邪說,謂之‘異端’。這種狀況,佛教、道教都具備。儒家則不講出世,不主張有一個來世的天國。這是人們通常指出的儒家不同于宗教的根據。”(《儒家與儒教》,載《中國哲學》第3輯,第7頁)在這些特點中,有些似乎不是宗教所特有的。宗教都有教主,任繼愈同志也承認教主必須具有半人半神的地位(同上書,第9頁)。這一點我同意。但是一個思想流派是不是也可以有其自己的思想體系,有其自己所根據的經典呢?每一個宗教都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其中分為許多流派,每個流派也都認為自己是正統。這也是事實。但是一個思想流派,是不是也可以有這種情況呢?我認為,這些都是可以有的。不能說,因為有這些情況,一個思想流派就是宗教。至于說到精神世界,那也是一種哲學所應該有的。不能說主張有精神世界的都一定是宗教。如果那樣說,古今中外的哲學流派的大多數都可以稱為宗教了。問題不在于講不講精神世界,而在于怎么講精神世界。如果認為所謂精神世界是一個具體的世界,存在于人的這個世界以外,那倒是可以說是宗教的特點。像基督教所說的天國,佛教所說的西方凈土,那倒是宗教的特點。但是道學所講的儒家思想,恰好不是這樣。道學不承認孔子是一個具有半人半神地位的教主,也不承認有一個存在于人的這個世界以外的、或是將要存在于未來的極樂世界。道學,反對這些宗教的特點,也就是不要這些特點,怎么倒反而成了宗教了呢?
任繼愈同志說:“宗教所宣揚的彼岸世界,只是人世間的幻想和歪曲的反映。有些宗教把彼岸世界說成僅只是一種主觀精神狀態。”(同上書,第7~8頁)我想,他在這里是把我們對于宗教的分析和宗教混為一談了。說宗教所說的彼岸世界只是人世間的幻想和歪曲的反映,這是我們的分析,宗教自己可不是這樣說的,如果它這樣說,它就不成其為宗教了。任繼愈同志在下文舉禪宗為例,這是不恰當的。
禪宗雖然“呵佛罵祖”,但是它的根本思想還是佛教的根本思想,那就是“超脫輪回”、“涅槃清凈”。就“形神關系”這個問題說,它還是主張神不滅論。涅槃就是超脫了輪回的“神”的一種狀況。從人的觀點看,它是一種精神世界,一種彼岸世界。這跟道學所說的精神境界不同。精神境界是依附于一個人的肉體的,一個人的肉體如果不存在,他的精神也就不存在了,他的精神境界也就不存在了。這是一種神滅論。禪宗所說的涅槃是超脫輪回了的神的狀況,一個人的肉體如果不存在了,他的超脫輪回了的神仍然存在,而且照禪宗說,存在得更好。這是一種神不滅論。所以道學和禪宗雖然在表面上有點相似,但在本質上是絕對不相同的。這個不同就是宗教和哲學的差別。
任繼愈同志說:宋明理學體系的建立,也就是中國的儒教的完成,它中間經過了漫長的過程。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義和崇奉的對象為“天地君親師”,其經典為儒家六經,教派及教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統論,有所謂十六字真傳,其宗教組織即中央的國學及地方的州學、府學、縣學,學官即儒教的專職神職人員。僧侶主義、禁欲主義、蒙昧主義,注重內心反省的宗教方法,敵視科學,輕視生產,這些中世紀經院哲學所具備的落后東西,儒教(唯心主義理學)也應有盡有。(《儒家與儒教》,載《中國哲學》第3輯,第9~10頁)這個辯論,好像有形式邏輯所謂“丐辭”的嫌疑。所謂丐辭,就是用所要證明的結論,作為前提,以證明那個結論。宗教必須有一個神,作為崇拜的對象;有一個教主,作為全教的首領,這是前提。這個論證,認為“天地君親師”就是儒教崇拜的對象,那就首先應該證明,“天地君親師”是神,孔子是個半神半人的人物,有這樣的性質,孔子有這樣的資格;不能首先肯定“天地君親師”有這樣的性質,孔子有這樣的資格,然后以這樣的肯定,證明儒教道學是宗教。在中國哲學史中,首先提出“天地君親師”作為“三本”的是荀子(見《荀子·禮論篇》)。荀況是中國哲學史中的最大的唯物主義者,他能把“天地君親師”說成是神嗎?“天地君親師”這五者之中,君親師顯然都是人,不是神。每一個人的親就是他的祖先,不是像基督教所說的耶和華。如果是耶和華,那么每個人不都成了耶穌了嗎?無論如何,在道學家中,有誰認真地討論過“天地君親師”呢?沒有調查,大概不是很多的。孔子的祖先世系,歷史資料中都有詳細的記載。他的子孫,一直到孔德成,孔氏的家譜中,也都有詳細的記載。無論后世的皇帝給他什么封號,他總是個人,沒有什么神秘,也沒有什么可以懷疑的地方。這樣的人能說是教主嗎?儒家所尊奉的五經四書,都有來源可考,并不是出于神的啟示,這樣的書,能說是宗教的經典嗎?這樣地一考證,如果說道學是宗教,那就是一無崇拜的神,二無教主,三無圣經的宗教,能有這樣的宗教嗎?如果說這也是宗教那恐怕就是名詞的濫用。至于說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的東西,道學都有,因此道學是宗教。這樣地推論,也是不符合邏輯的。在形式邏輯所講的直接推論中,不能把一個命題的主辭、客辭互相調換,由此得出新的結論。因為,在一個肯定命題中,客辭是不周延的。比如說,“凡人都是動物”,如果顛倒過來說,“凡動物都是人”,那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動物之中,包括有各種的動物,這些各種動物,除了有是動物這個大同之外,還有很多的小異。西方中世紀所有的宗教的東西,道學全有,這個命題是不是真的,還可以研究。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因此就說道學是宗教。
在中國歷史中,確有一個時期,其時的人,企圖把儒家變為宗教。那就是漢代,董仲舒等公羊春秋家以及緯書,確實是把先秦的儒家宗教化了。董仲舒所講的天,就是一個活靈活現的上帝,孔子受天命作《春秋》。有些緯書說孔子是黑帝之子,是一個半神半人的人物。照此說,儒家確實是宗教了,而這種說法,在當時就受到古文經學家的反對。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斗爭,在表面上說,是一種關于文字版本上的斗爭,實際上是一種宗教與反宗教的斗爭。東漢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都是古文經學家,都支持反宗教的斗爭,把宗教的氣焰壓下去了。可是從印度來了佛教,在中國也土生土長地建立了道教。于是又有了反對二氏的道學,這是中國歷史中的第二次反宗教斗爭。
任繼愈同志說:“有人不承認宋明理學是宗教,不承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是宗教,認為儒家有功,事實上它本身就是一種宗教。”(《儒家與儒教》,載《中國哲學》第3輯,第11頁注①)
我認為,不能把董仲舒和道學混為一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目的論是宗教,道學的反二氏是反宗教,所以道學的道統論中不列董仲舒,認為孟子死后,道學就失傳了。道學家也認為,董仲舒尊崇孔子有功,但是道學是從孟子繼續下來的。他們的褒貶是有分寸的。
在這次反宗教的斗爭中,道學勝利了,并被封建統治階級定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作為統治思想,它起了鞏固中國封建社會的作用,不然,它就不成其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了。從這一方面批判道學,那是應該的,也是可以的,但也不能抹殺道學的反宗教的作用而說它就是宗教。如果說它就是宗教,這就和中國的歷史、特別是哲學史的發展不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