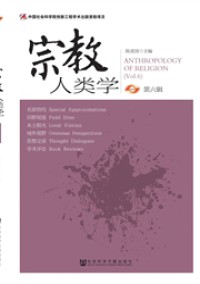人類學史教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人類學史教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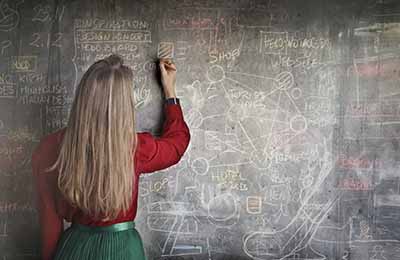
摘要:通過對《金翼》、《銀翅》的解讀,人類學對史學的啟示清晰可見:擴大了史料范圍,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加深了史學家的素養,同時舊史料與舊問題也會得到新的解讀。由于其研究眼光向下,使它與后現代視角有某些契合之處,這在史學的新近進展中有了明顯體現。
關鍵詞:人類學史學后現代
《金翼》、《銀翅》以閩南鄉鎮社會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相同,因而把兩書并列閱讀并觀察人類學的當代進展便是有意義的,尤其是人類學能給史學帶來什么更是不得不考慮的。這在當代“社會史”大潮的背景下,史學界不斷索尋史學出路時,其意義更加明顯!
一、兩書的人類學發現
林耀華先生師承吳文藻先生而被視為人類學研究中的北派,主張研究現代社會與原始社會并重,并以理論提升去追求人類學的中國化、本土化。《金翼》一書注描述當時福建漢人社會,其建樹清楚地可見當時結構功能理論的影響。因為它注意分析當時客觀的鄉村變化,并提出了“均衡論”的理論框架,這使其過于注重了社會穩定的一面,但是他也注意到了當時社會的沖突和變遷,如當時湖口鎮的崛起,辛亥革命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以及當時軍閥勢力與共產黨的入侵,以及基督教的傳入等一系列現象,同時注意到當時社會人倫關系的變化及家族內部的矛盾。這給當時西方人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于其成見的中國鄉村的畫面。與結構功能學派不同的是,該學派更多地關注社會的整合及其要素的功能,而林則是關注的個人人生及家庭的平衡及其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所引發的對命運的感嘆,因而其“均衡”帶有濃厚的文化意味。但就注重歷史文化變遷而言,它與南派并無多大差異,由此可見,同是研究人類社會學的南派與北派的差異可能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大。同時林似乎暗示著,如果因人世的無常引發了人的心理失衡,時間能抹平一切,但它沒有說明社會重新整合所通過的橋梁和機制,這些則要更多地會追溯和分析至制度層面。
林書所提及的兩位老者最后的命運是頗值得人感嘆的,但是書中無疑也沒能說清楚芬洲為何晚年會有與東林不同的命運,是其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化嗎?這個解釋似乎可信,但是如此籠統的解釋恐怕無法說明多少實質性的問題,因為其分析的工具和手段不夠深入,而且對于社會個體的解釋有時也很難去做社會學式的解釋,所謂社會學式的解釋是指迪爾海姆所提出的從社會事實中去尋找另一事實發生的原因。其解釋固然有科學和客觀的成分,但是面對個體的悲喜時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尤其是在面對命運感嘆之時,或許這時候拿金翼之家的風水去解釋問題更意味深長。這也正是閱讀時所應懷有的文化直覺。芬洲之家的衰落無疑與其人丁的衰落有很大的關系,其實東林家門五哥之死也給東林的生意造成了巨大影響的。東林所以讓孩子們接受西式教育更多的是因為其吃了官司的個人經歷,而不是其生活環境與芬洲有多少不同,或他有更多的遠見,此時我們不能不感嘆人生的轉機往往會出現于某一刻,甚至自己有時都沒來得及發現。
《銀翅》作者莊孔韶先生同樣也是頗有文化關懷的,其提倡的“不浪費”的人類學頗有意義,的確,只有用各種手段去保留我們行將隱去而又越發熱愛的文化時,我們才能說我們是在盡力保存著這一切。
《銀翅》的最后也提出了一種人類學理論的構架,可能由于師承的原因,他提出了“新均衡論”與“類蛛網式結構”,類蛛網式社會結構比起“竹竿和橡皮帶的構架”無疑是復雜和精細多了。竹竿橡皮網是在說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平衡與失衡關系,而“類蛛網式結構”則是指地方社會的運作及各種因素在其間的作用,而且這個網絡會因為新的因素不斷參與而改變各要素之間的作用力,應該說《銀翅》和《金翼》的內容同樣豐富,它分析了宗族,經濟和地方人事過程,更多的內容是描寫地方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其“類蛛網式社會結構”在書中得到闡釋的主要是地方政治結構與人事過程,盡管分析了經濟、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作用,但沒有詳盡地展示各種要素之間的關系,當然,由于宗族的研究相對成熟,所以其對宗族在各種關系中的分析則較為詳盡,但其他要素分析的內容遠不如這么豐富,盡管這種模式有很大的涵蓋力,但由于分析與讀者的期望尚有差距,因而此理論的分析效用尚待作者做進一步的闡述。
同時,作者也提出了人類學分析和研究的兩種方法:“反觀關聯方法”和“文化直覺的方法”。應該說反觀關聯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新見,所謂研究必定是針對已有的成果作出創造性解釋,因而在研究前心中應存有相關的文化背景和分析要素,且解釋必須置于某種意義網絡之中。作者提出要有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的儲備,這一點應該是人類學者或任何觀察者都應該具備的知識。但是是否應該把歷史的敘說大篇幅地應用于人類學的著作中,去作研究背景的鋪敘,則似可商榷,因為人類學著作的讀者應該具有一般的歷史知識,如果對這些歷史文化做過多的背景鋪敘,很難見作者有什么新的發現。這就好比在寫作前應該了解相關研究成果及知識背景一樣,只是個常識性的問題。書中對大合作和的上層材料大量地鋪敘,而且對儒教觀念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儒學的“中庸”、“仁”等作了大量的說明,對于稍具歷史知識的人來說,則無多大意義。
文化直覺的方法在人類學的調查和敘說中至關重要,但作者追尋中國文化及中國哲學的直覺性特征,似乎于人類學本身意義不大,因為人類學調查的村莊的變遷是大眾文化的研究,大眾的生活一般是憑經驗與推斷,其中可能含有直覺的成分,也可能有邏輯推理的成分。而作者把直覺與邏輯作為中西文化的特征對立起來,姑且不說這種特征主要表現于精英文化典籍思想的差別中,只就中西的二元對立而言,可能并不太科學。我們說中國文化時經常以西方為參照對象,可能文化直覺本身便存在于許多文化中,包括許多部落文化中。這種二分無疑是把西方作為“他者”來參照自身的定位。面對西方強勢的物質文明和具有特色的精神文化,中國人在為自身文化定位時總是以它作為參照來反觀自身文化的特征,而忽視了其他異文化的存在,或許參照更多的文明,我們能研究的特征便不成為特征了,這是西方沖擊和文化民族主義的爭鋒中容易出現的中西二元對立的解釋誤區。
二、人類學給歷史學的啟
首先,它擴大了史學研究的范圍,暗示了史學研究的多種可能性。《金翼》盡管是小說體裁,但無疑我們能看見黃村金翼之家幾十年的歷史進程,這是以一種人類學的線索呈現歷史,而不是以時間為順序,他考察的對象盡管有些不是人類學特有的研究對象,但不以時間為序和小說體體裁便足以讓人耳目一新,它主要考察村莊的婚禮、糾紛、家族家內矛盾,農村人情風俗等無疑有與紀事本末體頗為相似,如果僅以時間為序,則難以集中,當然,當今史學的研究現狀正在改變,很多即是對這些成果的吸收,尤其是吸收了其中的很多分析概念,如宗族、婚姻、家庭結構等,這些無疑使史學更進一步精細化。
同時,在人類學的影響下,大量的地方文獻進入史學的視野,如《銀翅》中所提到的地方道教唱本、寺廟及道觀中的簽文、農家的對聯,以及地方傳說及流傳地方唱本。無疑,對一個地方作精細的研究,需要盡可能地搜集材料,而史學要走向深入則必須要盡可能正確地看待各種流傳的文本,盡可能發掘其中的史料價值。當然有很多學者都已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趙世喻對碑刻傳說資料的利用、王子今對詩詞和竹枝詞及驛壁題詩等的利用。更重要的是,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貫重視的獲取材料的方法——田野調查,它可以使我們了解某些觀念在地方的遺存,國家的政策控制在地方的實行,一些當然的觀念在地方中重新得到審視和矯正,也正是對人類學、社會學的吸收,使史學的界限開始模糊,有很多文章很難說是史學還是人類學、社會學。讀完《銀翅》我們便很難給這樣的作品作定位,也正是在人類學的影響下,很多口述材料得到利用,新的史學領域得到拓展,如劉小萌開展的知青史的研究便是大量地利用口述材料,才得以深入。這一些尤其是對時段較近的歷史領域的新拓展尤具意義,當然,由于史料的記載,一些古史中的傳說也得到了保存,通過對其梳理,有時可能會解決很多重大問題,如王子今先生對平利女媧故事的研究,找出傳說傳播的路徑與當時交通系統之關系,這一些無疑都是在新的學術空氣和氛圍中才產生的。
其次,它加深了史學的理論素養,促進了史學新范式的形成和史學研究新取向的進展。由于人類學多以村莊、社區、部落等為研究對象,是區域史研究的一部分,因而使區域史研究大大推進。在這些研究中一般要研究區域社會如何演進,尤其是在面對現代性入侵如何調適又如何作出反應。與此密切相關的則是關注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尤其是地方精英與地方政治之間的關系,這類問題的討論在史學的研究已不少見。但是以往的研究可能還是受歷史學本身學科優勢的影響,很多關注是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國家政權建設和社會動員及社會控制,如杜贊奇對華北社會的研究。當代對身體史的研究和關注,這些可能也受其他思想和學科因素的影響,如對社會控制的研究就是受了福柯對監獄研究的影響。按此路徑發展下去,史學界已發展出一種專門研究方法和視角“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視角,有些強調地方精英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管理式配合,有些研究紳士在其過程中的兩難抉擇,《銀翅》中更有對“保長”這一類角色的研究。
另外,人類學的研究還可以在以往史學的爭論中作出自己范式的貢獻,由于受中西困境的影響,史學界一方面反對“沖擊——反應”的外力作用論,希望關注本國的經驗,尋找本國文化在面臨西方的沖擊時如何適應與抗爭,同時希望找到本國歷史發展的延續性。但是,全球化和西方沖擊又是一種不可否定的事實,世界體系論的影響又讓我們無法忽視,因而如何在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雙重作用下去找尋社會演進的動力的確是個難題。事實上,由于社會的演進是一個過程和整體,無論你找出多少分析的概念與范疇,似乎都很難將這個整體再度重現,一個件事或一個理論分析中所蘊涵的因素,都很難看出哪些是中,哪些是西,因而“摸著石頭過河”可能是一個有效地避免爭論而同時又能較為清晰地展示這些要素的現實態度。而人類學選定研究對象,以“事件——過程”的方式展示,以揭示各因素在其間的參與程度和相互關系,就是這一態度的實踐。同時我們也會發現,人類學自身也難以清晰地展示我們所知的世界,但較史學而言,無疑是前進了一步,或許這本身就是語言的蒼白吧!
最后,它給予我們一些零星的思想火花,對某些具體問題作了不同于成見的敘述,在此背景下,舊問題與舊史料就能得到新的解讀。如《金翼》對家庭糾紛的描述,《銀翅》中提出的“準-組合家族”,對于理解歷史上的家庭形態很有幫助,對賈誼所描述的家庭關系的不和諧有了比較切真的認識。商鞅規定“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要分開而居,解散大家族,此時家族的實際生活形態可能也是“準-組合家庭”式的。還有關于公共食堂與人口增長的關系,說明有些政治事件只有落實到具體的實施環節中才能看清其所引發的一些問題,家族勢力對單身增長傾向的影響,說明文化與社會之間復雜的關系,讓我們看見了家族勢力對傳統社會的負功能。
三、人類學與后現代主義在史學中的交匯
在史學的新近變化中,人類學與后現代主義的視角總是交匯在一起的,它們一起促成了史學的新變化,后現代流派復雜,影響深遠,在史學領域中也有否定史學客觀性的論調,認為史學與文學一樣同樣是虛構,是歷史學家根據文本所呈現的表象進行的表象的再創造過程。他們認為語言本身有其自身的結構,語言的意義的表述主要是靠語言之間的差別,語言本身的結構決定了其“能指”和“所指”是有差距的,這促成了“歷史敘事學”的興起。的確,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也時常發現語言無法清楚地呈現一切,但是試圖清楚地展現過去的真實仍是史學家的矢志。只不過有時我們曾經認為的真實可能是受了意識形態和某種權力話語的支配,而當下的任務一方面是描述權力話語的生成過程,指出以往研究的虛幻性,另一方面指出歷史中被忽視的事件和人物,或者糾正曾經錯誤的解釋。這一點應是史學經過反省后的當下任務,而人類學也有相同的作用,具體表現如下所述。
1、思想史的研究中,要避免受過去目的論的影響,認為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發展是不斷邁向唯物主義和思想啟蒙的過程,以西方思想作為參照物,忽視傳統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一方面要探討思想史發展中出現了什么新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說明某些思想消亡的原因,“既做加法,也做減法”。另一方面要關注過去知識階層所未曾注意的思想層面,超越典籍思想的研究,注意一般的思想、信仰和行為,并關注大小傳統之間的互相影響,一方面要關注大傳統向小傳統滲透的媒介和路徑,另一方面也要關注小傳統如何通過精英階層的思想環境中滲入典籍思想,同時還要關注一些特殊的事件,如民間信仰如何獲得官方的認可,尤其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中,由于皇帝有時能對一些事件和思想的推行起關鍵作用,因而關注梁武帝等這類皇帝、皇帝詔書等內容就別具意義。
2、人類學本身在走向現代社會自身的研究后,即不再局限于以部落社會為研究對象后,實際上是慢慢擺脫西方中心觀的影響,他們本是把對原始社會的研究作為西方的“他者”用來介定自身的,而在中國開始邁入研究漢人社會之后,便越發關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及近代社會的演進,而且關注下層社會本身,去呈現弱者的身影,聆聽弱者的聲音,如《金翼》、《銀翅》中對碼頭工人的關注,但是那里的關注還是不夠的,沒有讓弱者呈現自己,講述自己。而林耀華對土匪的敘說,則能使人清楚看到其對居民的影響及在社區中的生活壓力,以及其落草和轉化等各方面的問題,這一些無疑具有了社會史的視角和取向,只不過有時分析還不夠具體。這些都是企圖使史學走向精細和深入。
3、由于人類學關注基層文化,善于分析文化在生活中的作用,這打破了原有社會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而轉而關注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生成過程,這點如家族文化影響婚姻生活便是例子,基督教加強小團體的整合也是說明。然而由于《金翼》和《銀翅》均是以展示地方社會的文化和生活變遷為目的,因而關注文化的建構作用還較少,如果看一看劉志偉先生的研究,便會發現地方并不總是在被動的適應中央,有時為了族群認同和贏得在當地社會的地位,人們可能建構關于宗族的認同,這說明宗族在明清江南也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產物。這些研究無疑已是具有后現代色彩的歷史研究,當然這點在王斯福的“帝國的隱喻”的民間信仰圖式中已有說明,但劉志偉把沙田、宗族神明、戶籍等均納入文化建構的視角中,則是更具典型的后現代風格。
4、由于人類學深入的研究,可能自動破解一些西方中心論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的以往研究中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的偏見,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問世后,中國人總是要慣常性地思考中國傳統的儒教與資本主義到底呈什么樣的關系,當然,韋伯是從一種發生論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而現今的研究者們則企圖說明東亞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可能包含哪些文化因素,儒家傳統在其間的作用如何。但人類學的研究說明閩南人既具有商人的動機和精明,同時又深受儒道等各種宗教信仰的影響,這使我想起了經濟研究中的“道義經濟學”和“理性小農”的矛盾。其實,農人可能既是理性的同時又要顧慮道義,這兩者似乎不可以并存,事實上,他們就這么并行不悖,宗教與科學也在中國鄉村中合理而有效地運行,盡管在莊孔韶先生把宗族的存在歸因于農村封閉的社區和教育體制使教育尚未深入,知識普及程度不夠,這些說法,固然有些道理,但是莊自己也認識到科學有自己的界限,宗教提出的問題可能科學既無法證明也無法反駁,這一些說明了某些因素可能扎根于我們的民族心理中,或許宗教與商業本是兩個不相關的領域,我們過多地討論儒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的適應性本身就陷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中。
應該說,在史學的研究中人類學已深深地打上其烙印,甚至有時有向史學爭奪地盤之感,但史學的新近轉變無疑是多學科的交融,因而討論人類學的影響時可以清楚看見后現代思想留下的印跡。
四、余論
人類學對史學的影響已清晰可見,但是無疑人類學也吸收了史學的歷史維度,也注重到了與其研究相關的史學文獻的研究,但人類學決不是歷史學的全部。人類學所展開的研究多以村莊為中心,他們所得的是“片面的深刻”,他們也無意去把握歷史的全景,但是我想,如果沿人類學的研究的道路順著走,我們無疑還不能清楚揭示中央控制甚是嚴密的中華帝國的中央與村莊的關系,因為這一過程還會經歷許多媒介,地方精英的影響也決不會止于地方鄉鎮的范圍,因而如《叫魂》一樣探討中央心態與地方省縣各級之間的關系在這類研究中可以補上不足的一環。同時我們還可以討論省縣周圍的精英與省縣府之間的關系。盡管這類研究可能也是片面,但無疑會更具體地考察了其作用的媒介及調適應對的過程,然而當下這類研究似乎尚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