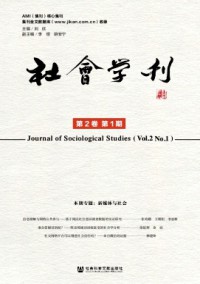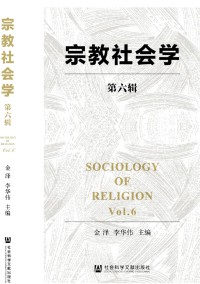社會學視野下倫理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社會學視野下倫理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倫理學不是一種理論科學主義倫理學,相信科學在學問形態上的普遍性從而以科學代替倫理學,它在人的文化心理中認定生命理智相對于生命情感的普遍性。“倫理學只給人以知識而不給人以任何別的東西,它的目標只是真理,就是說,任何一門科學,就其為科學而言,都是純理論的。”石里克這種關于倫理學使命的界定,完全是科學性的。它不但取消了倫理學作為一種學問形態的獨立性,而且使倫理學從屬于科學。其實,任何個別學問形態的成立,都不能從單一的學問形態得到普遍的規定,即使它們是內在相關的,但其差別性更為重要。倫理學與其說是規范科學,不如說是象征性地展示人的生命情感的學問形態。要想在倫理學中規范什么,這是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審視倫理學的產物,在人的文化心理中也是其生命理智替代生命情感的結果。倫理學的語言為感受性象征語言,它所帶出的東西就是帶出那東西的原因。
倫理學不為人創造出一種價值規范,即使其中部分有規范性的成份,但它由此岸的生命情感世界自然呈現出來,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象征。倫理學描述人的生命情感的邏輯圖景,即愛的圖景。當然,這種圖景不能同人的生活與人性相對立。人的現實生活,主要是一種情感生活,離開情感而相互照面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至少,陌生人的照面,是基于他們同為人的同根體驗。所以,倫理學的原則是情感的、愛的原則而非理智的、思的原則。所以,倫理學拒絕尋問為什么愛的問題,由于人所愛的對象就構成他愛的原因。它使用的陳述句,是描述性的而非判斷性的。倫理學不執著于人的行為的應然性,在邏輯上沒有支持或反對它的結論的證據。在此意義上,倫理學不是一種理論。這并不是指倫理不關懷普遍的道德問題,但不像羅素所說的那樣倫理學會賦予我們個人的某些欲望以普遍性。
倫理學不認識道德上的善倫理學展示愛的普遍邏輯圖式。
如果從人的文化心理中的客體化本源的相關性方面來審視倫理學,那么,它所展示的個人的某些欲望,乃是共在者全體在此岸世界同根的欲望。倫理學不評價人的行為但同人的行為相關聯。相反,人的行為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展示。個體生命選擇什么樣的行為,除了根據其理性外,還更多地以情感原則為原則。此岸的情感生活,主要表現為愛的行為。人只有從愛的行為過程中才會理解愛的本根;男女只有在愛的實踐中才明白自己尋到什么樣的愛。從愛的行為探究倫理學,就是從個體生命的情感活動展示倫理學。
同樣,把倫理學的使命規定為“認識道德上的善”,這是科學主義倫理學對其使命的無明,又是它的必然推論。
倫理學的對象與其說是善,不如說是人在此岸世界中所表現出來的愛感圖景。善僅僅為倫理學附帶的產物。倫理學家,不可能也不應該教導人愛誰及如何愛。因為,愛隸屬于個人的實踐。而且,倫理學不能停留在認識愛的水平上,它要展示、呈現愛的邏輯圖式。以此岸的生命情感為對象的倫理學,使人喪失了為之下定義的條件。倫理學家只能象征性地描述那些展示此岸世界的情感生命。相反,外在于人的意識生命的道德,也外在于共在活動中的精神生命體。這種道德,通過理性的論證演繹出來,認識善構成其內在的動機。它是法律而非道德。因為,真正道德的律令,不能由理性給出證據,它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需要,從人的生命情感在此岸世界中生長出來。若某人感受不到愛的需要,任何關于愛的道德律令對他將無效。
倫理學的社會性社會倫理學以社會主體論為特點。這個主體,不是一個認識性的理智主體而是實踐性的情感主體。倫理學關懷人與人的情感關系或他們的情感共在。這為倫理學所獨有的社會性。誠然,共在者全體的情感共在,超越于任何個別的共在者之上。任何個別的共在者,都不可能為共在者全體的情感共在承諾可能性。只有在差別于人的耶穌基督的上帝那里,共在者全體的共在才成為現實。換言之,是那承諾共在者全體的存在性的存在本身,構成普遍道德的內容。個別道德的共在從此才獲得了終極依據。
普遍道德的普遍性,根植于普遍存在中。這種存在是普遍的,它內含永遠超越個別存在者的力量,同時和個別存在者發生內在關聯。只要個別存在者在共在活動中守護著自己和對方的存在性,這種根源于個別道德的存在者就分享了普遍道德。按照普遍道德的承諾,任何個別存在者的存在性的被剝奪都是不道德的。并且,那剝奪個別存在者的存在性的剝奪者,往往充當普遍道德的化身,否則,他就失去剝奪他人存在性的根據。在此關于普遍道德與個別道德的關系的探究,表明倫理學的社會性還有在上的存在本源。
倫理學對象的后驗性價值邏輯論用后驗性限定社會倫理學。后驗性,指在個體生命經驗了經驗之后產生的經驗。如同科學的經驗對象一樣,社會倫理學的后驗性,使它面對著現成性的經驗對象,即使該對象必須在個體生命的經驗之后。個體生命只要是完全的,他就會經驗到生命情感在不同層面上的對象化對象。而且,社會倫理學的后驗性,迫使個體生命和他所愛的對象發生關聯。個體生命所愛的對象必須內化為他自己的感性經驗,否則,情感共在就不可能發生于他身上。
倫理學對象的后驗性,意味著它以此岸世界的生命情感——、親愛、情愛、友愛、圣愛——為對象。
生命情感的此岸性,指個體生命在存在活動中所經驗的情感對象的現成性。愛的對象,就是那從虛無地平線上聳立的人,就是那和愛者一樣具有動物性與神圣性向度的被愛者。個體生命通過和其他共在者相遇,豐富著自己的動物性與神圣性的情感內容。愛本身乃是對愛的方式的創造,其結果形成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這人格置身于動物性與神圣性之間。生命情感首先展示在倫理學家的此岸生活里。倫理學,并不是為了認識而是要求個體生命體驗這種生活,體驗生命同根的源泉。對生命情感在不同層面的對象化毫無體驗的人,對倫理學就不會有差別性的言說。當然,這種體驗,并不以藝術形式的方式展現出來,而是借助感受內化于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中。
倫理學的對象,喚起個體生命向共在者全體合一同根的欲望,它拒絕任何事實的判斷,它不對任何同根體驗的狀況進行論斷,因而不可能找到一種客觀的證據來反駁倫理主體有無同根體驗。在此意義上,倫理學所含的陳述句是描述性的,描述的正誤無關緊要。科學能夠探討生命情感的各種起因和實現方法,其中不含任何真正的倫理句。因為科學涉及何為正誤的問題。“雖然科學確不能解決各種價值問題,但那是因為,它們根本不可能用理智來解決,它們不屬于真偽的問題。任何可獲得的知識,它必然是用科學的方法獲得的;而科學不能發現的東西,人類是不可能知道的。”羅素在此言說出科學作為一種學問形態的有限性,但這并不會導致否認倫理學對象的可感受性。
倫理學語言的后驗性倫理學對人的行為不作出任何價值判斷,但它要用感受性象征語言呈現倫理學家的生命情感體驗。
價值邏輯論把語言的起源問題懸置起來,根據語言的功能把它分為符號性語言、象征性語言、指使性語言。符號性語言強調所指與能指的差別性,語音的差別導致語意的差別。這種差別是人的理性發揮作用的前提。語音與語意之間,是一種社會性的契約關系。語言起源的所謂約定俗成論,就是根據符號性語言的意義發生方式提出來的。
象征性語言的所指與能指,處于一種相關性狀態,語意的差別和語形相關,語形的不同帶出語意的不同。語意出于語形的展示、流射。其中,能指與所指,既不是外在的強加關系,也不是解釋者附加的產物,而是所指從能指中呈現、語意從語形中涌現。符號學利用符號性語言體系的經驗,不可能在根本上闡明象征的功用,更不可能對象征性語言體系作出明晰的規定。在象征性語言中,語詞的所指與能指的相關性決定了語意的多樣性,盡管這種語意始終和語形相關聯。
指使性語言的所指與能指,完全處于同一的關系中。人在這樣的語言活動中,即是他的存在本身的昭示。語詞的所指就是能指所表示的東西,語音或語形的差別對于語意的出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雙方的絕對同一性,甚至是和人的生命存在的同一性。
生命情感的特點是它的流逝性,當其流在不同的存在者身上時形成不同的情愛圖景。這種作為倫理學對象的情感,要求其呈現語言的象征性,而且是基于情感主體的感受而非形式化的感覺。倫理情感的呈現,是為了呈現者本身的生命存在。感受者在感受現實的情感圖景中,感受到自己生命情感的留駐。所以,倫理學將展示此岸的生命情感圖景當作自己的使命。由此表明,在倫理學中無所謂真理與謬誤的問題,它也不是為了傳達知識。雖然我們關于生命情感的感受是在符號語言中不可言說的,但在象征語言中我們依然可言說自己的內在感受。情愛感受的存在依據,在感受者的個體生命里。在此意義上,倫理學是通過改變他人的生命情感來改變他人行為的。
倫理學使命的后驗性倫理學在對象、語言上的后驗性,帶出它在使命上的后驗性。價值邏輯論在關于倫理學的定義中指出:它的目的,是在此岸社會為人類中的個體生命建立原初人格。對于個體生命言,它要形成其原初人格;對于人類生命言,它將彰顯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并匯注為理想的人生形象。無論原初人格或理想人生形象的生成,都是個體生命在經驗生命情感后的一種經驗。這正是倫理學使命的后驗性的涵義。
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根源于他對在上終極信仰的承受,即使他以某種偽終極信仰為終極信仰。個體生命以此為基點,對其所遭遇的一切展開價值判斷。一般情況下,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具有時間性的規定性,他在一段時期內自認為是對自己最根本的人格觀念,也將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實質上,倫理的人生,就是探究原初人格的原初性的一生。一些普遍的觀念,往往成為激勵人生開掘原初人格的動力。例如,藝術家的藝術作品經常發生質變,但他對藝術本身的信仰依然如故,而且,作為藝術家的原初人格的原初形式,通常伴隨個別藝術家的人生。
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為一種有限人格。它不承諾其他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但認同和其他原初人格主體的共在。社會有序性的基礎,在于個別原初人格的共在。倫理學在此岸社會建立有序化的生活,不是為了某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而是為了個體生命共在者全體的共在。反之,若以個別原初人格為共在者全體的人格理想,這便抹去了該原初人格的有限性,本來應由社會共在建立起來的社會平權就會被社會暴力所代替,縱然這種暴力未必采取武力的形式。
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以言語的方式在一段時期內呈現于他的存在與共在活動中。凡是那些頻繁呈現的言語,都在不同層面展示出個體生命的原初人格。在個體生命的言談或書寫兩種活動中,不斷呈現的言語透露出他的原初人格的信息。當然,日常生活的漫談中反復涌現的語言因和個體生命無關聯,所以,其中沒有原初人格的言語性成份。
文檔上傳者
- 主導社會服務社會
- 社會政策
- 社會政策
- 社會公正社會主義遺產和社會民主主義
- 社會主義現象和社會主義本質
- 和諧社會與社會學
- 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失誤
- 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
- 社會主義社會矛盾
- 和諧社會增強社會活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