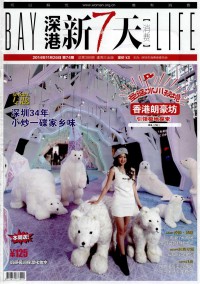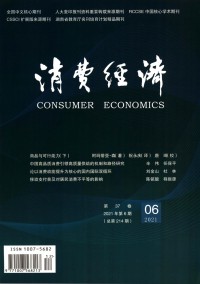消費邏輯的美學后果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消費邏輯的美學后果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消費邏輯對整個社會進行了整體性塑造,引發了消費文化形態的形成,并引發了審美泛化的美學后果,其突出表現就是審美自律性的消解、審美功利性的彰顯和審美快感化日盛。
[關鍵詞]消費邏輯;美學后果;審美觀念
消費社會中,消費邏輯占據要津,成為一種結構性力量,對整個社會進行整體性塑造,致使文化形態為之一變,呈現出嶄新的面目來。衣食住行都披上了文化的外衣,社會活動稟賦了文化的特質,文化作為消費對象已是明顯的事實,而這同時預示著文化也成了審美對象,無不文化,無不消費,無不審美,整個社會都彌漫著濃厚的文化消費和審美消費氣氛,生存、文化、審美三者在消費社會中奇妙地相互滲透,彼此融構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樣態。在消費營造的特殊文化類型里,美學觀念得以演進,審美新變悄然發生。審美觀念與既往的美學主張判然有別,與傳統的美學理念拉開了距離,消費時代的審美觀念表現出了新的質地。
一、審美自律性的消解
作為最重要的審美價值,自律性曾經確保了經典文學藝術的美學價值,也讓人們迷戀其間,執著于從文學藝術本體之中尋求審美享受。及至后現代消費社會,西方現代主義自律性的構想卻遭到根本的質疑,諸多學人在論證自律性只是一種幻象,既無法實現也無法確證。現代主義審美自律性最明顯的特征在于:“否定、拒斥和顛覆資產階級日常生活及其意識形態,即不僅反叛傳統,對抗以啟蒙理性主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明,而且還與它自身相對立,通過把自己視為頹廢且在不斷毀滅自身中尋求鳳凰涅槃之再生,進而在體制外保持自己的先鋒激進傾向。”[1](導論P.1)西方現代派,憑借與日常生活切割的方式,力圖確保藝術的自律性品格,又以頹廢的面貌和激進的姿態作為策略,在自律性的迷戀中祈求再生。但是,隨著后現代消費社會的到來,人們逐漸認識到,審美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所謂審美自律性的背面,往往有著社會、歷史和政治因素潛在地發揮著支配性作用,將藝術自律置于尷尬境地。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美學范疇,自律性的概念尤為資產階級所鐘愛,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發展階段,彼時物質生產尚不發達,文化生產與物質生產均相對獨立,藝術還可以從實際語境中脫離出來,與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自律性的特征,形成了一種藝術作品孤絕于社會現實之外的觀念。但是,藝術與生活的脫離本身就是一種歷史化的過程,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會受到社會歷史因素的支配和制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藝術自律觀念的合理性也將面臨挑戰,這在后現代消費社會尤為突出。事實上,“這塊飛地”避不開社會實踐,居于支配性地位的社會秩序終究要發揮影響,或以顯性的方式進行,或以隱性的方式實施。所謂自律,標示著藝術與生活實踐相互分離這一事實,但這種分離卻把社會歷史過程抽空了,將其虛無化了,藝術成了藝術本質演繹發展的結果。“藝術與生活實踐之間有著交互性的辯證關系,而‘自律’意味著自足性,自足的事物不需要依賴他者而存在,這就是試圖將一個需要中介性過程辯證性的發展簡化成為直接性的‘神話式’演變,而由于這種改造出于某種目的歪曲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它向我們呈現為一種曼海姆意義上的意識形態。”[2]此處曼海姆式的意識形態,亦即統治集團的特定的集體無意識,是特定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某種策略,而這種策略往往罔顧事實,甚至故意歪曲社會現實。表面上看,審美自律性的概念,將藝術與社會生活脫離開來,從而為藝術墾拓了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也被賦予了反抗資產階級權力規訓的可能性,但是,這種自由發展空間無疑還將受到種種社會秩序的操控,也必然遭遇資本運作機制的約束和羈絆。因而,審美自律頗似一張畫餅充饑的理想畫卷,既美好又誘人,但實際上卻具有麻醉劑的功能,讓審美主體一味沉醉其中而難以自拔,忘卻了馬克思意義上的反抗。而事實上,所謂的審美自律不可能脫離社會秩序的支配,不可能隔絕社會歷史的規約,自律的背后往往有著他律的規制,這種規制其實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隱蔽呈現。歷史地看,審美自律性的觀念由來已久,遠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前就已存在,它在幫助我們認識文學藝術作品的內在屬性方面起到了促進作用,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文本闡釋方法的理論依據。但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審美自律性逐漸淪為資本操控的手段,淪為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策略,這就使得審美自律性更多地成了一種幻象,具有麻醉世人的作用。而進入消費時代,一切都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審美自律的幻夢破滅了,它的意識形態屬性昭然若揭,審美受制于文本內外多重因素的操縱,文本意義與社會歷史的聯系,都隨著“消費”的結構性力量和系統性作用變得越來越顯明。審美,已由自律走向他律,或者說自律與他律共享共治,已成為審美批評的時代轉折。事實上,在審美批評實踐中,我們堅持的原則毋寧是,不要以自律排斥他律,更不能只顧他律而置自律于不顧;只有兼及兩者,保持兩者間必要的張力,尋求兩者間適當的平衡,我們才能恰切地解讀文學藝術文本的意義,并把文本的意義放置于意義生產的現場,徹底地展示出審美批評的時代價值。
二、審美功利性彰顯
法蘭克福學派的群星對“文化工業”的揭橥,道出了消費社會文化生產和藝術作品的功利化實質。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最初的論述中,他們使用“大眾文化”一詞來指稱流行藝術的當代形式,后來又采用了“文化工業”的概念,而文化工業的各種產品也都成為了審美的對象。阿多諾曾以《文化工業再思考》一文名世,其見解至為深刻,他認為文化工業的那些產品根本上就是專為大眾消費而制作的,是為了滿足大眾消費的性質要求而有計劃地炮制出來的。文化產業的各個分支,結構相似、功能對等,彼此適應、相互協調,形成了一個溝通無礙、運行高效的完整系統,“這成其為可能,既是由于當代技術的發展水平,也是由于經濟的和行政的集中化。文化工業別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費者”[3](P.198)。文化工業對消費者進行整合的過程,憑借的是當代技術和社會機制的集中化運作,并有計劃地使各個分支結構一致起來,共同構成一個整體系統,從而炮制出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同時也是各式各樣的消費品。這些消費品是為大眾生產的,而對這些消費品進行消費的性質也是特定的,其中的功利和效用目的不言自明。阿多諾進而斷言:“文化工業的全部實踐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3](P.199)恰恰出于盈利動機,文化工業的產品里自然蘊含著對于效用的精確算計,而且這種算計始終居于首要地位。阿多諾的“文化形式”指的就是文化工業炮制出來的產品,也即審美對象,審美對象身上被賦予了“赤裸裸的贏利動機”,在對效用的精打細算中,在對效益的癡心追逐里,審美自律性告別了昔日的理想狀態,逐步遭到了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對審美對象的功利性打量,審美活動中的功利心和效用意識占據了上峰,而且這種占據還是整體性的和結構性的。在這一結構系統中,消費彌足可貴,在文化工業的運行機制里發揮著重要作用,使得各種文化形式的生產和消費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導向,文學藝術不再是獨立的精神產品,而蛻變為文化工業的種種商品。也就是說,文化工業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大規模生產出的標準化的文化產品,與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化作品大相徑庭,其最為突出的特征便是商品性和消費性,而為了確保對這種商品的消費,又往往與大眾傳媒深度結合,借以達到賺取利潤的功利目的。而“文化工業是整個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系統,而且在生產和消費的背后一直隱藏著一種強大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力量,憑借這種力量,大眾的自覺意識被束縛了,主體性被控制和操縱了”[4](P.29)。對于這些商品,無論是在生產環節,還是在消費過程,都有著明確的功利導向,都存在意識形態力量的操演。藝術作品的自律性被文化工業不可逆轉的歷史化過程剝奪了,審美也就具備了功利化的傾向,審美自律性反求諸外,向著功利目的和效用宗旨靠近,這既是文化工業的機制化結果,又是大眾文化語境中審美自身流變的必然。法蘭克福學派中,對消費時代藝術和審美特性提出真知灼見的另一位學者是瓦爾特•本雅明。他將“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與傳統藝術作了比較,認為“藝術作品的可復制性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把藝術品從它對禮儀的寄生中解放了出來”[5](p.93)。這就意味著,機械時代的技術為藝術品的復制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使得藝術品以復制的形式大量涌現,從而讓大眾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享有對藝術品的“親近”,這契合了大眾的文化和藝術需求。但是,與傳統藝術作品相比,“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取消了傳統藝術的獨一無二性,也令藝術作品的“光韻”消失了。所謂“光韻”,在本雅明看來,指的就是“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5](P.13)。曾幾何時,這種“光韻”屬于經典美學視野中的文學藝術作品,其散發的光芒帶給人們永恒的精神愉悅和心靈律動。但隨著機械復制時代的來臨,人們日漸滋長的接近藝術作品的強烈愿望,終于以藝術作品的復制物取代了藝術作品的獨一無二性。一言以蔽之,在我們這個時代,機械復制的藝術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光韻”藝術。面對傳統的“光韻”藝術,人們“膜拜”其審美價值,采取的往往是凝神專注式的欣賞方式;而在機械復制的藝術作品面前,審美主體則常常以消遣性的接受方式,不再“膜拜”其審美價值,而是關注其展示價值。“膜拜價值要求人們隱匿藝術作品”,而“由于對藝術品進行技術復制方法具有多樣性,這便使藝術品的可展示性如此大規模地得到了增強,……現在,藝術品通過對其展示價值的絕對推崇便成了一種具有全新功能的創造物。”[5](PP.19,20-21)這樣,審美的本質便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于藝術品的距離感消失,其獨一無二性所稟賦的權威性得以消除,一種無差別、無距離感、基于個人品味、閑適性甚至游戲性的審美體驗應運而生。本雅明對攝影、電影、繪畫等藝術形式的探討,體現了他對視覺文化的重視,視覺藝術具有更為明顯的展示價值,追求視覺快感取代了關于美的沉思。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審美,消除了傳統藝術審美的那種儀式化的莊嚴感,走向一種通俗的、便利的、平面化的直觀體驗,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三、審美快感化日盛
審美的本來面目即感性體驗,不過隨著消費社會的來臨,這種感性體驗越來越流于快感化。消費社會的典型特征就是符號消費,符號的象征意義置換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幾乎所有的商品都被符號化,被納入象征體系的價值系統,符號生產成了消費社會最具特色的景觀。符號的靈動,在消費社會繪就了擬象和仿真的畫卷,也誘導人們在審美化的體驗中完成對商品的購買和消費。社會生活固有的規律走向消解,社會關系更趨多元,符號承載起更多的文化意義,發揮著規范化和結構化的作用。符號“的過度生產和影像與仿真的再生產,導致了固定意義的喪失,并使實在以審美的方式呈現出來。”[6](P.21)符號的生產,影像的傳播,仿真的擴張,擬象的蔓延,這一切對社會生活進行了有效的重置,促成了一種典型的擬態環境。擬態環境的表意規則已發生顯著的變化,符號能指和所指間的統一性面臨分解,表征理論也顯得頗為單薄,這一切都不再適用于以大眾傳播為重要特征的信息環境,這種環境再也不像鏡子般客觀地對外部環境加以反映和再現,而是經由傳媒的遴選、設計和加工,并重新結構化后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虛擬環境。在這種虛擬環境中,人們對事物的認知有了顛覆性的變化,電視、廣播、網絡等傳媒手段會將某一重大事件呈現出來,供觀眾來理解和接受,但這種呈現或與事件本身無關,要么是經過加工設計的折射,要么是由不同傳媒提供的差異化表述,甚至同一媒介昨天和今日的報道也可能南轅北轍。慢慢地,人們相沿成習,但卻習焉不察,接受了這種虛擬的真實,不再追索客觀實在的真實性。大眾傳媒所營造的擬態環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認知和行為模式,而且也對客體世界作了改寫。客觀地說,這種狀態與消費社會達成了某種合謀關系,消費邏輯正是通過大眾傳媒所營造的擬態環境,來激發消費者的體驗欲望和情感共鳴,來挑逗消費者的購買欲和消費欲,從而實現消費主義的初衷。“大眾傳播媒介最突出的變化,在于它轉而訴諸人們的欲望、沖動、潛意識等,在對語言、畫面、音響、色彩等因素的技術合成中,頻繁刺激著人的感受心理,誘導大眾對生活的當下性體驗和即時感覺。”[7](P.48)消費社會中大眾傳媒的這些最突出的變化,會制造觸動心靈的美學圖景,這無疑將強化消費者的審美體驗激情,使其迷戀和追逐當下性的即時感覺,在快感化的驅使下完成消費。此時,人們消費的對象已遠離物品的實用性,而是轉變為商品的符號價值,這種符號價值是借由傳媒的聲光影像來傳達的。“對商品影像(image)的消費,其意義和價值將超過對商品傳統的使用價值本身的消費。通過廣告的衍射,庸常的消費品便具有了某種夢幻特質,與羅曼蒂克、欲望、希望等等人生意緒形成某種象征關系”[8](PP.40-41)。因而,商品的美學外衣至為重要,商品的陳列樣式需要美學的籌劃,商品的空間安置也離不開美學的設計,這一切都將在審美化的過程中完成,加之大眾傳媒所呈現的符號和影像誘惑,匯成了刺激人們消費的交響,這種交響確保了消費的過程也是審美的過程,消費就是在審美體驗的快感化過程中完成的。鮑德里亞反復說明,消費行為的目標指向對欲望曲折隱晦的表達,指向通過區分符號來生產價值的社會編碼。在消費行為中,符號生產的制約機制是象征邏輯,象征邏輯所形成的欲望修辭讓物品已與其明確的使用功能隔斷了聯系,同時讓物品的符號在象征序列中完成了意義生產,這種意義生產與消費者審美體驗的快感化保持了天然的聯系。正像周憲所言:“日常生活審美化本質上乃是通過商品消費來產生感性體驗的愉悅。……體驗貫穿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它構成了審美化的幸福感和滿足感的重要指標。”[9](P.287)這也就說明,消費社會中的審美體驗已經沉浸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納入審美化的進程,因而被納入審美體驗的范疇。日常生活的審美體驗,現在越來越感官化,越來越以快適和滿足為鵠的,逐漸成為衡量一個人幸福與否的標尺。不妨設想,如果一個人故步自封,躲在狹隘的小天地,排斥消費社會的種種奇觀,厭棄消費文化的符號征象,且不說他很難做得到,即便能夠設法達此境界,也很難給他貼上幸福的標簽。幸福是一種感覺,是一種基于體驗的感覺,絕非抽象的理性判斷,絕非知識學的客觀認定,無利害的審美景觀如果與他拉開了距離,就再也帶不來幸福的感覺;而如果是基于體驗,他的幸福也離不開消費社會日常生活的審美體驗。消費文化中,“大眾消費運動伴隨著符號生產、日常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織”[6](P.165),圍繞的軸心就是刺激消費者審美體驗的快感化,借以促發消費者普遍的感覺聯想和消費欲望。為達此目的,“把審美對象圖像化”“把審美對象感官化”“把審美對象身體化”[10],這三者既是審美體驗快感化的直接表現,同時又是迅速實現審美體驗快感化的有效途徑。收聽廣播,打開電視,登錄網絡,走進影院,欣賞曲藝,或者參與消費社會的各種文化藝術活動,我們會發現已經圖像化、感官化和身體化的審美對象比比皆是,已將人們團團圍困,這些所謂的審美對象以娛樂大眾為能事,以賺取碼洋為宗旨,卻不斷地向著文化舞臺的中心移動,不斷地消解宏大敘事,不斷地抽空審美價值。當然,大眾有娛樂的權利,有排解壓力和釋放壓抑的本能需求。即便如此,審美體驗的快感化也需要設定必要的界限,雖然它發揮著消費社會永動機和加速器的功能,但社會更需要它釋放出良性的動力。顯而易見,消費時代審美的種種征候,既反映了審美泛化與審美觀念演進的趨勢,又是當下審美文化的組成部分,絕不容忽視。對消費文化發展脈絡的梳理,對審美新動向的分析,對消費邏輯美學后果的揭示,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消費文化的本質特征,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消費時代審美范疇的變遷,從而在立足現實的基礎上,把握審美規律,辨明美學路向,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昌盛。
參考文獻:
[1]肖偉勝.西方現代主義自律性詩學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金永兵.“后文化”時代審美還能詩意地批判與拯救現實嗎?[J].當代文壇,2018(4).
[3]阿多諾.文化工業再思考[J].高丙中譯.文化研究第1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4]王曉路等.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6]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7]張晶.論審美文化[C].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8]蔣榮昌.消費社會的文學文本[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9]周憲.文化表征與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0]張玉能.消費社會的審美觀[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09(4).
作者:王敬民 單位:河北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