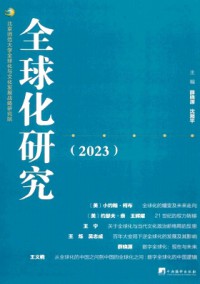全球化進程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全球化進程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互利作為中華民族和全人類從沉痛的歷史教訓中結晶而來的智慧,以其必然性不斷地凸顯。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進入新一輪迅猛發展,一國和他國、和全世界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一損俱損、一利懼利,“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兩極對立必擇其一”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為歷史;你贏—我贏的現代“互利”精神正在成為嶄新的時代精神,正在使中華民族精神和偉大智慧煥發勃勃生機。下面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對互利進行初步探討。
一、互利:從悠久的歷史主題到嶄新的時代精神
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只要有人和人的活動,互利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成為人類歷史深處悠久的主題;而從近代以來,互利逐漸成為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
微觀上,任何一個家庭正是靠著全家人彼此之間的互利,才能生存和發展。任何形態的家庭,從最古老、最傳統哪怕再專制的,到最現代、最前衛的;從最和諧溫馨的,到矛盾四伏劍拔弩張卻仍然延續的,概莫能外。“即使在一家人之間,利益的分歧也可導致爭吵,但是只要存在著共同的情感與傳統,和解就不是無路可尋,雖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誤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1](p.254),正所謂“兄弟鬩于墻,外御其辱”。而歷史上,除了常態的變更和不可抗力的破壞之外,那些意外地落入衰落、破裂甚至瓦解的家庭之所以遭遇如此的命運,根本原因是,在其大多數甚至每個成員之間,利益矛盾不可解決,而互利機制卻瓦解甚至蕩然無存了。中觀上,各種組織之所以產生、存在和發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每個組織和其每個成員之間在合作中互動;而任何互動在根本上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甚至以利益為核心的,是互利。組織和其每個成員之間、其成員彼此之間,因互利的紐帶而成為利益共同體:組織使每個成員受益、從每個成員受益;每個成員從其組織受益、使其組織受益。假如沒有互利,沒有由此形成或大或小或深或淺的共同利益,任何一個組織既難以存在,更不可能發展。宏觀上,國家之間,全球范圍里,互利同樣不絕如縷:從古到今,總有大欺小、富壓貧、強凌弱,總有滲透和反滲透、干涉和反干涉、顛覆和反顛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總有刀光劍影、腥風血雨;與此同時,通商、交流、和親等各種形式的對話、溝通、交流、合作、聯合也一直存續不絕。在全球化進程中,盡管利益矛盾在民族國家之間非常突出,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非常尖銳,但是總的來說,互利在不同國家之間、全球范圍內,畢竟是大大地推進了并正在更快地向廣度縱深推進——不同國家之間,有共同利益,在互利。總之從開闊而綜合的視野中可以看到,沒有互利,就沒有人類,沒有社會生活。互利是貫穿人類歷史的主旋律之一。
當然,實踐中,互利之不斷顯化、深化、強化,是和社會發展水平成正比的,是社會發展的歷史成果和指標之一:社會越發展,互利就實現的越完全、越徹底;近代以來,特別是在全球化進程中,互利逐漸突出,成為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
在古代,人和人之間相對封閉,有的情況下甚至絕對封閉。在經濟上,自給自足,自然分工占絕對優勢,社會分工非常有限,剩余產品很少,交換很少,偶有交換也作用甚微,并且常常被排斥,個別勞動直接是社會勞動,勞動的目的是自己需要的滿足。人際關系上,基本局限于血緣、地緣、業緣以及神緣(在宗教發達的民族和國家里)關系的范圍里,互相高度依賴。在此之外,交往很少,分化極小,整合很弱。由此決定了在利益關系上,同一群體中的每個人之間,彼此很少分化,高度重合,甚至混沌一體;而不同群體之間,大多數情況下互不相干,有的情況下刀兵相見。在利益追求及其實現過程中,空間封閉,手段原始,方法簡單,特別是目標單一且常常高度重合。于是,我得利,勢必你受損;只有你受損,才能我得利,正所謂“零和博弈”。互利雖然不是沒有,但其賴以產生的土壤少而瘠薄,其范圍很小,層次很低,程度很弱。
近代以來,無論在空間上、速度上,還是在性質和程度上,社會分化迅速擴大,越來越快,日益加深;與此相反相成的是,社會整合也不斷強化。在這兩方面的互補互動中,人們之間,交往越來越多,利益主體逐漸多元化,利益空間不斷擴大,利益差別日益拉開,利益追求及其實現的手段和形式也迅速地多元化、個性化、復雜化。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別勞動和社會勞動、具體勞動和一般勞動日益分裂,必須通過交換,才能達到具體的統一,即勞動本身成為交換的手段;社會結構在迅速的分化中又多層次、多維度地整合;人與人之間,職業高度分工又密切配合,各自的利益在空間、內容、目標和手段等方面都由高度地同一而逐步分化,利益邊界日益明晰。正是在生產的交換和生活的交往中,在生產和貿易的互補、互動中,比較利益逐步形成,從小到大,使每個交換主體都可以用較少的具體勞動換到較多的一般勞動,從而使每個主體共同受益;以最少的付出獲得最大的收益,不但日益成為共同的目的,而且逐漸成為普遍的現實。于是,人們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勞動使用量,促使可用于交換的商品數量不斷增長,質量和性能不斷提高,覆蓋面和滲透力不斷擴張,從而使可以分配和消費的各種資源不斷增加,使各主體可以享有的利益在可能性和現實性上都不斷增長。于是,不論在利益追求的目標、內容、空間和手段等每一方面,每個主體之間,各自獨有的特殊利益既高度地分化,并全方位地向立體化、個性化擴展,同時又高度地互相依存,從而形成廣闊的、多維交織的、網絡狀的共同利益,把不同的共同體乃至全社會日益緊密地聯系起來,互利逐漸凸顯成為時代精神的強音。
特別是在發達的全球化市場上,產權、人才、技術、信息、資本、勞動、土地,甚至制度安排等各種資源,都高度地商品化、市場化,交換高度發達,從生產到生活,從經濟生活到社會生活,本質上是通過互利機制調節復雜的利益關系的,更加凸顯著互利的時代精神。
現代市場經濟中,滲透著如下原則:第一,公平——人們之間自由交換和選擇,從而獲得利益的權利和機會都是公平的。買賣之間,有支出或投資,或必然和必須有受益;支出或投資多少,和受益多少之間,其常態是成正比的。交換不僅對一方有利,對另外一方甚至對多方、各方都有利,至少沒有損害。假如相反,交換輕則受限制、被損害,重則萎縮甚至無法進行,從而以客觀的必然性迫使各主體回到公平交換的道路上來。第二,自愿——每個主體都想實現自己的利益追求,并且力求不斷擴張,這目的只能通過各主體自愿向市場提供日益豐富并且質量價格比、性能價格比高的商品和服務,在交換中實現價格以后,才能達到。而任何利益的相互交換、讓渡和轉移,都只出于交換各方的自愿,沒有強迫。市場價格在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出于各方意愿,通過談判而形成。任何主體之間的任何談判中,任何一方要實現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自愿地把對自己相對次要的、等量的利益讓渡給對方;對方對該讓渡是否接受,取決于該讓渡對他是否有利及利益大小。即任何談判都通過互利機制,進行利益的讓渡和交換。沒有互利,談判不能發生,不能進行,更不能有積極成果。談判失敗,是由于互利機制沒有形成,或者形成后得不到維護而破裂。第三,等價——每個主體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必須得到尊重。這要求每個利益主體在利益追求中,既關心自己的支出或投資能否受益,也必須承認并維護其他主體的利益,讓他人的支出或投資相應地受益,把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主體的利益相結合、相交換。他人利益、共同利益是自己利益的前提;自己利益的實現和擴張是通過和他人利益的互補、互動實現的。由于交換是重復進行的,騙人只能一次,難以永遠;被騙也只能一次,難以重復。因此,誰要想在市場上為自己謀求更大的利益,就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為他人實現自己的利益提供起碼的保證;只想利己,卻不愿利他、利公眾,就會被拒絕進行交換,甚至被逐出市場,其利益難以實現,甚至可能被剝奪,一無所有。[2]市場經濟以客觀的互利機制,對遵循市場規律、尊重其他主體利益的行為進行獎勵;對違背市場規律、損害其他主體利益的行為進行懲罰。由此把不同的利益主體緊密團結起來。換句話說,互利成為了時代精神的一個鮮明主題,在市場經濟中日益強化,在全球化進程中更加突出。
基于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上述特點,現代法也滲透并凸顯著互利的精神。比如,在主體上,法在傳統上被劃分為公法和私法。而現代法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公法和私法結合,形成社會法,既保護、支持和促進公共利益,也保護、支持和促進個人利益,從而保護、支持和促進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互補互動,保護、支持和促進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利。比如經濟法,其核心是反壟斷法,在現代法的視野中,它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把公法和私法、民法和行政法結合起來,產生新型部門法。它的本位不是國家利益,也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在個人、國家的互利中,發展和壯大各個主體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他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福利保障法、環境與資源法等,都是這樣的。再如,在內容上,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在性質上是互相的,在數量上則是等值的:不僅社會的權利總量和義務總量是相等的,而且每個公民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也趨向于相等。“如果既不享有權利也不履行義務可以表示為零的話,那么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就可以表示為以零為起點向相反兩個方向延伸的數軸,權利是正數,義務是負數,正數每展長一個刻度,負數也一定展長一個刻度,而正數與負數的絕對值總是相等的。”[3](p.65)權利是獲得利益的條件,義務則是要實現自己的利益就必須維護其他主體的利益而承擔的責任,是從自己的利益中必須付出的必要的份額。權利和義務等值,就是利益等值,是互利。
互利作為人類歷史深處的主旋律,從近代以來,特別是在全球化推進的現代市場經濟中,逐漸強化和凸顯,而成為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開始成為人類的共識和共同追求。然而,這是來之不易的,是在艱難曲折的道路上、在付出了沉痛的教訓和代價之后,才使人類認識到的。
二、互利:沉痛的歷史教訓換來的智慧
歷史上,在層出不窮的各種爭端中,互利的主題屢遭破壞,暴力和戰爭卻不斷出現,其教訓是慘痛而沉重的。一部人類史在一定程度上同時就是暴力史和戰爭史。比如,在中國,從上古到20世紀初,大規模的戰爭多達4000次以上;僅春秋時代的243年中,有文字記載的戰爭就多達480多次,“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4](p.358),血流遍地,生靈涂炭;戰國時代更是充滿了血雨腥風。在歐洲,古代姑且不說,僅1480年以來,戰爭越來越頻繁:1480-1499年,9次;1500-1599年,87次;1600-1699年,239次;1700-1799年,781次;1800-1899年,651次;1900-1940年,高達892次[5](p.266)。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和隨后持續近40年的一次冷戰,給人類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破壞,烙下了極其慘痛的記憶:每一次世界大戰卷入33個國家、15億人口,傷亡人口3000萬;第二次世界大戰卷入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億人口,僅死亡人口就在5000萬以上。光是在德國,西部居民1/5被炸死,無數家庭在戰爭中慘遭破壞:到1948年底,全國人口的性別比,男性:女性=100∶160;單身者性別比更加懸殊,30歲男子:26歲女子=100∶300。有的歷史學家把1914年以來的世界巨變叫做“大災變”!
與此同時,戰爭使沖突各方之間,舊恨非但不能消除,反而加深,并從舊恨的累累傷疤又激起更刻骨的新仇,埋下新一場甚至新一輪戰爭的禍根,其巨大的破壞性、毀滅性自古以來都受到批判和反對。“殺敵一千,自傷八百”,就是中華民族對戰爭的評價。丘吉爾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TheUnnecessaryWar";羅素則不無幽默地指出,即使僅僅“從財政的觀點來看,現代戰爭并不是一樁好生意。盡管我們贏得了兩次世界戰爭,但是如果戰爭不發生的話,我們現在將要更富有的多。如果人們都不被自利所驅使,——但除了少數圣徒而外,人們并沒做到,——那么全世界就會合作起來。”[6](p.1747)這類思想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上政治家、思想家和社會各界的共識:戰爭對人類社會是極大的禍害;要解決國際爭端,再也不能靠戰爭,而必須靠和平;必須消滅戰爭。同樣是丘吉爾,作為國際上公認的頭號反共人物,毫不掩飾對當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敵意,視之為“魔鬼”,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基于資本主義英、美和社會主義蘇聯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為了消滅當時最兇惡的敵人希特勒,而不得不和蘇聯結盟。而希特勒也看到并企圖利用英美—蘇聯聯盟中的矛盾,在垂死掙扎中,還指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于兩種社會制度引起內訌而瓦解。所幸的是,反法西斯戰線的領導人以其戰略智慧,在徹底消滅希特勒之前,沒有使矛盾激化。
然而,不幸的是,反法西斯戰爭剛剛結束,兩種社會制度就日益對抗,進入冷戰。丘吉爾本人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不可逾越的障礙就像“鐵幕”(Ironcurtain)一樣;對蘇聯這個“魔鬼”,無法用戰爭消滅,只能用其他方法“頂住”,防止蔓延。他呼吁“鐵幕”西邊的資本主義聯合起來,共同抵抗東邊的社會主義,進而發展成冷戰思維。雖然在短期內,實施了復興歐洲等計劃,卻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出于對社會主義的猜忌、仇視和對抗,展開激烈的軍備競賽,造成了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拒絕別國的有益經驗,犧牲社會主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阻礙其發展;通過掠奪別國發財,給別國造成了沉重的債務,造成了深刻的南北矛盾;在歐洲資本主義各國內部,也引起許多矛盾,無情地阻礙了發展,使其實力下降[7](pp.179-185)。
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迅猛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大規模運用于軍事和國防,任何現代戰爭都可能造成毀滅性的消耗和破壞,甚至會毀滅全人類。不論戰爭的結果如何,都和爭端各方預朋的利益完全相反,更和全人類的利益完全相反。比如,世界上,100萬噸級以上的核彈頭已有2萬多枚,其總爆炸力相當于200億噸TNT;如果其中1/4爆炸,其臨界水平就會使全世界完全毀滅。即使按照已簽署的裁軍協議,核彈頭仍然保持2萬枚,爆炸總當量仍在100億噸以上,更何況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又在展開。而1945年8月,美國投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其當量分別僅1.5萬噸、2.5萬噸TNT,就使幾十萬人喪生。顯而易見,今天,即使僅有一顆100萬噸級的原子彈爆炸,其毀滅力就是當年美國投在日本廣島或者長崎原子彈毀滅力的40~60倍,會殘害幾千萬甚至幾億人的生命——從潛在的威脅看,光是現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把地球摧毀幾千次;“核冬天”的預言絕不是危言聳聽!
物極必反。危機強迫人類自省:不論核大國通過核武器撈到的利益有多少,都會被其危害抵消得蕩然無存,并且使全人類面臨被毀滅的威脅。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絕不允許這樣的厄運發生。而從更廣闊的、客觀的視野看,比如,在經濟上,全球化進程中,世界貿易持續高速增長;國際范圍內資本流動巨大;跨國公司使各民族國家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賴、互相滲透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摧毀對方,也就摧毀了自己;一利俱利、一損俱損越來越多地成為共識。這使戰爭的性質和后果發生了逆轉:一旦發動戰爭,沒有贏家,只有輸家;對誰都不利,是雙輸。正如羅素幽默的那樣,光是從經濟角度看,任何一方發動戰爭,損別人,也害自己,是賠本的買賣;而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來看,危害更大更深。在國際關系中,隨著全球化迅速推進,由沖突走向合作,告別“零和博弈”而走向雙贏,日益成為主流,不論發達國家之間分割市場,還是全世界范圍的經濟貿易,都基本上不再訴諸于戰爭,而通過市場競爭和外交談判。在外交領域,各國積極推進互利合作,特別是從“9·11”事件以來,各國對反對和打擊全球性的惡性犯罪和恐怖主義,正在形成新的合作框架和機制。在國際法領域,正在針對發動戰爭和使用武力,努力通過法律和制度使之非法化,進行限制和打擊。這種在全世界范圍里反對和打擊戰爭與非法武力的努力盡管不斷受到個別國家的挑戰,引起激烈的爭議和辯論,卻正在一步步地成為立意崇高的國際法原則之一。凡此種種,都使互利的時代精神在各種挑戰中不斷地清晰和強化起來,展現出樂觀的前景。
宏觀上,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各國經濟在國際化的專業分工中,互相滲透、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趨勢不斷加強。跨國公司、國際兼并、合作經營、股權國際化等形式迅速發展。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密切,互相依存、整體發展的程度不斷加深,以一國利益為中心的時代,逐步讓位于各國利益共存的時代。比如,1938年以前,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70%分布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而1945-1975年,主要資本輸出國向國外長期投資增長了約10倍,其中,發達國家相互投資占其全部對外投資的70%;1945-1980年,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累計達6000億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總額的12倍;80年代初,美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全部對外投資的75%,英國的同一數字是80%。1972-1980年,日本的同一比例是45.3%,1981-1984年間上升到50%。1980年以來,這個趨勢更加強化和突出。而投資是為了利益;互相投資,是因為互利,每個國家都能從全球性的交換中獲益。互相投資越多、市場和交易量越大,財富的增殖也越快,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的增長就越快。正是因為潛在而巨大的利益,驅動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不斷擴大的國際經濟貿易體系,從而進一步推動互利的發展。
微觀上,一些跨國公司順應全球化浪潮,實行互利戰略,而超常發展。康柏電腦公司強勁的發展就是個典型。該公司創建于1983年,在全球計算機生產企業中。1991年排名第18,1992年是第16,1993年第8,1994年第7;1995年,居IBM、富士通、惠普、NEC之后,是第5位;2000年,躍居全球第1,取代IBM成為世界第一大計算機制造廠商。康柏公司在短短時間內,能夠成為世界同行業第一,其發展戰略就是互利:和同行合作,特別是善于和其他世界頂級公司建立緊密的利益關系,結成最廣泛的戰略同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術和市場,使戰略型合作伙伴日益增多,從而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這是它的“遺傳密碼”,是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的保證之一。它創立之初,就是靠和IBM合作生產兼容機而立足市場的;后來,它又和微軟公司合作生產軟件,和英特爾合作生產微處理器、CIS-CO系統、數據設備;還和諾維爾、費謝爾·普萊斯、德國SAP公司結成穩定的“戰略伙伴”。曾有人預言說,SAP是它的主要殺手。然而,它卻通過“戰略伙伴”關系,通過互利機制,化干戈為玉帛,在巨大的市場風險和激烈的競爭中迅速成長。
20世紀后期以來,互利以其必然性從沉重的歷史教訓中日益凸顯,作用不斷加強,終于在“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迅速推進,成為時代精神中一個有力的音符。
三、互利:中華民族精神及其當代貢獻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在“天人合一”的宏大視野中,形成了“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民族精神。儒家認為,對各種異質的要素,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進行整合,就發展為“和”。它有更大的包容性、開放性、成長性,指向具有新質的、更高更廣的境界,為進一步大發展打開了道路;相比之下,把同一類要素簡單相加,哪怕加得再多,也只是“同”,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和實生物,同則不繼”[8](p.515)。道家則主張超越世俗的兩極或多極對立,從更高的層次上,使萬事萬物不斷地超越和升華,就能在更加寬廣深邃的境界上,達到新的統一,“得其環中,以應無窮”[9](p.15)。民間普遍崇尚“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儒家、道家的理論和民眾的智慧都追求在更高層次上謀求新的大發展,致力于就對立的多元要素進行整合,進入新的更大更完整的系統。這種智慧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凝聚成為偉大的民族精神。她對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促進世界和平與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有獨特的價值。
中華民族在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的當代實踐中,正在使互利的民族精神和偉大智慧進一步弘揚。
在中國國內,中國人民加大加快對外開放,進入世界經濟大舞臺,大力引進和利用外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和管理,不僅謀求中國的戰略利益,而且對東亞地區的繁榮、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對發達國家進一步發展,對世界和平,都有更大的戰略利益,對各方是互利的。
具體來說,對中國自己,掌握和推廣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形成先進的生產能力,帶動一批行業和企業的發展,勞動者增加收入,國家增加稅收,富民強國。對東亞,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地區,和日本、韓國及東亞其他國家之間,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增長很快,有力促進了東亞經濟發展,特別是對戰勝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做出了大貢獻。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可以提供直接援助、經驗借鑒,為世界3/4的人口脫貧致富,走出一條成功之路。對發達國家,中國作為巨大的市場,隨著其迅速發展和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對資本、技術、人才、商品的需要越來越大,促使這些要素在更大范圍里流動,減少發達國家之間因爭奪市場而日益激化的貿易摩擦,就為發達國家解決市場問題、經濟發展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市場。按照西方的就業標準,每出口5億美元,可安置1萬人就業。中國如果進口1萬億美元的設備,等于為西方創造了2000萬人的就業機會。這對于失業率很高的發達國家,是巨大的幫助。所以,在發展經濟、維護增進國家戰略利益方面,中國和發達國家有互補、互助、互利的一面。中華民族歷史上酷愛和平,現在更是制約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國和世界上一切和平進步力量合作,正在有力地推進各方在互利基礎上深化和擴大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協調發展,保證全球化健康發展,消除戰爭威脅,維護世界和平。這對中國,對其他國家和全世界,都是戰略利益所在,是互利的。
對和有關國家的關系,中國以平等、合作、互利作為基本原則,捍衛中國的戰略利益,又照顧對方的戰略利益,力求對有關國家和世界和平都有利,促進全球化健康發展。對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從各自和共同的戰略利益出發,從世界和平的戰略利益出發,求同存異,積極發展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對有爭議的棘手問題,包括對歷史上遺留的和鄰國的邊界問題,主張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上彼此讓步,尋求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決矛盾,積極推動互利合作;一時解決不了的,先放一放,在經濟、貿易、文化等領域,彼此讓步又互相合作,從更廣闊的空間實現各自的戰略利益。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集中反映著互利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在國際上,中國堅持平等、合作、互利的原則,積極促進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促進全球化向著有利于各國發展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健康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關系出現了新變化,和平與發展等問題突出起來。各國之間不僅有利益矛盾,也有共同利益,有互利的一面。比如南北關系中,差距越來越大,問題非常突出,嚴重阻礙世界經濟的發展。北方發達國家盡管越來越富,也面臨嚴重的經濟“滯脹”和嚴峻的再發展問題、發展速度問題,內部發展空間非常有限,其資本、貿易、市場都在找出路。而南方發展中國家越來越窮,如果沒有適當的發展,繼續窮下去,北方也沒有大的市場,其經濟也不能大發展。這說明南方的發展固然離不開北方的發展,北方的發展也離不開南方的發展,需要南方的發展;南北差距急待縮小,否則,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對世界各國都不利。因此,發展問題事關南方,也影響北方,是關系到全人類的大問題。中國從這樣的高度看待和解決發展問題,積極推進南北對話、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推動世界范圍的平等合作和互利。特別是針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歷史上遺留的很多主權爭端長期解不開,挑起好多爭端和武力沖突,中國反對打仗,主張用互利機制,對主權問題暫時擱置,以共同利益的紐帶致力于共同開發,合資經營,使爭端各方在互相讓步中,共同得利,至少不受損害。這樣能消除陳年老賬,消除爆發點,穩定國際局勢,維護世界和平。這對爭端雙方,對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1]馬漢.海權論[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
[2]喬洪武.互惠—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道德法則[N].光明日報,1993-9-1(3).
[3]徐顯明.公民權利和義務通論[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4]司馬遷.太史公自序[A].司馬遷.史記[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弗洛姆.人類的破壞性剖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
[6]伯特蘭·羅素.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7]黃鳳武.從丘吉爾的“鐵幕”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A].叢鳳輝.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C].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6.
[8]左丘明.國語[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王先謙.莊子集解[Z].北京:中華書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