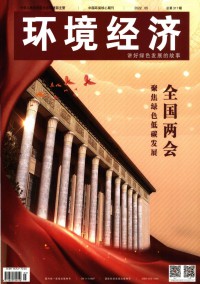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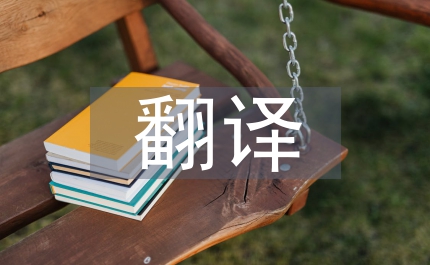
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范文第1篇
學(xué)弈
先秦:佚名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xué),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譯文及注釋
譯文
弈秋是全國最善于下圍棋的人。讓弈秋教導(dǎo)兩個人下圍棋,其中一人專心致志的學(xué)習(xí),只聽弈秋的教導(dǎo);另一個人雖然也在聽弈秋的教導(dǎo),卻一心以為有天鵝要飛來,想要拉弓箭去把它射下來。雖然和前一個人一起學(xué)棋,但棋藝不如前一個人好。難道是因為他的智力不如前一個人嗎?說:不是這樣的。
注釋弈秋:弈:下棋。(圍棋)
秋,人名,因他善于下棋,所以稱為弈秋。
通國:全國。
通:全。
之:的。
善:善于,擅長。
使:讓。
誨:教導(dǎo)。
其:其中。
惟弈秋之為聽:只聽弈秋(的教導(dǎo))。
雖聽之:雖然在聽講。
以為:認(rèn)為,覺得。
鴻鵠:天鵝。(大雁)
援:引,拉。
將至:將要到來。
思:想。
弓繳:弓箭。
繳:古時指帶有絲繩的箭。
之:謂,說。
雖與之俱學(xué):雖然這個人和那個專心致志的人在一起學(xué)習(xí)。
弗若之矣:成績卻不如另外一個人。
為是其智弗若與:因為他的智力比別人差嗎?
曰:說。
非然也:不是這樣的。
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范文第2篇
1、翻譯:謝安在寒冷的雪天舉行家庭聚會,和他子侄輩的人講解詩文不久,雪下得大了,太傅高興地說:“這紛紛揚揚的白雪像什么呢?”他哥哥的長子胡兒說:“跟把鹽撒在空中差不多可以相比。”他哥哥的女兒說:“不如比作風(fēng)吹柳絮滿天飛舞。”太傅大笑起來她就是謝安大哥謝無奕的女兒謝道韞,左將軍王凝之的妻子。
2、原文:謝太傅寒雪日內(nèi)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fēng)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范文第3篇
中國哲學(xué)本體思想下的翻譯本體探究
不同的翻譯學(xué)家對翻譯從不同角度有著不同的認(rèn)識。自從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以后,翻譯研究的領(lǐng)域由內(nèi)部轉(zhuǎn)向外部,研究的視角由原文轉(zhuǎn)向譯文,研究的方法由規(guī)定轉(zhuǎn)向描寫,研究的重心由語言轉(zhuǎn)向文化、認(rèn)知。除了翻譯界以外,越來越多的其他學(xué)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譯研究,翻譯的領(lǐng)域越來越大,翻譯是什么變得越來越模糊,如翻譯是科學(xué),翻譯是藝術(shù),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譯是什么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試圖從形而上的哲學(xué)高度探討翻譯本體問題。
中國古代農(nóng)耕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在人們眼里草木是人類賴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詩經(jīng)》的《大雅》中有“: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這里的“本”的含義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漸在有的典籍中,逐漸出現(xiàn)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會人事的說法。《莊子知北游》中說“:六合為巨,未離其內(nèi);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顧;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憫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萬物根據(jù)的含義。“本”還有事物的根據(jù)、根基或主體的意思。如《論語學(xué)而》中:“君子務(wù)本”。對“本”的重視,是農(nóng)耕社會中哲學(xué)研究的一個特色。“體”的最初的意義是身體,人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能近取譬”是中國先哲創(chuàng)建的哲學(xué)范疇和建立哲學(xué)體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學(xué)家十分關(guān)注與身體直接相關(guān)的感受和體驗。所以“體”首先與人對自己的直接體驗有關(guān)。《禮記大學(xué)》中說“:心微寬體胖”。《論語微子》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體之外“,體”還有“實體”“,形體”,“形狀”“,卦形”“,卦狀”的意思。《易經(jīng)系辭上》有“: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本體”二字,很早就出現(xiàn)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學(xué)中。其最初含義是“本來面目”“,本來狀態(tài)”。后來“本體”的含義擴展為“根本性狀”“,根本依據(jù)”“,根本源泉”等意義。唐代佛教經(jīng)典《大日經(jīng)》中有:“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這里的本體已經(jīng)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進入了無形之境。到宋代“本體”已經(jīng)成為哲學(xué)界普遍通用的范疇。張載在《正蒙太和》中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這里的“本體”指天下萬物本來恒有的狀態(tài),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學(xué)范疇的基本屬性。中國哲學(xué)中“,本體”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tài)。
東晉僧人道安,他在《摩訶缽羅蜜經(jīng)抄序》中指出,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來,佛經(jīng)翻譯必須要“案本”,而何為“本”,這是一個非常關(guān)鍵的問題。道安認(rèn)為,翻譯的目的正是因為人們不通異域之言,因而需要譯者傳達,使其通而曉之。由此看來,這個“本”指的是經(jīng)文“大意”。然而,從道安的“五失本”的表達來看,“本”又可以說是包括了內(nèi)容、形式及文體風(fēng)格的。一“失”指經(jīng)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經(jīng)文文體風(fēng)格的改變;三、四、五失指經(jīng)文內(nèi)容的刪簡。可見,道安對“本”的理解遠遠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對翻譯之“本”的闡釋中不自覺地把內(nèi)容、形式、風(fēng)格和意義結(jié)合了起來,認(rèn)為它們都是意義的組成部分。這在當(dāng)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點。這樣,形式、風(fēng)格、內(nèi)容和意義的關(guān)系構(gòu)成了翻譯的本體論即“翻譯是什么”的論題。然而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中國哲學(xué)在沒有發(fā)展到對本體有著充分認(rèn)識的時候,道安沒有能從正面找到翻譯的本體,而是從側(cè)面指出翻譯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譯內(nèi)容、風(fēng)格,抓住了翻譯的“根本”,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本體”對“根本”的重視。而近代的錢鐘書先生飽讀詩書,深諳中國國學(xué)之道。在中國哲學(xué)對本體有充分的認(rèn)識前提下,錢鐘書先生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翻譯是什么即翻譯的本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化境”。
“文學(xué)翻譯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zhuǎn)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xí)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fēng)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紀(jì)有人贊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zhuǎn)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致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yīng)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象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jīng)過翻譯似的。”從錢先生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翻譯本體的理解與中國哲學(xué)中“本體”的解釋不謀而合,翻譯的本體就是翻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本來狀態(tài)。無論“化境”能不能達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譯的本來狀態(tài)。在中國哲學(xué)體系下,本體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tài)。翻譯的本體是“化境”,可以說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根本狀態(tài),本來狀態(tài)。但從實際翻譯來看,受源語和譯語差別、文化知識等等因素的影響,會有道安說的“五不翻,三不易”現(xiàn)象,“化境”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實現(xiàn)。“五失本,三不易”從側(cè)面體現(xiàn)著翻譯的本體。而說翻譯是科學(xué),翻譯是藝術(shù),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等,都是翻譯本體的具體化,是本體的某個方面。
認(rèn)知視域下翻譯客體探究
從字對字翻譯,意對意翻譯,到動態(tài)對等,文本類類型,再到最佳關(guān)聯(lián),翻譯的對象由最初的靜態(tài)語言現(xiàn)象,到重視讀者反應(yīng),到被視為跨文化交際行為,這體現(xiàn)著人類認(rèn)知的不斷發(fā)展,由對世界(客體)的認(rèn)識,深入到主體的認(rèn)識,再到主體和客體之間關(guān)系的認(rèn)識。翻譯活動隨著人類認(rèn)知的發(fā)展不斷拓展,翻譯理論也經(jīng)歷了由文本為中心到讀者為中心,和文化的轉(zhuǎn)向,認(rèn)知轉(zhuǎn)向。翻譯的客體大概由詞、意義、意義及其語用范圍、意義及其文化、意義及語篇發(fā)展到概念內(nèi)容及識解能力。翻譯的客體發(fā)展過程也是人類認(rèn)知發(fā)展的過程,受人類認(rèn)知水平的決定,也是人類認(rèn)知發(fā)展的結(jié)果。翻譯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活動,各種語言有著不同的語法和特點,現(xiàn)有的翻譯理論都是以某兩種或幾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雖然語言不盡相同,但是語言背后的人類認(rèn)知本能是一樣的。隨著人類認(rèn)知水平的發(fā)展和認(rèn)知科學(xué)的發(fā)展,在翻譯理論呈現(xiàn)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局面下,認(rèn)知視角為翻譯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p#分頁標(biāo)題#e#
羅馬時代的“字對字”翻譯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人們用拉丁語最貼近的語法對等語替換希臘語的每一個單詞。這樣,羅馬人閱讀譯文時可以把希臘原文與拉丁譯文逐字對照。這與當(dāng)時人們對希臘源文的崇拜、敬畏有關(guān),也與當(dāng)時的翻譯范圍狹窄有關(guān)。當(dāng)時翻譯僅僅局限于經(jīng)典著作和宗教文獻翻譯。“字對字”的翻譯方法將單個的字詞作為了翻譯的客體。公元前1世紀(jì)的西塞羅和公元4世紀(jì)晚期的圣哲羅姆提出了“意對意”的翻譯,將“字對字”的翻譯客體拓展到了意義,包括語言的風(fēng)格和力量。奈達將翻譯客體拓展到意義及其語用范圍。奈達從語義學(xué)和語用學(xué)理論以及喬姆斯基的句法結(jié)構(gòu)理論獲得啟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術(shù)語提出形式對等和動態(tài)對等。功能主義學(xué)者霍爾茲-曼塔利將翻譯視為涉及文化轉(zhuǎn)換的“信息傳遞綜合體”。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慮到翻譯的語用和意符層面,以及各類話語和話語所屬不同社會的社會語言和意涵問題。認(rèn)知視角下,翻譯過程被視為有源語文本觸發(fā)的心理場景的激活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表現(xiàn)或刻畫該場景的目的文本的選取。翻譯的客體是概念內(nèi)容和識解能力。
翻譯客體的不斷演化,從不同側(cè)重點強調(diào)了翻譯主體指向、認(rèn)識和改造的對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義、文化、語篇等等。而概念內(nèi)容和識解能力將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蓋起來,實現(xiàn)了概念內(nèi)容和識解能力的譯文就實現(xiàn)了形式、意義、文化、語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對源語文本的心理場景的激活。概念內(nèi)容和識解能力是認(rèn)知語法的兩個術(shù)語,可以被借鑒到翻譯理論中。概念內(nèi)容由一系列的認(rèn)知域組成的,識解能力是人們用不同方式描繪或構(gòu)建相同場景的能力。認(rèn)知學(xué)法學(xué)家蘭蓋克認(rèn)為語法認(rèn)知觀必須建立在語義之上。翻譯同樣要建立在源言語和目的語語義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礎(chǔ)上。蘭蓋克指出意義是概念化的結(jié)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經(jīng)歷的任何一個方面,包括對物質(zhì)的、語言的、社會的及文化的等經(jīng)歷的理解。但他也強調(diào)對語義結(jié)構(gòu)作完整及確定的描繪是不現(xiàn)實的。語言意義都是開放的,在范圍上是百科全書式的,意義要依賴語境及對世界的百科知識來理解。語言的意義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義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類的世界知識上。意義包括語義內(nèi)容及人對該語義內(nèi)容的識解,而識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義是內(nèi)容和識解作用的結(jié)果。認(rèn)知域給我們提供了內(nèi)容,認(rèn)知能力給了我們識解。一個語言表達的概念內(nèi)容是由一系列的認(rèn)知域提供的。認(rèn)知域構(gòu)成意義的基礎(chǔ),但它們本身卻不是語言表達的意義。作為認(rèn)知主體,人們可以強調(diào)不同的認(rèn)知域,其結(jié)果是同樣的客觀事實不同的語義表達。在翻譯理解原文和譯文輸出時,對不同認(rèn)知域的強調(diào)通過識解的不同維度的側(cè)重來實現(xiàn),尋求譯文最大程度上對源語文本心理場景最大的激活。
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范文第4篇
伽達默爾認(rèn)為讀者對文本的解讀并不是一種向作者原意的回溯運動,相反,它是一種借助于文本而實現(xiàn)的此在的存在方式。伽達默爾認(rèn)為關(guān)鍵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實現(xiàn)過去真理與現(xiàn)時態(tài)生命的思維性溝通。溝通是伽達默爾最大的成就,也是他一生的追求,《真理與對話》強調(diào)對話和溝通是翻譯的真實存在,在翻譯過程中只有注重了對文本對話和真實的梳理,才能駕馭文本。
原著是作者通過對生命和生活的體驗和智慧的結(jié)晶凝結(jié)成的結(jié)果,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對人生的一種寫照,尤其是小說等大框架作品,更需要作者去發(fā)現(xiàn)自我,發(fā)現(xiàn)生活的本質(zhì)。這表明譯者在重新喚醒對原作者和文本意義的時候,也會把自己的思想灌注于他的理解中。哲學(xué)詮釋學(xué)代表伽達默爾認(rèn)為“理解的本質(zhì)不是施萊爾馬赫所說的對作者意圖的單方面理解、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由于理解的歷史性,理解應(yīng)該是相互理解,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理解的雙方,即作者和譯者有各自的視界。這種視界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歷史理解。源語文本代表的總是作者的視界,而譯者的視界是在其自身的時代氛圍中形成的。由于時間和空間的隔離,兩種視界肯定存在著一定差距。伽達默爾主張譯者應(yīng)在理解過程中,使兩種視界融合在一起,達到“視界融合”,從而使譯者和原作者都得到提升,到達一個全新的視界境界。因此,翻譯時已不是以文本為主體,而是以譯者為主體。
英國文學(xué)的代表作莎士比亞為例,莎士比亞是世界公認(rèn)的最偉大的劇作家,同時,莎士比亞也是詩人,他通過自己對生活的感觸和理解創(chuàng)作出很多優(yōu)秀的劇作,這些劇作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要考慮莎士比亞所生活的環(huán)境以及莎士比亞本人的思想活動,只有了解了這些全部譯者才能通過伽達默爾的闡釋學(xué)理論去實現(xiàn)對話的平等,才能夠真正還原作品原貌,盡量減少作為譯者自我的情緒和狀態(tài)。《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亞重要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深刻反映了威尼斯的商業(yè)活動和在這個社會的人情冷暖,同時,我們也要明白莎士比亞這部劇作的喜劇成分,如果你不了解這部作品的背景和莎士比亞本人的喜好,那么你就不會真正去發(fā)現(xiàn)這部作品的真實性。
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范文第5篇
關(guān)鍵詞:模糊語言學(xué) 文學(xué)翻譯 語言運用
引言
模糊的表達在語言表達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產(chǎn)生語言模糊的原因是由于思維變得模糊。語言模糊問題是當(dāng)前語言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從1965年美國學(xué)者提出相應(yīng)的概念之后,語言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對模糊語言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多,進而產(chǎn)生了模糊語言學(xué)。模糊語言學(xué)是運用模糊集合論和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的方法對語言的模糊性進行分析的一個過程,在對語言進行分析時,如果用完全精準(zhǔn)的方式對語言進行研究,往往很容易產(chǎn)生問題。尤其是在翻譯過程中,如果使用完全精準(zhǔn)的方式進行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語言翻譯的效果。
一、模糊語言學(xué)的產(chǎn)生以及與文學(xué)翻譯的關(guān)系
(一)模糊語言學(xué)的產(chǎn)生
1965年,美國控制理論專家扎德創(chuàng)立了模糊集合論,開始奠定了模糊語言學(xué)的研究基礎(chǔ),模糊語言學(xué)也開始產(chǎn)生。模糊理論的產(chǎn)生與語言學(xué)本身就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因為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模糊集合論是一個重要的工具,是對自然語言的模糊性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手段。在研究的過程中還延伸了學(xué)科的范疇,并且產(chǎn)生了相應(yīng)的著作。
(二)模糊語言學(xué)與翻譯的關(guān)系
在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研究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語境的改變。世界上的語言有很多種,為了促進文化的傳播與融合,需要對各種文化作品進行翻譯,于我國而言,最常見的翻譯就是將英文作品翻譯成為漢語,由于漢語的特殊性,在翻譯的過程中,如果采用直譯的方式,將會對作品本身的美感產(chǎn)生很大影響。因此在語言學(xué)的研究過程中,對語境的研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huán)節(jié)。語言中的語境的構(gòu)建可以說是一種內(nèi)向的語境構(gòu)建,涉及的范圍比較窄。西方社會發(fā)展過程中,認(rèn)為語言形式本身是交際中傳達信息的一種重要的方式,無論是什么樣的交際問題都可以通過語言進行闡述以及解釋,語言表達的是一種精準(zhǔn)的信息,比如傳遞出“我要工作”的信息,就說明說話人有十分強烈的行為目的性。但是語言之外的語境則呈現(xiàn)一種復(fù)雜、不確定的現(xiàn)象,語境是一種難以捉摸的東西。然而在中文表達過程中,一句話可以表達出幾種不同的意思,正是這種語言的模糊性,使得漢語變得更加有內(nèi)涵。在語言學(xué)的研究過程中,有學(xué)者提出語言學(xué)要研究的是對人腦中的各種語法進行內(nèi)化,內(nèi)化的語言并不是各種句子之間的集合,而是能夠生成不同語法句子的能力。而語言的模糊問題也是在語言應(yīng)用過程中產(chǎn)生的,將語言學(xué)研究過程中的語境排除之后,進行語言的研究就變得比較簡單。但是在中文表達過程中,語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翻譯是信息傳遞的方式之一,不僅是一種技術(shù),也是一種藝術(shù)。翻譯質(zhì)量的好壞對各種被翻譯作品在當(dāng)?shù)匚幕尘跋氯藗兊睦斫庥泻艽蟮挠绊憽T谕鈬膶W(xué)作品的翻譯過程中,翻譯的質(zhì)量參差不齊,尤其是一些作品在翻譯時往往只采用直譯的方式,使得很多作品的語義以及語境發(fā)生了改變,最終導(dǎo)致甚至很多翻譯在語句上不通順、錯別字等現(xiàn)象,嚴(yán)重時還能見到一些生僻詞匯或者與文章內(nèi)容完全不相關(guān)的詞匯。在翻譯過程中,加強模糊理論的運用,是提高翻譯質(zhì)量的關(guān)鍵。由于不同的語言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漢語在某些時候就體現(xiàn)出一種朦朧美,因此在對外國文學(xué)作品進行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加入模糊理論的運用,加強對各種語言因素的應(yīng)用。
翻譯研究流派眾多,盡管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但是翻譯研究學(xué)者大多認(rèn)為翻譯是一種文化交際和語言交際的活動,是用一種語言來表達另一種語言的重要方式,也體現(xiàn)了不同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正是由于不同的語言之間有不同的特性,因此在將作品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的過程中,往往就會產(chǎn)生語言的不確定性,即模糊性。語言的模糊性是語言的一個本質(zhì)屬性,在語言研究過程中對模糊理論進行運用,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在文學(xué)翻譯過程中,模糊語言的產(chǎn)生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一些抽象的詞語、一些沒有實際代表的詞語等,這些都可以被歸納為模糊語言的范疇。
二、文學(xué)翻譯的原則
翻譯是一項復(fù)雜的活動,而文學(xué)翻譯則更加復(fù)雜,由于文學(xué)作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不能完全按照刻板的方式,做到十分精準(zhǔn),毫無變化。在文學(xué)翻譯的過程中,必須要加強模糊理論的運用,要采用模糊理論對文學(xué)作品進行處理,從而體現(xiàn)出作品原作者的真實意圖以及想要表達的語境,在表達作者的意圖以及對語言進行還原的過程中,還需要產(chǎn)生優(yōu)美的語言形式。漢語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優(yōu)美的語言,在應(yīng)用的過程中可以對各種外國文學(xué)作品進行體現(xiàn)。在翻譯過程中如果忽略了翻譯語言的模糊性,則很容易導(dǎo)致翻譯作品出現(xiàn)生硬的現(xiàn)象,對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涵的體現(xiàn)帶來很大影響。
在對外國文學(xué)作品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掌握語言使用的原則以及規(guī)范,即使要使用模糊理論對語言進行推敲,以便使用最適當(dāng)?shù)恼Z言對作品進行體現(xiàn),但是從整體上來講,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對原著進行最大程度的尊重,一方面是在語言上進行尊重,另一方面要在文化背景上進行尊重。漢語語言文學(xué)是包羅萬象的,同時在使用方法上和語法、句法、詞法上也是十分復(fù)雜的,因此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可以為了美化語言的方式,采用一些模糊的漢語語言形式,但是需要在尊重原作品的前提下進行,對背景進行充分地了解,對文學(xué)作品本身的創(chuàng)作意圖進行了解,才能避免在翻譯的過程中出現(xiàn)一些比較低級的語法以及用詞錯誤。其次,在翻譯的過程中,其實是對各種文化進行轉(zhuǎn)換的過程,從外國文學(xué)作品到漢語文學(xué)作品,不僅是一種語言的改變,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背景的改變。外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尤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對特定元素的表現(xiàn)和接受都是很委婉的,因此在語言的應(yīng)用上,漢語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xiàn)出一種委婉以及模糊的性質(zhì)。在這個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充分注意和理解外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在進行翻譯時應(yīng)該要將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合理地轉(zhuǎn)換,為了做到模糊以及和諧,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對語言進行詳細地推敲,尤其是在涉及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內(nèi)容時,要在保持文化真實的基礎(chǔ)上進行
三、模糊翻譯的模糊性
模糊翻譯是翻譯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方式,其中包括語言上的模糊以及語境上的模糊等。比如對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的名著翻譯中,有一部為《The Price and the Pauper》,我國對這部作品進行翻譯時將其翻譯為《王子和貧兒》,再比如《Gone with the Wind》這部作品中,最后在我國比較流行的翻譯方式是《飄》,給人一種模糊的感覺,給人一種體現(xiàn)了主旨的感覺,飄,可以理解成為是人的漂泊不定,也可以理解成為靈魂上的一種飄渺。 再比如對于同一部作品中的一段話進行翻譯,其中一個翻譯是:“一會兒功夫,道路上就蓋滿了雪。四周景物全都又消失在昏黃的一團混沌之中,但見一片片雪花狂舞,天地渾然莫辨。”另一個翻譯是:“路一下子就封住了,周圍的一切都消失在一片昏黃的黑暗之中,鵝毛大雪在黑暗中飛舞著,天地連成了一片。”其中都使用了簡單的詞匯對環(huán)境進行了描繪,但是其中第一個翻譯中的詞匯更加具有意境,比如“狂舞”“渾然莫辨”等,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譯者運用模糊思維,藝術(shù)地再現(xiàn)了原著作中的一種模糊之美,因此使得作品更加有韻味。
在翻譯的過程中,一般說來,只要是忠于原文的翻譯都是直譯,也就是存意也存形的翻譯,直接翻譯是用一種語言直接代替另外一種語言的方式,不同語言之間的對等翻譯方式,在英文的翻譯過程中,就需要用一種語言的模糊詞去翻譯另一種語言的模糊詞。在翻譯的過程中,有的時候會加上注釋,有的時候沒有注釋,直接進行翻譯,直譯的目的是為了保留原文中的異國情調(diào)及源語文化意象。如果文學(xué)翻譯過程中能夠有注釋,則可以對作品的意圖進行更好地體現(xiàn),但是有的時候可能會產(chǎn)生翻譯作品比較冗長的情況,不便于讀者的閱讀。因此為了使得讀者有更好的閱讀體驗,可以不進行注釋。如果只是與原文的內(nèi)容比較類似,但是與原文的形式不相同的翻譯都可以成為意譯,也就是存意失形的翻譯,對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翻譯進行定義時,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度”的問題,這個度中本來就存在模糊性,無論是直譯還是意譯,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且任意一種翻譯都必須要符合譯語的規(guī)范。比如對于一段話的翻譯是“遇到綿羊是好漢,遇到好漢是綿羊”,這是一種直譯方式,而欺軟怕硬則屬于意譯。在翻譯的過程中采用變異的翻譯方法指的是利用一種語言中的模糊的詞匯對另一種語言中的相關(guān)概念進行標(biāo)示,在翻譯時用另一語言的非對等詞來表達相同的概念。這種變異的翻譯方法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對作品的意思進行體現(xiàn),不能違背語言想要真實表達的意圖。
結(jié)語
模糊語言是語言學(xué)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文學(xué)翻譯過程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于語言的模糊性是語言的一種本質(zhì)屬性,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對模糊理論進行運用,有助于對文學(xué)作品的美進行挖掘,從而獲得更多優(yōu)秀的文化作品。語
參考文獻
- 學(xué)奕文言文翻譯
- 學(xué)奕課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