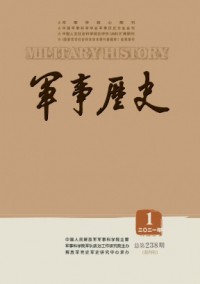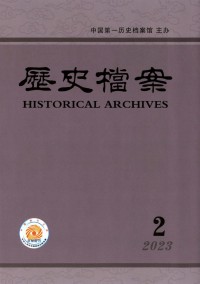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范文第1篇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學研究》、《哲學動態(tài)》編輯部和南開大學哲學系共同舉辦的“第七屆哲學創(chuàng)新論壇”在天津舉行。與會學者六十余人圍繞“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這一中心議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現(xiàn)將會議中呈現(xiàn)的各種新觀點、新見解評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觀”為焦點的論爭是歷史的延續(xù)
當前哲學研究中以“唯物史觀”為焦點的一系列論爭是歷史的延續(xù),圍繞對“唯物史觀”的闡釋和理解、逐步推進哲學的深入研究始終貫穿于傳播和發(fā)展的整個過程。
考察哲學在中國的發(fā)展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景源研究員指出“唯物史觀”一直是哲學研究中的重點,更是難點。他認為,回顧學術史,以信仰唯物史觀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徹底把握了唯物史觀的理論本質;認定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也不等于會用它來正確分析事物和問題;口頭上宣傳唯物史觀,實際上可能還固守于傳統(tǒng)的哲學的解釋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認歷史唯物主義,但不了解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合理形態(tài)的辯證法。揭示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有關唯物史觀的認識,對我們今天準確理解“唯物史觀”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
回到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早期,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波副教授指出,當時恰逢思想自由時期,因而招來方方面面的批評。一開始唯物史觀就沿著兩個向度展開:一是對唯物史觀本身的批評;二是對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適用性的批評。但是,針對各種批評,信奉唯物史觀的人們也做出了種種辯護。可貴的是,此時圍繞唯物史觀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評與辯護,已經蘊含著唯物史觀偏重物質因素、凸顯經濟的決定性、忽視倫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觀的時代局限等學理性問題。對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早期歷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紹,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zhàn),也有助于對唯物史觀的進一步研究。今天我們意欲對唯物史觀做出新的更為深入的闡釋,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源頭,盡可能地了解當時的總體情況和細枝末節(jié),從而幫助我們對唯物史觀研究在當今中國的走勢做出審慎而清醒的判斷。
近些年來,“唯物史觀”已經在學界的爭論中逐漸成為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求是》雜志社李文閣對這一爭論的過程予以綜合考察,并進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在今天引起廣泛爭論的原因。他認為,對于創(chuàng)始人而言,歷史唯物主義從來就不是什么“學問”,而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理論武器。這樣一種理論定位使得歷史唯物主義與現(xiàn)實和革命實踐緊密聯(lián)系起來,因而那些致力于無產階級解放的后來者就不能無視、越過這樣一種理論,必須根據(jù)時代進步“發(fā)展”之,根據(jù)形勢的變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見”、“偏見”,必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和爭論。既然爭論在所難免,那么我們如何看待今天這場有關“唯物史觀”的爭論呢?李文閣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們有關唯物史觀的討論置于唯物史觀產生以來的歷史長河中、置于時代的巨大變遷中來考量。從19世紀末到今天,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主要發(fā)生了四次大的爭論:第一次是列寧和葛蘭西、盧卡奇、科爾施等早期的西方者與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爭論;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與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lián)教科書派的爭論;第三次是以法蘭克福學派和薩特為代表的人道主義與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科學和以科亨為代表的分析的之間的爭論;第四次是在中國發(fā)生的在主張改革的反教條主義者與反對改革的教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前三次爭論是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個問題展開的,在中國發(fā)生的第四次爭論則是圍繞著“中國的發(fā)展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道路”問題展開的。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問題有兩個前提性的理論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會主義”。今天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爭論實際上主要是圍繞這兩個理論問題展開的。
從以上的探討可以看出,對于當前我國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我們應該用長遠的眼光、廣泛的視界來審視,不僅應將其置于歷史上幾次爭論的背景中予以關注,更重要的是將其看作是我們當前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我們在學術研究中自覺地融入歷史和現(xiàn)實的視野。
二、“唯物史觀”在當代的新闡釋和新發(fā)展
以“唯物史觀”為焦點的論爭在當代呈現(xiàn)出來的整體趨勢可以用一種總體性面相來概括:重釋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在立足當今中國現(xiàn)實、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釋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各種觀點的交互碰撞。無疑,異彩紛呈的觀點共享著一個前提:不滿足于現(xiàn)有國內外學者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闡釋。
馬克思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并非呈現(xiàn)為概念清晰、邏輯嚴謹、完整系統(tǒng)的現(xiàn)成體系,因此重新闡釋歷史唯物主義,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解讀。北京大學聶錦芳教授運用其馬克思文獻學研究的豐富成果,重點解讀了《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費爾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個段落。他的具體方法是將原來的段落順序打亂,以文本中反復出現(xiàn)的核心范疇“現(xiàn)實的個人”、“共同體”及其相互關系的辨析為線索,重新組織其論證層次和邏輯結構,從而獲得了馬克思有關“現(xiàn)實的人”與“共同體”關系的新見解:“現(xiàn)實的人”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但是在歷史的演進中社會的主體卻不是“現(xiàn)實的人”而是他們所屬的階級;每個個人迫于生存條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約而形成共同關系,進而結成共同體,但其個體和自由卻又受到了共同體的制約。從“現(xiàn)實的個人”的角度來衡量和檢視社會,也即以“現(xiàn)實的個人”的個性和自由是否得到顯現(xiàn)及顯現(xiàn)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動”是否參與以及參與的程度來關照歷史,將會非常鮮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體”、“現(xiàn)代市民社會”、“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的變遷軌跡。只有個人的“自主活動”參與、滲透到生產交往形式交織而成的社會結構中,才能實現(xiàn)上述三種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真正轉變。這種有關馬克思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會形態(tài)學說。從更大范圍來說,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僅是社會歷史理論探究的重要議題,而且是關乎每一時代個體生活態(tài)度、行為以及社會發(fā)展的價值導向問題。還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之后,對“現(xiàn)實的個人”與“共同體”關系的思考一直是馬克思社會實踐和理論建構的中心線索。因而,回到文本尋找馬克思歷史的、邏輯的論證與當代實踐的內在關聯(lián),必然是一件既有現(xiàn)實意義而又緊迫的事情。
重新闡釋歷史唯物主義僅僅回到馬克思經典文本的研讀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重新 研讀這些文獻?這就需要我們在基本理念與研究方法上實現(xiàn)新的突破,從而能夠在更深層次上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對此,北京大學仰海峰教授認為,今天重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一方面是為了深入理解馬克思的哲學理念;另一方面是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理念來面對當代的問題,這就決定了重釋歷史唯物主義必須要具有當代的歷史與文化視野。這種當代視野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文化。馬克思面對的是剛從封建社會中脫胎而出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構成了這一社會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紀后期,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競爭轉向了組織化的社會階段,以福特制為基礎的現(xiàn)代大工業(yè)生產取得了主導性的地位。到20世紀60年代,以電子技術為主導的后組織化生產階段登上了歷史舞臺。在這三個不同的階段,資本邏輯都體現(xiàn)各自的一些特征。這意味著不可能簡單地以歷史唯物主義來面對歷史。重釋歷史唯物主義就必須揭示當代社會的內在結構及其歷史變遷。另一方面,在這三個不同的階段,西方社會的文化理念也發(fā)生了相應的變化。盧卡奇與法蘭克福學派面對的是大工業(yè)生產的資本主義,而后面對的是后組織化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我們必須揭示這種社會變化與文化理念變遷之間的內在關系。這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在當展歷史唯物主義時必須加以探索的問題。
如果從上述意義上來理解和發(fā)展歷史唯物主義,那么立足當今的“信息時代”,對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唯物史觀理論確立的前提和方法進行全面反思,進一步分析和提煉它在信息時代與時俱進的新發(fā)展,我們會有許多新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院孫偉平研究員認為,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fā)展和廣泛應用,特別是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因素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意義的增強,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發(fā)生引人注目的變化,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正在來臨。信息等無形資本的可共享、可傳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質,至少對傳統(tǒng)的以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產關系為標準劃分社會形態(tài)的理論提出了理論上的挑戰(zhàn)。在信息社會中,先進生產力應與哪些因素相聯(lián)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創(chuàng)造者是否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擁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傭者、白領工人在生產中的地位如何?他們是否仍然屬于無產階級陣營?以信息為重要資源的社會將走向何處?這些現(xiàn)實問題已經構成了對唯物史觀的新挑戰(zhàn),這就要求我們特別重視研究唯物史觀的方法,從信息的特質出發(fā)推動唯物史觀的創(chuàng)新。
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要想有新的發(fā)展,同時還要結合和借鑒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將這些成果納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之中,我們才能真正實現(xiàn)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闡釋,同時真正地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面對當代的歷史與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孫美堂教授就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引入了“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成果,同時借鑒庫恩的“科學范式”理論對當今歷史唯物主義主義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幾點看法。他指出,相比經典物理學,復雜性科學在研究范式上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從線性的決定論思維模式轉向不確定性、隨機性的開放式思維。運用復雜性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唯物主義目前主要體現(xiàn)在西方的研究中,表現(xiàn)為對歷史本質主義的解構。當然從這種范式出發(fā)研究歷史唯物主義,還可以從以下一些問題逐步深入:歷史的本質是固定的還是生成的?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與路徑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是決定式的還是隨機性的?歷史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封閉的系統(tǒng)還是開放的系統(tǒng)?評價歷史的尺度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等等。黑龍江大學雋鴻飛教授則選擇“歷史哲學”這一視角切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這樣一種理論視角的獲得,首先應該澄清有關歷史哲學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問題,如什么是歷史的時間、歷史的進程、歷史的規(guī)律、歷史的意識等基礎性問題。作為這種研究視角的推進,其次要在對歷史哲學的深入理解中獲得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經對歷史的意識進行了一種生成論的闡釋:從生成論的視角來看,意識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歷史的進程之中通過人的對象性的實踐活動現(xiàn)實地生成的。所謂歷史意識,不過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識,是人對自身存在的意識。
還有一部分學者通過與其他理論問題的關聯(lián)性展開自己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思考和闡釋,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豐富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闡釋。中山大學劉森林教授通過對“虛無主義”的考察,進入了有關歷史唯物主義與虛無主義之間關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對虛無主義的三個語境進行了仔細辨別和梳理,即施特勞斯所謂的特殊的德國現(xiàn)象、尼采所謂的柏拉圖主義和認定世界是完全墮落和虛無的諾斯替主義。在對尼采虛無主義闡釋的基礎上,他重點研究了第四類虛無主義,即掙脫了柏拉圖主義、歷經新價值創(chuàng)造后最終否認一切存在之真實意義的徹底虛無主義。現(xiàn)代文化中自然與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對個別性的推崇,被施蒂納極端化后與馬克思發(fā)生沖突,再加上通過黑格爾與諾斯替主義的鏈接,使馬克思與虛無主義發(fā)生了雙重關聯(lián)。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保持了價值與意義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學維度,重新思考并確立了超驗價值的路徑和根基,從而在保留形而上學精神追求的同時遏制了徹底的虛無主義。北京師范大學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國思想史中考察德國“歷史主義”傳統(tǒng)對馬克思產生的深刻影響,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本質上是關于存在的歷史性的科學。馬克思為什么會如此關心“歷史”?他所說的“歷史”究竟意味著什么?其與歷史主義思潮有著怎樣的關系?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具有自己的獨特內涵,使之區(qū)分于一般意義上的歷史主義,也并不是波普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首先,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建立在對存在的歷史性規(guī)定基礎之上,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tǒng)一;其次,馬克思歷史主義的本體論基礎是唯物主義的;再次,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確實承認了歷史的一定的客觀性和可認識性,正是這種歷史主義使我們有超越普遍主義、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對立的可能。
綜觀以上有關“唯物史觀”在當代的新闡釋和新發(fā)展,文本研究的路徑和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突破同樣重要,同時多學科成果的借鑒豐富了重釋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關聯(lián)性問題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當代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然而,還有一個領域或視角的研究所獲得的欣喜成果是我們不容忽視、并且應該特別予以關注的,即政治哲學研究對于“唯物史觀”當代闡釋的推進。
三、“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的研究
前述有關“唯物史觀”的新理解無形中推動著當代政治哲學的建構;與此同時,我國政治哲學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一定意義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觀”的理論空間。因而,怎樣理解和推進政治哲學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學與唯物史觀的關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觀的重新理解。 南開大學陳晏清教授特別指出,“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兩個方面研究的結合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種結合許多關鍵性的問題難以解決,這兩個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難以向前推進。比如唯物史觀是否僅僅是一種揭示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理論,僅僅是一種認知理論,是否同時還有規(guī)范性的理論維度?如果沒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夠與作為一種規(guī)范性的政治哲學關聯(lián)起來,怎么能夠成為政治哲學的方法論基礎;在涉及到權利、民主、正義這一類規(guī)范性問題時,話語權為什么曾經總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學特別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手里,而哲學則處于長期的失語狀態(tài),馬克思在哲學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類問題中掌握話語權?與此相關的是,人類解放與政治解放的關系問題,唯物史觀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的實質意義是什么?在著力建立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我們重新思考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我們還有沒有政治解放的任務或屬于政治解放范疇的任務?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不能超越市場經濟的階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務?我們在什么意義上和應當經過什么樣的途徑超越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狹隘途徑,更進一步的追問可能是在當今特殊的時代條件下,政治哲學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思考和探討相同的問題有時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結論,那么與自由主義的根本區(qū)別在哪里?又比如說,觀察政治活動的文化視角和社會視角是什么關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學強調文化視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這種文化視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觀強調深入經濟生活的社會視角的原則性區(qū)別在哪里,我們應該怎樣完善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才能更加適用于關照當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是當今政治哲學不可回避的問題,也是在探討唯物史觀的當代意義和當代闡釋的時候不可回避的問題。
明確了兩者研究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之后,更應該探討的是如何在學術研究的實踐中發(fā)揮這種“結合”所產生的思想力量?南開大學李淑梅教授通過考察馬克思創(chuàng)立和完善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指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包括兩個基本向度:一是揭示處于一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社會本質和規(guī)律;二是揭示歷史發(fā)展的一般進程和規(guī)律。前者主要聚焦于歷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別是現(xiàn)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對其進行認識,屬于社會政治哲學的研究內容;后者則放眼于人類歷史長河,是一般意義上的唯物史觀。南開大學王新生教授認為只有從深化哲學基本理論的意義上理解我國當前的政治哲學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這一正在興起的領域哲學的意義和價值。首先,近代以來政治哲學的任務實際上就是整個哲學的時代任務,而在出現(xiàn)之前,這一任務主要是在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完成的。其次,我們必須肯定一個事實,在的發(fā)展史上,它的理論始終是與作為主流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的對峙中發(fā)展起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馬克思哲學的變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義的過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正義范圍內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視野,也就從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來的哲學通過政治正義為人的自由規(guī)定的限度。這是一種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類解放基礎之上的全新哲學觀。它的另一個層面是其現(xiàn)實性層面,即對現(xiàn)實生活的正義關懷,而這一關懷需要通過對現(xiàn)實政治制度正義性的肯定得到落實。政治哲學從其歷史主義出發(fā),在理想性正義原則與現(xiàn)實性正義原則、終極自由與現(xiàn)實自由之間建構起張力關系。這是破解現(xiàn)代人自由秘密的鑰匙。
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范文第2篇
關鍵詞:自然觀;生態(tài)中心主義;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生態(tài)學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對全球性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問題,西方綠色思潮批判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反生態(tài)性,他們試圖用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或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取代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以此走出生態(tài)困境。生態(tài)學者通過揭示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缺陷,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展開了有力的辯護[1]。本文旨在系統(tǒng)地論述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及其理論特質。
一、生態(tài)學對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生態(tài)中心主義以利奧波德、羅爾斯頓和奈斯為代表,他們在自然觀上堅持自然價值論以及自然權利論,反對一切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與自然和諧共處[2-4]。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的上述主張受到了生態(tài)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們不僅揭示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后現(xiàn)代特征,生態(tài)學者同時批判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探尋生態(tài)問題的理論主張。
第一,生態(tài)學者揭示了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的理論困境。生態(tài)學者指出,自然價值論面臨著如何從事實認知推出價值判斷的理論難題。在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看來,自然的價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觀存在的,正因為自然價值的客觀存在,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一般的倫理關系。基于此,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認為完全可以從“是”中推導出“應該”來,因為 “實然之道蘊含著它的應然之道”[5]。生態(tài)學者指出,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把價值等同于事實,這是他們最根本的理論困境。事實和價值存在著聯(lián)系,并非截然兩分,但是生態(tài)中心主義把它們等同起來,是不可取的。不僅如此,生態(tài)中心主義必須論證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客觀性。為此,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把生態(tài)系統(tǒng)構成要素的價值等同于它們的存在本身,這種論證方法不僅犯了前面所說的把價值論等同于存在論的錯誤,而且把自然作為評價主體去評價價值的內在屬性,這是不可能作出客觀評價的。除此之外,生態(tài)中心主義對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客觀性的論證并不是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和嚴密的推理基礎上,而是歸結于人的直覺,這種作法很難保證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性。除了上述難題外,生態(tài)中心主義還需面對如何定義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挑戰(zhàn)。在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那里,這兩個概念沒有嚴格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在定義自然價值概念時,他們要么認為自然價值就是一種“內在價值”和“客觀價值”;要么認為自然價值是指自然物的內在結構和屬性;要么認為自然價值就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對于什么是自然權利,他們強調非人類存在物具有與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權利和自利在內的道德權利,這種道德權利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可見,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把本屬于人的價值和權利概念不僅做了寬泛的解釋,而且推廣到非人類存在物上,但這種嘗試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態(tài)學者指認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具有后現(xiàn)代特征。生態(tài)中心主義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理性主義,反對科學技術,使其理論具有鮮明的后現(xiàn)代特征。對此,生態(tài)學者展開批判性分析。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生態(tài)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強烈反對,具有后現(xiàn)代反主體的特征。人類中心主義本身并沒有錯,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態(tài)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勢必會帶來各種反人道主義的體制。其一,在對待人類理性方面,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指認生態(tài)危機緣起于人類理性的驕橫和對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須消解人類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觀念。生態(tài)學者一方面強調不能消解理性主義,而是應該探討如何正確地發(fā)展理性主義,使理性主義的優(yōu)勢充分體現(xiàn);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著對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識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對待科學技術方面,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目睹科學技術在現(xiàn)代社會中使用產生的諸多負面影響,他們反對科學技術,主張放棄技術,使人類退回到前技術時代。生態(tài)學者批判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反技術主義傾向,強調應該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具體的社會結構中看到科學技術所帶來的消極作用和負面影響。可以說,當今社會的生態(tài)危機根本不是科學技術本身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以及這種制度對科學技術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機。
第三,生態(tài)學批判生態(tài)中心主義分析和解決生態(tài)危機的理論主張。生態(tài)中心主義把生態(tài)危機產生的根源歸咎于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上的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提出要解決生態(tài)危機,必須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自然價值”和“道德權利”。對此,生態(tài)學者展開了嚴厲的批判。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生態(tài)中心主義將生態(tài)問題的根源歸咎于個人對環(huán)境的價值觀和態(tài)度,這種觀點是非歷史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即生態(tài)中心主義把自然看作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根本沒有看到自然的社會歷史性;把生態(tài)問題唯心主義地歸結為世界觀和價值觀問題,看不到生態(tài)問題背后所隱藏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因此無法真正找到產生生態(tài)問題的根源。生態(tài)學者指出,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中去探尋生態(tài)危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伙同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發(fā)達資本主義向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實施非正義的“生態(tài)掠奪”等才是全球生態(tài)危機產生的罪魁禍首。生態(tài)學者不僅批評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對生態(tài)問題根源的探尋,而且批評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對生態(tài)問題的解決方式。對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來說,未來社會生態(tài)問題的解決只需要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即用一種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看待自然以及自然與人的關系,培養(yǎng)一種對大自然的“生態(tài)意識”。福斯特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當今最緊迫的問題并非改變人類的價值觀,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正義性,打破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權力關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決生態(tài)問題,在一個非正義的社會制度下,即使個體的生態(tài)道德得到明顯提升,也無益于生態(tài)問題的根本性解決。同樣,戴維?佩珀也認為,生態(tài)中心主義過分地迷戀個人的態(tài)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并把它們看成是促進社會變革、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主要動力,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現(xiàn)有社會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決生態(tài)問題所面臨的巨大阻力。
總之,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抽象地和非歷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忽視了生態(tài)問題產生的社會現(xiàn)實根源,因而無法在實踐中找到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生態(tài)學對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生態(tài)學者不僅批判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而且批判了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主要以墨迪的“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和諾頓的“弱式人類中心主義”為代表[6-7]。生態(tài)學者指出,無論是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弱式人類中心主義,都具有鮮明的內在缺陷,這些內在缺陷決定了它不僅依然是一種與資本緊密聯(lián)系的近代機械自然觀,而且不能真正解決生態(tài)問題。
第一,生態(tài)學者揭示了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內在缺陷。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無論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如何鼓吹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長遠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根本無益于生態(tài)問題的解決。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堅信“生態(tài)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由此可見,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內在組成部分,這種內化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僅不能解決生態(tài)危機,而且有可能與資本相結合加劇生態(tài)問題的產生。此外,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整體利益在現(xiàn)實中是無法實現(xiàn)的,因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類整體利益。在現(xiàn)有資本全球權力框架中,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打著人類整體利益的旗號,實則維護著以資本為核心的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人類整體利益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它是一種裸的地區(qū)中心主義和階級中心主義。不僅如此,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要求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全球權力范圍內是無法真正落實于實踐來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之所以這樣,不僅是因為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長遠利益虛無縹緲,無從實現(xiàn),而且當代全球范圍內的生態(tài)問題實質上是資本全球化的產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依仗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優(yōu)勢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生態(tài)殖民主義”,加劇了生態(tài)問題的惡化和社會不公正。生態(tài)學者強調,探尋生態(tài)問題需要全球性視野和全球性行動,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對虛無縹緲的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他們提出的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理論主張只可能是紙上談兵。
第二,生態(tài)學者指認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實質是一種近代機械自然觀。在對待自然問題上,近代機械論明確指出,自然是上帝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是一個按照客觀數(shù)學規(guī)律運行的冷漠的和無趣的世界。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僅認為自然對人類而言只具有工具價值,而且認為自然只是獨立于人之外的客體,完全忽視了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特征。由此可見,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在對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種近代機械自然觀。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近代機械自然觀繼承了西方哲學中主客二分的認識傳統(tǒng),指認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就是一種主客關系。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與自然關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終究要受到理性思維的制約,否則生態(tài)問題隨之出現(xiàn)。可見,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所理解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只不過是一種建立在人類利益和需求基礎上的,控制與被控制的主仆關系,它仍然沒有跳出傳統(tǒng)哲學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對待科學技術問題上,近代機械自然觀十分推崇科學技術的作用,甚至把科學技術的進步等同于社會的進步,但是它沒有關注到科學技術運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雖然注意到了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但它堅信只要以人類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過技術進步和技術革新就能夠解決生態(tài)問題。生態(tài)學者指出,無論是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還是近代機械自然觀,他們都是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和歷史條件抽象地談論“控制自然”觀念和科學技術的效應問題,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觀念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與資產階級“控制人”的觀念緊密結合的,因而不能正確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內涵,無法對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本質作出正確的評價,正是在這一點上,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和近代機械自然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態(tài)學批判性地分析了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與生態(tài)危機。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一樣,缺乏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它們僅僅從抽象的價值觀層面探尋生態(tài)問題,忽視了價值觀所依存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歷史條件,因而無法建立科學的生態(tài)自然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建立在資本利益之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它在探討生態(tài)問題時,只不過是一場“賊喊捉賊”的游戲。另外,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全球權力關系范圍內,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態(tài)學看來,人類本身并不是生態(tài)危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的全球權力分工。如果不變革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不打破這種以資本為核心的全球權力關系,一切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途徑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態(tài)學者指出,生態(tài)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不能離開人類立場,對此,格侖德曼、戴維?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侖德曼認為,人類在分析生態(tài)危機和反思對待自然的現(xiàn)代態(tài)度時,絕對不能夠放棄“人類的尺度”。 戴維?佩珀指出:“生態(tài)社會主義是人類中心論的(盡管不是在資本主義-技術中心論的意義上說)和人本主義的。”[8]休斯發(fā)現(xiàn)人類中心主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并斷言就是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9],與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同,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能夠為保護自然提供理論支撐。
生態(tài)學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批判了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內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資本利益基礎之上的抽象的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不僅無法解決生態(tài)危機,反而會引發(fā)生態(tài)危機。人類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打破資本全球的權力關系,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態(tài)危機的困境。
三、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
基于對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生態(tài)學明確指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生態(tài)學并不是對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具有生態(tài)意蘊,以此為基礎,生態(tài)學展開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
第一,生態(tài)學深入挖掘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生態(tài)意蘊。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對自然概念和人類社會與自然關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異化的觀點都包含著一種生態(tài)學的關注。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現(xiàn)代性的自然概念。格倫德曼認為,馬克思關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濃厚的現(xiàn)代氣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爾,并延伸到尼采。馬克思還發(fā)展了一種獨特的對待自然的現(xiàn)代性觀點,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種功用性的物體,它可供人類利用以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欲求。在這個物質世界中,人類為了生存,必須“控制自然”。自然在馬克思那里不是擬人的,它自身沒有目的,只是人類將其需要和欲求強加于它,因此人類對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種肆意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必須尊重自然的規(guī)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不僅強調自然概念的現(xiàn)代性,而且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戴維?佩珀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戴維?佩珀看來,人與自然不可分離,人類通常與自然處于一種統(tǒng)一和斗爭狀態(tài)中,自然往往以一種與人敵對的姿態(tài)存在著,人類既依賴于自然生存,又要與自然作斗爭。勞動是人類與自然發(fā)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類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毫無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時自然也被人化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相互改造,即當人類通過生產改變自然時,也改變他們自己,即人類的自然。隨著我們對自然改造的不斷深入,我們開始懂得應該去了解自然規(guī)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時發(fā)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的自然是一個社會概念,是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自然的異化意味著自然在人類社會實踐中從自身分離,它被視為一個社會產物的失敗,自然的異化其實就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異化。要消除自然的異化,就必須消除社會的生產方式對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規(guī)范自然對整個社會的用處。生態(tài)學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指認自然異化的根源在于社會生產方式,主張通過變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來消除自然的異化、解決生態(tài)問題,這種對自然異化的觀點是建立在人類-社會關系一元論基礎之上的。
第二,生態(tài)學者提出,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具有自然維度,而且具有文化維度。對此,詹姆斯?奧康納作出了詳細的論述。詹姆斯?奧康納指出,要充分重視自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并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向外擴展到物質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動性和自主運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雖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運動規(guī)律,自然本身的運動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詹姆斯?奧康納不僅強調自然的自身運動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強調自然界的自身運動規(guī)律和內在屬性還會對人類的實踐活動產生影響。除此之外,詹姆斯?奧康納認真考察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自然和文化維度。對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自然維度,詹姆斯?奧康納認為,自然系統(tǒng)不僅內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而且自然系統(tǒng)的內部發(fā)展趨勢和發(fā)展規(guī)律將會對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產生影響。不僅如此,自然系統(tǒng)的內在發(fā)展趨向和內在規(guī)律也會影響到社會形態(tài)和階級結構的形成和發(fā)展,并產生一定的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文化維度看,詹姆斯?奧康納指出,文化在前蘇聯(lián)那里只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這就直接導致了前蘇聯(lián)理論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社會勞動等概念缺乏一個文化的視角。從文化視角來看,不管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它們都與一定的文化規(guī)范和文化價值觀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傳統(tǒng)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fā)展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不僅是勞動力,而且包括勞動協(xié)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tǒng)下進行,并受到這些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此外,詹姆斯?奧康納還考察了社會勞動的自然和文化維度。他指出,人類的生產勞動既受到自然的影響,是一種物質性的實踐,又受到文化的影響,是一種文化實踐。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勞動被賦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觀規(guī)律制約著人類的生產勞動。另一方面,社會勞動被賦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會結構中的文化規(guī)定和文化實踐是社會勞動的建構基礎,而文化規(guī)定和文化實踐反過來又被社會勞動的形式所決定。
第三,生態(tài)學始終堅持歷史觀和自然觀的辯證統(tǒng)一。在生態(tài)學者看來,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與人類社會系統(tǒng)相互影響,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制約人類的實踐活動,而人類通過社會勞動調節(jié)和控制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生態(tài)學者所建構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正是建立在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辯證聯(lián)系的基礎之上的,以歷史觀與自然觀的辯證統(tǒng)一為其理論特征。生態(tài)學者指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規(guī)律是不依賴于人的一切意識和意志而獨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規(guī)律具有先在性、客觀性、制約性。人類只有不斷地認識自然,自覺地遵循自然規(guī)律,才會使自然向著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方向發(fā)展。在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人類通過社會勞動把自然帶入到他們的視野。人類不斷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會歷史性。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而且堅持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生態(tài)學者指出,“人類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會存在物”[10],人類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雙重特征。一方面,人類作為擁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體一樣,能夠僅僅存在于自然環(huán)境中,人類不僅依賴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規(guī)律的制約,人類還可以通過勞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滿足人類的需要。另一方面,人類同樣也是社會存在物,他有別于其他生物體,人類通過“有計劃的意識”活動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而且這種“物質變換”也發(fā)生在人類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生態(tài)學者強調,人類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人類不僅與自然發(fā)生關系,而且人類與人類之間也會發(fā)生關系,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與人類的關系始終貫穿在馬克思的整個著作中,人與人的關系受制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又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關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是辯證統(tǒng)一的。
總之,生態(tài)學者通過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以及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實現(xiàn)了人類-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自然-人類、人類關系的辯證統(tǒng)一。生態(tài)學者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歷史觀辯證統(tǒng)一,在此基礎上探討生態(tài)危機的根源和解決之道,體現(xiàn)了其鮮明的理論特征。
四、評論
生態(tài)學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缺陷。基于此,他們深入挖掘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生態(tài)意蘊,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維度重構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勞動等概念,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辯證統(tǒng)一。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堅持的是立場,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第一,生態(tài)學對西方綠色思潮自然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性質作了準確的定位。生態(tài)學把生態(tài)中心主義看作是具有后現(xiàn)代性質的綠色思潮,把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看作是建立在資本利益基礎之上的近代機械自然觀,而把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tài)批判,認為它是現(xiàn)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后現(xiàn)代性質體現(xiàn)在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科學技術,反對理性主義,主張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等方面;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之所以說是一種近代機械論自然觀,是因為它把自然看作是與人類相對立的客體,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其自然仍然是與資本結合在一起的。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是現(xiàn)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一方面是因為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不抽象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科W技術的運用,它反對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運用,強調生態(tài)危機的解決仍然需要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立場,強調科學技術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態(tài)危機的解決。另一方面是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強調人類對自然的“合理控制”,對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滿足人類的利益和需求基礎之上的,因此,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不反對經濟增長,不主張對工業(yè)實行限制,主張經濟理性與生態(tài)理性的統(tǒng)一。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論述與西方綠色思潮的自然觀有著原則性的區(qū)別,這對于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生態(tài)學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性質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野。
第二,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強調人與自然辯證統(tǒng)一的自然觀。無論是生態(tài)中心主義還是現(xiàn)代人類中心主義,他們都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之上,要么強調生態(tài)系統(tǒng)對人的制約和限制,要么強調人對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控制和利用,最終導致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根本無法解決人與自然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矛盾沖突。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那里是一個有機體,人類社會與自然是不可分離的,人和自然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態(tài)學反對脫離人類社會歷史的抽象自然觀,主張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所研究的自然是“人類歷史的自然”,自然的異化產生于人類社會中,具體地說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過程中。解決自然異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實現(xiàn)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因此生態(tài)學指出,要解決生態(tài)危機,實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就是要打破現(xiàn)存的資本全球權力關系和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走生態(tài)社會主義道路。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反對脫離具體的社會結構,單純從價值觀維度談論生態(tài)危機的根源以及解決之道,提出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正義性和非生態(tài)性才是生態(tài)危機的根本原因,其理論導向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tài)批判。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繼承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向度,推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現(xiàn)當展。
第三,生態(tài)學者主張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歷史唯物主義中,建構起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理論。他們不僅突出自然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自然對于人類社會的生產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tǒng)一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主張文化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生產力和協(xié)作方式,進而導致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進程。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視,把自然、社會和文化看作是一個辯證統(tǒng)一的有機整體,這不僅在理論上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文化、自然等領域的研究視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可以肯定地說,生態(tài)危機與我們忽視自然在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過分強調經濟基礎的作用而輕視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關系。因此,生態(tài)學所建構的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對于我們從哲學意義上思考生態(tài)危機頗具啟發(fā)性。
五、結語
總而言之,生態(tài)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針對的是西方綠色思潮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反生態(tài)性的詰難,其辯護的實質是強調基于立場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認識和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科學理論工具,以彰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性。生態(tài)學者與西方綠色思潮關于自然觀的爭論,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把握西方綠色思潮自然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性質;而且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自然異化的實質,倡導通過變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來消除自然的異化、解決生態(tài)問題,具有非常現(xiàn)實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 .生態(tài)自然觀研究[M].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 2014.
[2]勞倫斯?布伊爾.為瀕危的世界寫作:美國及其他地區(qū)的文學、文化和環(huán)境[M].岳友熙,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3]王正平.環(huán)境哲學――環(huán)境倫理的跨學科研究[M].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4]胡志紅.西方生態(tài)批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5]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哲學走向荒野[M].劉耳,葉平,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6]楊通進,高予遠.現(xiàn)代文明的生態(tài)轉向[M].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7.
[7]周玉玲.生態(tài)文化論[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戴維?佩珀.生態(tài)社會主義:從深生態(tài)學到社會正義[M].劉穎,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范文第3篇
關鍵詞:;歷史唯物主義;邏輯起點;勞動;工具;人類起源;勞動異化;《資本論》
中圖分類號:D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3)02-0005-04
一
探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歷史起點,必須首先考察人類歷史的起點。那么,人類歷史究竟從哪里開始呢?這個問題的確是歷史之謎。從《圣經》里的上帝創(chuàng)世說,到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異化論,不能說沒有進步,至少,黑格爾在對于自然界和社會的源頭關系上的理解,有其積極的合理因素。但從根本上說是依然不科學的。
隨著科學和人類思維進程的發(fā)展,才從根本上正確地揭示了從猿到人的進化方向,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發(fā)生論的高度上,科學地回答了人類歷史的起源問題。但是,由于唯物史觀的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的理論環(huán)境和政治氛圍下,主要著眼于唯物史觀思想體系的創(chuàng)立,而沒有像建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那樣,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體系(思想體系與邏輯體系是不同的,人們對于這種區(qū)別往往并不注意),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像《資本論》闡述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那樣,明確地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的問題。然而,《資本論》“邏輯地表述”方法(“邏輯地表述”與“表述的邏輯”也是不同的,人們對此也往往不注意),確定理論體系邏輯起點的一般的方法理論原則卻是普遍適用的。
根據(jù)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原則,理論界有些人研究的結果認為,勞動是歷史的起點,“勞動”范疇也就當然地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并從勞動出發(fā),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結構,得出“勞動”范疇是“打開社會奧秘的鑰匙”的結論(以下稱勞動起點論)。對于這個結論,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歷史是社會的歷史,社會是人類的社會,追溯歷史的起點,實質上是追溯人類的起點,而要科學地揭示人類的起點,必須著力澄清下述幾個問題:第一,人類提升的本質是什么?第二,歷史的定指含義是什么?第三,真正人的勞動究竟從哪兒開始?
第一個問題是人類提升的本質。筆者基于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原著的學習,認為人與動物的區(qū)別不在于外延擴大化意義上的“勞動”而在于怎樣勞動,用什么勞動。如果人類不以自己特有的勞動方式和特有的勞動手段,而僅僅是和勞動那樣運用自身的天然的生理器官去獲取生存資料,那它就不可能從動物中提升出來,成為宇宙之花、萬物之靈。史前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證明,在遠古時代,類人猿基本上還是一種樹上動物。后來分化為兩支:一支發(fā)展為森林古猿和巨猿,現(xiàn)代大猩猩就屬于這一類;另一支則沿著另一種方向發(fā)展,為了抵御猛獸的襲擊和適應獲取食物的活動(一般稱作適應性勞動),他們便開始利用石塊、木棒等自然物來彌補自身機體生理的天然器官的軟弱與不足,這種活動的長期繼續(xù),又使他們開始直立行走,由此便進行到了從古猿到人的“過渡生物”的階段,即“形成中的人”的階段。這種“形成中的人”與古猿的活動方式并無本質區(qū)別。經過漫長的進化過程,語言開始形成,人類才從獸類脫離出來,勞動工具在自然——社會共生態(tài)中,是人與動物、社會與自然的界碑。當“形成中的人”使用石塊、木棒和其他天然物的活物(這種活動可以叫做前人的適應性勞動)必然會發(fā)展到這樣一種限度,這時,如果不完善被使用的工具,即如果不過渡到勞動工具,這種活動就不可能進一步提高。而一旦跨出了這一步,原先使用天然的勞動就變成了制造工具并使用這些工具從事活動的生物了。這種情況大約發(fā)生在200~250萬年前。上述證明,人類提升的本質是“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而不能籠而統(tǒng)之的歸結為“勞動”。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歷史定指的含義問題。筆者結合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原著的學習,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歷史,是定指真正的人類的歷史,不能包括非人的歷史。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以人類社會的普遍本質與一般規(guī)律為對象的。在古猿進化為真正的人類之前,無論怎樣講都是“非人”,這種“非人群”還不是氏族或社會,它仍然是自然界尚未分化的一部分,只具有生物的自然本質,它所恪守的是自然規(guī)律,而不具有社會的本質和規(guī)律,所以,它不在歷史唯物主義特定對象范圍內。
第三個問題,即真正的人的勞動究竟從哪兒開始的問題。勞動起點論認為,勞動所以成為歷史的起點,因為勞動是人的起點;而勞動所以成為人的起點,是因為“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本身”。這樣一來,實際上就陷入了一個循環(huán)論證:什么是勞動?勞動是人改造自然的自覺的活動;人從哪兒來?人從勞動中來。這種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勞動,即真正的人的勞動究竟從哪兒開始呢?從“形成中的人”的活動特點來看,他們主要是憑借自身生理的天然器官,偶爾也使用石塊、木棒等天然“工具”,覓取天然的食物,它們在自然界中,完全受著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規(guī)律的支配。在他們未知使用石器以前,這些“構木為臺”、“錯木作穴”和“掘穴”的工作,都是無法實現(xiàn)的,充其可能,也只能是“構木為巢”,所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這種過渡生物的勞動,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在考察真正的人的勞動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制造工具的活動起初必定具有動物的反射形式。這種活動,就其性質而言,不會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自覺活動,而是一種反射性活動,并且是在純粹生物學聯(lián)合體的范圍內實現(xiàn)的。因此,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不是人,而是動物。
上述引證說明,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的活動不是“勞動”,所以,認為“勞動先于工具存在”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其實,馬克思對此早有論述。他曾明確地指出,真正的勞動不是開始于石制工具之前,而“只是有了用于新產品的最初的產品——哪怕只是一塊擊殺動物的石頭——之后,真正的勞動過程才開始”。[1]馬克思的這段話,闡述了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即正在形成中的人運用天然“工具”,例如一塊天然的石塊擊打另外一塊天然石頭,使之成為一塊比天然石塊好用一些的石器的活動或行為,還不能稱為勞動,只是在有了這“最初的產品”——石器之后,并且再運用這最初的工具作用于自然對象,改變自然物質的存在形態(tài),創(chuàng)造出某種使用價值,實現(xiàn)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的過程,才是人類的真正勞動。
換句話說,在最初的“反射性”活動所“制造”的“工具”未投入“新生產”之前,人的勞動是不存在的,只有把這“最初的”工具投入“新生產”時,真正人的勞動才開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沒有工具,人就不能從一般動物中提升出來,沒有人的勞動,也就不可能有歷史。從終極意義上說,工具不僅是人所以為人的起點,也不僅是人類勞動的起點,同時,也是歷史的起點。根據(jù)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原則,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應該是什么呢?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二
作為邏輯起點的范疇,不僅應與歷史的起點相統(tǒng)一,而且它本身還必須是以后歷史展開過程一切矛盾胚芽的潛在孕含體,即在這個抽象的范疇中,孕含著特定對象尚未展開的內在矛盾的全部豐富性。勞動起點論認為,“勞動”范疇孕含著歷史過程一切矛盾的胚芽,故以勞動為起點,構想了勞動對象化——勞動分化——勞動異化——勞動社會化——勞動自主化這樣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骨架”。本作者認為,以人類勞動的發(fā)展為主導線索,來分析歷史發(fā)展的邏輯,描述人類社會演進的“軌跡”自然不乏睿智,但仔細想來,不覺又發(fā)生了這樣的矛盾,即:如果說這“勞動”包含了“前人”——“形成中的人”——猿的活動,那么勞動范疇的外延便被擴大到人類歷史之外,這種外延擴大化了的“勞動”范疇使人的勞動和動物的活動失去了界限;如果說這“勞動”是定指人的活動那么它似乎又不及“生產”范疇涵蓋得那樣寬泛。比如:生產范疇涵蓋了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以及人類自身的生產——人口的生產;而勞動范疇僅涵蓋了體力勞動、腦力勞動,或抽象勞動、具體勞動,但人類自身的繁衍行為很難說是一種什么勞動。退一步說,即使勞動范疇涵蓋了生產范疇的全部內容,那又有什么必要非用勞動范疇取代生產范疇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2]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范疇與生產范疇并無本質區(qū)別。如果說生產范疇不能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那么同樣,勞動范疇也不能作為這樣的起點。我們知道,《資本論》所以把商品范疇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因為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豐富性都包含生產者之間發(fā)生聯(lián)系的實在的商品形式。由此可以認為孕含社會一切矛盾胚芽的范疇“生產”,也不是“勞動”,而只有工具范疇這一實在形式才孕含了歷史發(fā)生發(fā)展的內在必然性,因為只有工具范疇才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矛盾的交匯點。
第一,工具范疇包含了人與自然矛盾的胚芽。在自然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自從有了工具,人類便從動物中提升出來,使“人”成為人,使“人群”成為社會。至此,物質世界便發(fā)生了亙古未有的裂變——一方面是人類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主體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在這裂變了的世界和裂變了的世界矛盾體系中,是工具首先把人同自然界區(qū)別開來,對立起來;同時也是工具把人與自然界聯(lián)系起來,統(tǒng)一起來,形成了人——工具——自然界這樣一個兩對矛盾三個環(huán)節(jié)的動態(tài)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作為人與自然界的中介工具有著內在的二重屬性,一方面它是自然力量的人化,客體力量的主體化;另一方面,它具有了標定人與自然矛盾性質的功能,這是其他任何范疇所不能代替的。換句話說,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的分裂,另一方面則是能動的主體對于這種分裂的征服。而這種征服,主體又必須憑借一定手段,因為人總是通過外物手段和他自身相聯(lián)系,這種手段集中地表現(xiàn)為工具。工具確定了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界限,工具又不斷地打破這種界限,確立新的界限,這種界限是歷史標定的,歷史打破的,又是客觀存在的,消除了這種界限,人類便被湮沒在自然中。正因為工具具有這些功能,所以馬克思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qū)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是人類勞動力發(fā)展的測量器”。[3]在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矛盾運作中,工具不但孕含著物質生產矛盾展開的胚芽,作為精神生產的特殊工具,也孕含著精神生產矛盾展開的胚芽。正因如此,理論家們就把勞動范疇作為“打開社會奧秘的鑰匙”,“鑰匙”也是一種工具。上述說明,在工具背后,隱藏著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矛盾。
第二,工具范疇還孕含著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胚芽。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經濟的關系,社會關系中的其他方面——政治關系、思想關系,從根本上說都決定于經濟關系。而在經濟關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人們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以及對它的占有關系。在生產資料中,要使之轉化為現(xiàn)實的衣食資料,原始人類只能依賴于勞動工具這一中介手段;另外,原始人類處在兇禽猛獸的包圍中,人們只有依靠武器(特殊工具)才能戰(zhàn)勝他們,以維持自己的生存。這時,人們的價值觀念僅僅是“工具——生存”觀念。私有制產生之后,“工具——生存”觀念被“工具——財產”觀念所取代。人們意識到“要強迫人們去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勞役,那就必須設想這一強迫者掌握了勞動資料,他只有借助這些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4]創(chuàng)造財富,這種“工具——財產”觀念,在奴隸占有制時代,被強化到了這樣的程度:奴隸主為了占有財富,不僅占有了無聲工具(無生命的工具),也占有了發(fā)聲的工人(牲畜),而且,就連奴隸也是當作工具——會說話的工具被占有的,占有奴隸的多寡,成為奴隸主富有程度的標志。到了封建制時代,農民(農奴)形式上占有一定的勞動資料,但實際上,封建主對于勞動資料的占有是通過對農奴或農民的半占有這種曲折的方式實現(xiàn)的,農民不過是自動的“牛馬”。當然,隨著社會形態(tài)的完善,人們的財產觀念也逐漸由勞動資料擴大為生產資料。這時,封建主一方面通過農民半占有這種曲折方式占有勞動資料;另一方面,則通過占有勞動對象(主要是土地)來占有勞動者及其勞動資料。到了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的時代,勞動者成為一無所有的“自由人”,但是勞動者一旦進入生產過程,資本對他們的奴役便表現(xiàn)為機器和工具上。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所以能夠成為社會的主人,也是因為實現(xiàn)了勞動群眾對于勞動資料的直接占有和結合。通觀歷史不難看到,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包括階級關系的變化,是以人與勞動工具關系的變化為轉移的,所以,我們要考察歷史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像《資本論》通過商品透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那樣,首先應當考察以不同性質的生產工具為標志的不同的經濟時期中,人們同生產工具的結合方式和占有方式,通過考察勞動工具的性質、功能、系統(tǒng)結構對于人們相互關系的決定與制約作用,透視人們之間的關系,嚴格說來,生產、分配、消費、流通,乃至分工、協(xié)作,都是以生產工具為軸心而逐漸展開的。總的說來,人類文明的根本標志,不是勞動,而是工具。工具才是人類文明的尺度。所以我們說,在工具的背后,隱藏著人與人關系全部矛盾的胚芽。上述特征表明,工具是歷史整體關系中最基本的范疇,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最初的前提與基礎。由此證明,只有工具范疇,它才能夠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5.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4.
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范文第4篇
關鍵詞: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生產力;生產方式
中圖分類號:A8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12-0041-02
市民社會作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概念由來已久,它并不是由馬克思創(chuàng)立,有著深刻的歷史烙印,其概念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其概念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兩類:一類是以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為代表,由于他們所處時代的限制,他們認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應該是高度統(tǒng)一的;另一類是以黑格爾為代表,在黑格爾的時代,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有了極大的提高,資本主義已經形成并發(fā)展,經濟關系逐漸脫離了國家政治而獨立,所以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一對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矛盾,主張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開來。黑格爾的這一理念,對于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的理解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馬克思市民社會思想的起源
馬克思市民社會思想始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在《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馬克思并沒有明確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或者說他并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只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批判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以客觀唯心主義的立場論述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系。他認為,雖然政治國家是從家庭和市民社會中發(fā)展起來的,但它仍是后者的原則和基礎。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也大體上持有同樣的觀點。然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徹底改變了他的觀點,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批評了黑格爾的警察和司法制度,否定了二者是過度到國家的必經之路,也不是調整市民社會特殊利益和政治國家政治聯(lián)系矛盾的工具,而認為警察和司法制度的實質是為保護和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的,并不是為市民社會服務的,這一論斷深刻地揭示了隱藏在背后的階級根源。他同時也批判了黑格爾認為家庭與市民社會沒有聯(lián)系的觀點,認為私人利益體系的一個部分就是家庭,它應該包含于市民社會理論之中,并且不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相反,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馬克思認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和前提,政治國家如果沒有市民社會的人作為基礎以及沒有家庭作為人的基礎就根本不會存在。他通過揚棄黑格爾的思想,把市民社會理解為在市場經濟中發(fā)展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交往和由這種交往關系所構成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的總和。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包括“兩個層次三個領域”的內容和要素。即:個人或私人層次、團體或組織層次,經濟生活領域、社會生活領域和文化生活領域。
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概念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是:“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fā)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也就是說市民社會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為基礎,建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礎之上。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市民社會的概念就要從生產力發(fā)展情況出發(fā)來研究。馬克思同時也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因此,對市民社會概念的理解要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出發(fā),結合人類社會的實踐,以人類社會的歷史發(fā)展為脈絡。
(一)市民社會的形成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fā),確定了一切人類生存的三個前提,即人類歷史的三個前提:首先,人類為了能夠生存,就要維持自己的生命,解決自己的吃飯和穿衣問題,因此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其次,在第一個前提的基礎上,人類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去,以求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生活,所以,人們就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了新的工具,用這些新的工具不斷地對自然界按照人類自身的需求去改造,從而創(chuàng)造人類自身的歷史。第三個前提就是人類自身的發(fā)展和延續(xù),也就是繁殖。人類通過繁殖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夫妻關系、父子關系等,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緊密,從而形成了家族。馬克思認為:“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產,或是通過生育而達到的他人生命的生產,就立即表現(xiàn)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自然關系就是人類通過自身繁殖而形成的血緣關系;社會關系則是由于人們在改造自然的歷史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關系以生產力為基礎,建立在生產力的基礎之上。在人類社會早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比較單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相對簡單;但在生產力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變得復雜多樣,這就導致社會關系也變得相對復雜多樣。
有了人類歷史的三個前提,也就找到了人類發(fā)展的根源。人類因生產力的發(fā)展并通過自身的繁殖而結成家庭,又由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fā)展和人類實踐活動的需要而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結成社會。因此,家庭與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它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家庭通過與家庭之間的聯(lián)系組成了社會,并且影響著人類社會,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也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在人類社會中產生了分工。人類社會早期的分工首先是從家庭分工開始的,進而發(fā)展到社會分工,家庭的分工是由于生產力的發(fā)展使生產方式發(fā)生了變化而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則是生產力的進一步發(fā)展,使人們各自從事的生產方式日趨專業(yè)化。生產方式的專業(yè)化就是人們“各盡其能”,發(fā)揮自己在生產方式上的優(yōu)勢,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推動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馬克思認為伴隨著分工而來的還有分配,因為在同一時期不同的人們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高的那些人,就可以在相同的生產時間內分配較多的勞動產品,而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那些人,在相同的生產時間內就只能分配較少的勞動產品。這樣,由于勞動生產率的原因,造成了勞動者生產的勞動產品在數(shù)量上的差異,從而導致了勞動者所擁有的勞動產品上的不平等。這樣,分配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分配的不平等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發(fā)展,導致了勞動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因而形成了所有制,早期的所有制就是奴隸制。隨著分工的發(fā)展,個人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其他人或家庭的利益就會產生矛盾。矛盾包含著對立和統(tǒng)一兩個方面:矛盾統(tǒng)一的方面就是個人或家庭之間通過一定的協(xié)商達成一致,以契約的形式形成了國家,國家成為維護這些個人或家庭的利益的工具,并通過強制力來維持這種契約;而矛盾斗爭的方面就成為了一切斗爭的根源,個人或家庭之間通過戰(zhàn)爭來獲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國家作為維護一個共同利益的形式,建立在家庭和社會的基礎之上,是以家庭和社會為基礎和前提的,沒有家庭和社會也就沒有國家,市民社會決定著國家政治。
(二)市民社會概念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就是“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會與生產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生產力的發(fā)展情況決定了市民社會的發(fā)展,反過來,市民社會的發(fā)展情況又影響著生產力的發(fā)展。馬克思還認為:“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yè)生活和工業(yè)生活。”因此,市民社,會概念應該是很廣泛的,既包括某一階段的商業(yè)生活,又包括某一階段的工業(yè)生活。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的全部概念都包含在了人類的歷史發(fā)展之中,所以,市民社會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綜上所述,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關于市民社會的概念是:市民社會由生產力決定,與生產力相互作用,并且包含了生產力的發(fā)展歷史和與之相對應的各個階段的物質交往的總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認為,與市民社會相對應的范疇是國家政治。市民社會和國家政治的關系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歸根結底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關系。市民社會的發(fā)展是由生產力的發(fā)展的水平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也就有什么樣的市民社會。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由于生產力的水平有限,市民社會的程度并不是很高,而在生產力水平相對發(fā)達的時期,市民社會的程度也就相應的變得很高。由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制約的市民社會也作為推動人類歷史發(fā)展的一個動力,決定了與之相對應的上層建筑,亦即國家政治的發(fā)展。有什么樣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什么樣的國家政治。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國家政治只能由市民社會所決定。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市民社會同時也有資產階級社會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由掌握絕大部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組成的,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占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多數(shù),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社會的發(fā)展方向以及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方向掌握在這些占大多數(shù)的勞動者手里,因此,市民社會也有資產階級的社會的意思。
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范文第5篇
一、以生態(tài)學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前提
福斯特是依據(jù)方法論思考資本主義生態(tài)危機的。他認為,隨著唯物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的不斷進步,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開始譴責對自然的侵犯行為”,但由于學界對馬克思生態(tài)理論研究的膚淺和零碎,因而并沒有系統(tǒng)而深刻地把握馬克思生態(tài)理論的實質。福斯特認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觀點,并在此基礎上,探究生態(tài)思想的本質。在開始這樣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者如盧卡奇等人思想的影響,福斯特長期以來,都將黑格爾主義化了,這妨礙了他從根本上把握內含的生態(tài)哲學觀點。“我多年所學習的,成了我探索生態(tài)唯物主義的障礙。我的哲學基礎一直是黑格爾和黑格爾主義的者對實證主義的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最早見之于在20世紀20年代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蘭克福學派和新‘左派”。這種將黑格爾主義化的后果,就是從根本上認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否認了辯證的思維方式運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認為,從根本上看,馬克思的世界觀來源于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是一種系統(tǒng)的、富含深刻生態(tài)思想的世界觀。西方者如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把黑格爾主義化,從根本上脫離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與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因而無法領會內含的豐富的生態(tài)思想,找不到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途徑,丟失了馬克思的生態(tài)思想的核心內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現(xiàn)實性與實質性意義。面對那些曲解生態(tài)思想的學者,以及那些指責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主義者,即強調人對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觀點的人,福斯特明確指出:“若期待用舊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來在科學中取得神秘巨大的進步,這是無聊的空想。我們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僅有極微小可鄙的進步,我們就必須從基礎上重新開始。”副福斯特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構造馬克思的生態(tài)理論”。無疑,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態(tài)正義理論之前的一個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認為,由于抽象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唯心主義看不到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一種“實踐的唯物主義”,這種“強大的歷史唯物主義”一直對自然保持高度關注,一直將自然一物理的內容視為物質存在的重要構成,并強調人與自然之間共同進化的物質變換關系。他直接援引馬克思的話,證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相互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馬克思實際上對如何調整我們與自然界的關系,對環(huán)境進程如何與社會發(fā)展和社會關系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見解。”顯然,在福斯特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其實也就是生態(tài)學歷史唯物主義,因為它堅持從歷史變革、制度變化與社會發(fā)展的宏觀視角看待和認識生態(tài)問題。我們看到,這是福斯特生態(tài)正義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前提。傳統(tǒng)的經濟學迷信市場的作用,把自然資源作為商品納入市場體系,但是,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短視行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態(tài)原則的方式組織生產,而是把自然視為迎合市場需要的公共產品,忽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帶來人與自然的對立與沖突,并造成人們價值觀的混亂,拜金主義的盛行。在福斯特看來,傳統(tǒng)經濟學狹隘的視野顯然是無視歷史唯物主義的后果。福斯特認為,的生態(tài)理論根本不需要“綠色化”。既批判了人與自然的異化,同時又對如何超越這種異化提供了科學的思考路徑,因此,它本身就是豐富的、科學的和完整的理論。那些生態(tài)社會主義學家“不能充分認識馬克思貢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這樣一種與日俱增的傾向:它把對生態(tài)價值以及生態(tài)形式的理解建立在與科學和唯物主義根本對立的基礎之上”。在福斯特看來,生態(tài)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價值問題。如果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系這一客觀事實被忽視了,那么馬克思思想中的生態(tài)價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來。
正是馬克思在社會歷史領域內與唯心主義的斗爭,才使他獲得了關于“物質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觀內容。從這個角度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又是一種“理性的唯物主義”,不僅能夠從根本上有效地解決當前的生態(tài)問題,而且又能夠將經濟的發(fā)展與生態(tài)危機的控制有效地結合起來。福斯特認為,在馬克思那里,唯物主義不僅是“實踐的”和“歷史的”,而且也具有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特性。生態(tài)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在于“拒絕了實在論和唯物主義,而把人類社會看作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人類社會關系的總和”。而這從根本上帶來這樣一個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理解成為一種抽象的、脫離現(xiàn)實的概念。殊不知,在馬克思那里,唯物主義從來都是與自然科學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會犯形而上學的錯誤,就看不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中內含的關于生態(tài)保護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認識。一旦被這些錯誤的觀點主導,其中的生態(tài)思想的光輝也就沒有了。
福斯特認為,綠色理論中激進的生態(tài)主義者將生態(tài)問題的根源歸結于科學革命的觀點是錯誤的。“今天人們常常作這樣的設想,要想成為‘生態(tài)主義者’,就意味著應以一種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自然,應當放棄據(jù)說是被科學和啟蒙運動業(yè)已證明了的那種對待自然的工具性的、還原性的敵對態(tài)度。從而作為一名環(huán)境主義者就意味著與‘人類中心主義’決裂,培育對自然內在價值的精神意識,甚至如有可能應當將自然置于人類之上”。因此,生態(tài)社會主義者才會將當前人類面臨的各種生態(tài)危機歸結于技術本身,并指責現(xiàn)代性的危機就是科學技術的危機。雖然發(fā)源于啟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種唯物主義哲學,與生態(tài)社會主義是截然不同的。
當然,我們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他自我設想與構造的生態(tài)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堅持物質存在的自然內容,堅持從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歷史變革、制度變化等范疇出發(fā)思考問題,并且把生態(tài)理論融入這些范疇,以認識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tài)問題。這樣一種符合生態(tài)學需要的歷史唯物主義,使得福斯特能夠站在一種很高的視野和平臺上看待生態(tài)問題,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談論自然,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這種理論努力不能從根本上把握生態(tài)問題的實質,認識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生態(tài)問題產生的最終動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態(tài)危機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系,在客觀上極易將生態(tài)矛盾擴大化,進而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問題就是生態(tài)危機。這種方法論沒有從根本上把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基本矛盾與規(guī)律的精髓。在馬克思那里,歷史與實踐不是兩個等同的概念,實踐也不直接等同于籠統(tǒng)的社會行動。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從未抽象地談論實踐或者行動,實踐或者行動總是在和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概念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被談論的。馬克思堅決反對將勞動過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系。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顯然,馬克思是從社會內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而福斯特則直接將馬克思的實踐指認為一般形式上的、脫離了現(xiàn)實與具體內容的“社會實踐”或社會行動,他眼中的勞動和實踐都是沒有歷史辯證法內涵的。
二、以社會正義與環(huán)境正義的聯(lián)盟為基本路徑
福斯特批判生態(tài)社會主義和西方的錯誤思維,堅持正義理論,認為生態(tài)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正義問題,環(huán)境問題從來都是與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對于社會的發(fā)展和人類的生存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不正義,而人與自然的和諧則是符合人類需求的正義。人與自然之間、各種生物之間的關系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新的政治哲學,而這種政治哲學終究無法避開正義問題的糾纏。這是福斯特生態(tài)正義理論的一個基本指認。
福斯特不但批判傳統(tǒng)的經濟學,而且批判以技術的改進來建構生態(tài)正義的路徑,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技術是服從于資本邏輯的,“將可持續(xù)發(fā)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xiàn)有生產框架內開發(fā)出更高效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能解決問題的不是技術,而是社會經濟制度本身”。因此,新技術的采用意味著對自然資源更大規(guī)模的掠奪與破壞。
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導致生態(tài)危機的罪魁禍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利潤為首要目標的,資本在不斷積累中,實現(xiàn)不斷地擴張,而這種生產方式嚴重依賴能源和技術,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是不可避免的。在資本不斷增值的過程中,“短期行為”往往導致長期和總體性的環(huán)境規(guī)劃的缺乏,導致不可持續(xù)地利用自然資源,破壞環(huán)境。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對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態(tài)所能承受的極限,并最終導致生態(tài)危機的出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變革現(xiàn)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實施新的生態(tài)戰(zhàn)略,才能實現(xiàn)生態(tài)與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因此,在福斯特看來,有效的生態(tài)變革策略是“紅綠聯(lián)盟”,即走紅與綠相結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與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構符合人類生存需要的生態(tài)正義。福斯特承襲了馬爾庫塞提出的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基本路徑,即將保護環(huán)境與社會主義革命結合起來。福斯特認為,生態(tài)問題的出現(xiàn)是同社會現(xiàn)實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態(tài)正義的建構必須訴諸生態(tài)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聯(lián)盟。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革命必須是將環(huán)境運動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正義的生態(tài)學”。顯然,福斯特的理論策略承襲了的觀點,即通過人類的社會變革實現(xiàn)生態(tài)正義。
福斯特認為,要消除生態(tài)危機,保護自然環(huán)境,建構符合人與自然關系原則的正義理論,首要的問題是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擺正人與自然的地位。傳統(tǒng)的生物平等主義的主張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與自然在現(xiàn)實中不平等是一個客觀現(xiàn)實。福斯特指出:“馬克思完全確認,任何一種未來社會的穩(wěn)定必將有賴于構建一種與自然界的全新的、更為均衡的合理的關系。”也就是說,不能盲目地把人與自然的平等視為生態(tài)正義的前提,不能單純地就自然而論自然,應當在生態(tài)學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下,將社會正義問題納入考慮的范圍,選擇社會正義與環(huán)境正義的聯(lián)盟。解決生態(tài)危機的正確的思路是,把生態(tài)的正義與社會的正義問題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并從社會正義的視角出發(fā)研究生態(tài)正義。那些呼吁所有物種平等、一味倡導自然具有內在價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靠的。顯然,與以往的“深生態(tài)學”的正義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將生態(tài)正義置于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的視野中予以觀察的,而不是將生態(tài)正義理論極端化。基于這一基本視野,福斯特指出,在馬克思那里,正義的實現(xiàn)是以一定的社會制度背景為支撐的,而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正義的,它不可能解決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等一系列不公正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呼喚社會公正與人道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資本邏輯的本性是剝削,這種剝削不可避免地要帶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解決諸多不正義問題,也不會帶來生態(tài)正義的美好愿景。馬克思眼中的新社會是一個包含著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和諧相處的社會,是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也是能夠增進人與自然合理關系的社會。
建構生態(tài)正義首先需要一場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對待自然環(huán)境的不道德行為。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導致社會權力結構的不道德,長期以來將自然當作商品買賣,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因此,建立一種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符合生態(tài)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生態(tài)道德十分必要。個體的道德修養(yǎng)當然重要,但還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證個體道德修養(yǎng)的落實。福斯特認為:“事物的正確與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wěn)定和美。”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對待自然問題的不道德行為,堅持文化與生態(tài)的多樣性存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僅有道德革命是不夠的。生態(tài)問題的解決,生態(tài)正義的建構,需要通過變革社會制度來實現(xiàn)。資本主義生態(tài)危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在資本主義社會,獲得利潤、不斷實現(xiàn)資本積累是生產的最高目標,對技術的推崇與非理性的生產方式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內在價值被忽視、環(huán)境的破壞與生態(tài)危機的出現(xiàn)。因此,生態(tài)正義的建構最為關鍵的事情就是實行自然生態(tài)觀的革命,并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看到了,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qū)的環(huán)境主義者僅僅從環(huán)保角度出發(fā)而進行的保護原始森林斗爭失敗的事實。這一環(huán)保運動因忽視了工人的生計問題,制造了林業(yè)工人與環(huán)境主義者之問的矛盾與對立,無果而終。這次環(huán)保運動的教訓使得福斯特確信,要想建構生態(tài)正義,必須使環(huán)境運動與社會運動結盟,通過斗爭的方式獲取環(huán)境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實現(xiàn)。但是,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個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開展這樣的“斗爭”,選擇什么樣的斗爭方式,福斯特卻沒有具體展開來說明。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福斯特有推動環(huán)境正義與社會正義結盟的想法,但他并沒有為這種新社會運動提供科學合理的證明。如果僅僅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對環(huán)境的不正義的角度認識資本主義制度,而放棄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正義、經濟正義的批判與思考,那么就不能從根本上把握資本主義生態(tài)問題的本質。
三、生態(tài)正義建構的主體尋求
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當下社會的核心體制,“這種體制的顯著特征猶如一種巨型的松鼠籠子。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其中的腳踏輪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從中脫離……他們僅僅需要有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而已……成為環(huán)境之主要敵人者不是個人滿足他們自身內在欲望的行為,而是我們每個人都依附其上的這種像踏輪磨坊一樣的生產方式”。環(huán)境正義與社會正義的實現(xiàn)依賴一定的階級力量,環(huán)境正義與社會正義的結盟是由這一革命主體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對那些主張超越階級斗爭的環(huán)保主義者進行了批評,認為這是不現(xiàn)實的。福斯特認為,環(huán)境問題的出現(xiàn)與人們的消費習慣、生活方式有關,更與不同階級、不同派別的意識形態(tài)有關,因此,階級斗爭的角度仍然是當前尋求生態(tài)正義的革命主體的正確思路。他指出,當代社會歷史依然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歷史由階級斗爭構成”的觀點依然沒有過時,無產階級在生態(tài)正義建構上的主體地位依然非常重要。無產階級在激進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變革中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要實現(xiàn)未來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強大力量不容忽視。在這個問題上,福斯特與奧康納有一致的看法。
奧康納也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tài)問題之所以是一個階級問題,是因為階級斗爭是環(huán)境、生態(tài)等運動中一個明顯的因素,而理論的核心思想與精華之處就是對于階級斗爭的堅持。在福斯特看來,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倡導的那種與無政府主義混雜在一起、帶有明顯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的綠色運動,不過是一種沒有現(xiàn)實根基的烏托邦。他指出:“忽視階級和其他社會不公而獨立開展的生態(tài)運動,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轉移環(huán)境問題,而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制度以其無限度地將人類生產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環(huán)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態(tài)予以商品化的傾向,進一步加強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權力關系。所以,這樣的全球運動對構建人類與自然可持續(xù)關系的總體綠色目標毫無意義,甚至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現(xiàn)存社會力量的分裂,給環(huán)境事業(yè)造成更多的反對力量。”即是說,不深入探究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主要權力關系,生態(tài)正義就無從談起。只有進行強有力的社會變革與斗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tài)危機。“行動”和“物質實踐”的概念,在福斯特這里就是指通過社會變革,建構理想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
福斯特認為,具體的社會變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會下層民眾參與的社會運動。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革命的階級主體,是因為他們不僅飽受生態(tài)危機的困擾,而且深受各種社會不公正問題的折磨。因此,環(huán)境斗爭的背后有更加復雜的問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當前并沒有過時,因此,在環(huán)境正義運動與生態(tài)正義理論的建構中,革命運動的擔當者也即無產階級的主體作用的發(fā)揮具有重要的意義。顯而易見,福斯特比那些主張僅僅依靠提高人的意識建構環(huán)境正義的環(huán)保主義者更進步。然而,遺憾的是,福斯特雖然指出了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革命主體的重要性,卻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一新的革命主體應當采取何種革命策略,應當如何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