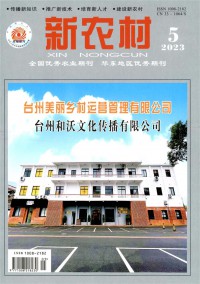新農村建設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新農村建設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整個西方社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干了一件事:完成了從一個生活必需品時代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這個轉型在社會層面上非常不容易,必須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的條件來支撐它。中國目前正面臨同樣的挑戰
城市社會又分成三部分人。
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承擔城市的生活費用,大體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農民工,拿著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但是不承擔城市生活主要費用,大體也算均衡;最慘的是從低端勞動力市場拿工資,同時生活費用又是城市的,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幾乎完全不對等,成為這個城市最不平衡的邊緣人
我們改革思路當中有一個誤區:老說制度不完善,必須要改革我們現有的制度。的確,制度不完善,人們會鉆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無懈可擊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國農村的問題如果脫離城鄉關系,就農村談農村,是談不下去的。以農民看不起病為例,在20—30年前,農村的醫療問題也沒有現在這么嚴重。盡管那時農民也沒有很高的醫療服務,但不至于像今天這樣,稍大一點的病就弄得傾家蕩產。經過3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后,為什么農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醫”和“藥”大多來自城市,其價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來制訂的。所以,農村問題需要從城鄉關系的新視角來重新看待。
“耐用消費品時代”到來導致的“斷裂”
關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去年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個計算結果,是將福利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結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單位的研究則得出另外一個結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3255元,但這當中包含了實物折合,比如過去一年養的豬長胖多少,樹長粗了多少……把這些實物增漲都折成錢,這才達到3255元,這部分非貨幣收入大約占農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實物這部分,只算貨幣收入,城鄉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等等都算進去,城鄉差距可能達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鄉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這是非常嚴峻的情況。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鄉兩部分人處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和世界。更嚴峻的問題是,兩部分人卻要面對同樣一個市場,同樣一種價格。醫療問題就是這樣的,城鄉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罷,醫療市場只有一個,藥品價格只有一個,而這個價格基本上是貼近城市收入水平確定的。教育價格也是如此,所以僅僅就農村看農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個大的背景下。
讀過《光榮與夢想》的人會發現,1929年之前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非常相近:經濟繁榮,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生產能力過剩,購買力不足,汽車、鋼鐵、房地產崛起,成為支柱產業,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世界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
1930年代美國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場大蕭條的產生原因到現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1929年發生的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周期過剩的危機”。這話只說對了一半,生產過剩是確實的,但說周期性卻并不準確,因為從1929年到現在70多年沒有再發生過這樣的危機。那么當時的獨一無二之處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當時西方社會開始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的時代。
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社會就開始進入這種轉折,但就是轉不過去,最后的結果是轉成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然后又經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后來“二戰”爆發,西方才最終完成了這個轉變。所以朦朧一點講,整個西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干了一件事:使得這個社會完成了從一個生活必需品時代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
猛一聽可能覺得奇怪:過去是柴米油鹽的生活必需品時代,現在是汽車、樓房的耐用消費品時代,這不挺好嘛,怎么出現大危機了?這個轉變從個人的角度看,絲毫困難沒有,從社會的層面來說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與耐用消費品相適應的一套消費模式,就必須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的條件來支撐它。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挑戰。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至少有三條非常重要。第一條就是社會保障。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就是認為社會保障是一件花錢的事,總以為政府手里錢多得花不出去,才會有社會保障,這是完全錯誤的。經濟大蕭條是1929年到1932年,美國福利國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來的,當時美國還沒有完全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為什么?很簡單,沒有社會保障,消費者就不敢買東西。
第二條就是貧富差距不能太大。現在人們在講一個社會要以中產階層為主,這其實是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重要條件。當時美國也面臨這樣的情況,大部分人從農村剛剛進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國比我們多了一個工人運動,多了一個工人可以對資本家進行博弈的工具,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工人工資迅速提高。現在我們講中產階層的社會,一定不能理解為這是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這個中產階層的壯大,是和一連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階級的權利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斗爭的結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資增加,但同時也意味著購買力提高,資本家的東西可以賣得出去了。
第三條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須達到一半以上。現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40%左右,但這其中包括所謂在城市中連續居住達到三個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樣“農轉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遠沒有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達不到總人口的一半,這個社會就進入不了耐用消費品的時代。這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還有生活方式的問題。
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是非常必要的。過去在三農問題討論中,我覺得有一個思維誤區,就是總想找出一個根本性的解決辦法,而實際上我覺得三農是一個沒解的問題。這次新農村建設表現出了一種新的思路,即針對一個沒解的問題,采取分解的方式來逐步緩解,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關政策都歸到一起,按照類型來分,我覺得至少能分成三條不同的路徑,然后多管齊下。
第一條路徑就是用農村發展來解決一部分問題。農村的產業化不能絕對解決農村的問題,但至少我們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差距。每有1元錢初級農產品,在美國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錢初級的農產品經過美國人加工以后可以賣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錢初級農產品經過日本人加工后能賣到3.2元。而中國的附加值僅僅是3毛8分,即1元錢初級農產品,最后我們只能賣1.38元,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如果我們通過拉長產業鏈條,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觀了。對農村本身來說,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個潛力。我認為這是比較務實的思路。
第二條路徑就是城市化。中國每年大約1000萬左右人口轉移到城市,這使得農村在其他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又減少了1000萬,1000萬的人口在城市當中會尋找一些新的機會。剛才說的產業化思路,實際上需要國家補貼,農村人口如果像現在這樣仍然多達七八億人,那其實無論產業化也好,國家補貼也好,都會受到嚴重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都是分解路數的一部分。
第三條路徑就是國家的投入。雖然大家都會說,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改造,制度建設比錢更重要,但建設新農村,國家還得向農村投入。我想,通過農村自身有限發展,一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國家再有一些投入,原來農民自己辦的教育國家大部分承擔起來,原來農民自己修的路國家承擔一部分,原來完全沒有的社會保障,國家能夠幫助搞起來,農村生存狀況惡化的速度會大大減緩,甚至說不定會有改善。
整個西方社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干了一件事:完成了從一個生活必需品時代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這個轉型在社會層面上非常不容易,必須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的條件來支撐它。中國目前正面臨同樣的挑戰
城市社會又分成三部分人。
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承擔城市的生活費用,大體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農民工,拿著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但是不承擔城市生活主要費用,大體也算均衡;最慘的是從低端勞動力市場拿工資,同時生活費用又是城市的,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幾乎完全不對等,成為這個城市最不平衡的邊緣人
我們改革思路當中有一個誤區:老說制度不完善,必須要改革我們現有的制度。的確,制度不完善,人們會鉆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無懈可擊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國農村的問題如果脫離城鄉關系,就農村談農村,是談不下去的。以農民看不起病為例,在20—30年前,農村的醫療問題也沒有現在這么嚴重。盡管那時農民也沒有很高的醫療服務,但不至于像今天這樣,稍大一點的病就弄得傾家蕩產。經過3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后,為什么農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醫”和“藥”大多來自城市,其價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來制訂的。所以,農村問題需要從城鄉關系的新視角來重新看待。
“耐用消費品時代”到來導致的“斷裂”
關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去年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個計算結果,是將福利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結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單位的研究則得出另外一個結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3255元,但這當中包含了實物折合,比如過去一年養的豬長胖多少,樹長粗了多少……把這些實物增漲都折成錢,這才達到3255元,這部分非貨幣收入大約占農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實物這部分,只算貨幣收入,城鄉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等等都算進去,城鄉差距可能達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鄉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這是非常嚴峻的情況。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鄉兩部分人處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和世界。更嚴峻的問題是,兩部分人卻要面對同樣一個市場,同樣一種價格。醫療問題就是這樣的,城鄉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罷,醫療市場只有一個,藥品價格只有一個,而這個價格基本上是貼近城市收入水平確定的。教育價格也是如此,所以僅僅就農村看農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個大的背景下。
讀過《光榮與夢想》的人會發現,1929年之前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非常相近:經濟繁榮,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生產能力過剩,購買力不足,汽車、鋼鐵、房地產崛起,成為支柱產業,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世界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
1930年代美國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場大蕭條的產生原因到現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1929年發生的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周期過剩的危機”。這話只說對了一半,生產過剩是確實的,但說周期性卻并不準確,因為從1929年到現在70多年沒有再發生過這樣的危機。那么當時的獨一無二之處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當時西方社會開始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的時代。
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社會就開始進入這種轉折,但就是轉不過去,最后的結果是轉成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然后又經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后來“二戰”爆發,西方才最終完成了這個轉變。所以朦朧一點講,整個西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干了一件事:使得這個社會完成了從一個生活必需品時代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
猛一聽可能覺得奇怪:過去是柴米油鹽的生活必需品時代,現在是汽車、樓房的耐用消費品時代,這不挺好嘛,怎么出現大危機了?這個轉變從個人的角度看,絲毫困難沒有,從社會的層面來說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與耐用消費品相適應的一套消費模式,就必須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的條件來支撐它。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挑戰。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至少有三條非常重要。第一條就是社會保障。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就是認為社會保障是一件花錢的事,總以為政府手里錢多得花不出去,才會有社會保障,這是完全錯誤的。經濟大蕭條是1929年到1932年,美國福利國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來的,當時美國還沒有完全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為什么?很簡單,沒有社會保障,消費者就不敢買東西。
第二條就是貧富差距不能太大。現在人們在講一個社會要以中產階層為主,這其實是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重要條件。當時美國也面臨這樣的情況,大部分人從農村剛剛進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國比我們多了一個工人運動,多了一個工人可以對資本家進行博弈的工具,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工人工資迅速提高。現在我們講中產階層的社會,一定不能理解為這是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這個中產階層的壯大,是和一連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階級的權利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斗爭的結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資增加,但同時也意味著購買力提高,資本家的東西可以賣得出去了。
第三條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須達到一半以上。現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40%左右,但這其中包括所謂在城市中連續居住達到三個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樣“農轉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遠沒有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達不到總人口的一半,這個社會就進入不了耐用消費品的時代。這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還有生活方式的問題。
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是非常必要的。過去在三農問題討論中,我覺得有一個思維誤區,就是總想找出一個根本性的解決辦法,而實際上我覺得三農是一個沒解的問題。這次新農村建設表現出了一種新的思路,即針對一個沒解的問題,采取分解的方式來逐步緩解,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關政策都歸到一起,按照類型來分,我覺得至少能分成三條不同的路徑,然后多管齊下。
第一條路徑就是用農村發展來解決一部分問題。農村的產業化不能絕對解決農村的問題,但至少我們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差距。每有1元錢初級農產品,在美國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錢初級的農產品經過美國人加工以后可以賣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錢初級農產品經過日本人加工后能賣到3.2元。而中國的附加值僅僅是3毛8分,即1元錢初級農產品,最后我們只能賣1.38元,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如果我們通過拉長產業鏈條,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觀了。對農村本身來說,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個潛力。我認為這是比較務實的思路。
第二條路徑就是城市化。中國每年大約1000萬左右人口轉移到城市,這使得農村在其他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又減少了1000萬,1000萬的人口在城市當中會尋找一些新的機會。剛才說的產業化思路,實際上需要國家補貼,農村人口如果像現在這樣仍然多達七八億人,那其實無論產業化也好,國家補貼也好,都會受到嚴重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都是分解路數的一部分。
第三條路徑就是國家的投入。雖然大家都會說,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改造,制度建設比錢更重要,但建設新農村,國家還得向農村投入。我想,通過農村自身有限發展,一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國家再有一些投入,原來農民自己辦的教育國家大部分承擔起來,原來農民自己修的路國家承擔一部分,原來完全沒有的社會保障,國家能夠幫助搞起來,農村生存狀況惡化的速度會大大減緩,甚至說不定會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