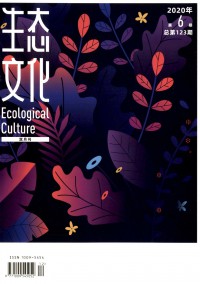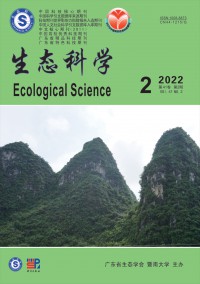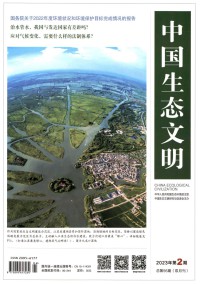生態文明下的資本主義研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生態文明下的資本主義研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探尋“生產性正義”
生態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除了傳統的導致經濟危機的社會基本矛盾以外,更關注生產關系(包括生產力)和生產條件的矛盾,主張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的“生產性正義”,強調生產活動在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公共條件上獲得正當合理性和社會生產關系的公平正義,以期生態和諧。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一輪科技革命———生命科學創造出的巨大生產力,推動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從線性經濟、高能耗經濟向循環經濟、節能經濟的轉變,使得原本存在制度根源的資本主義社會正義獲得了全新的生態學意義———“所謂正義社會這個概念也已將其關注視線從定量方面轉向定性方面了,從社會產品的分配過程轉向這種產品的生產過程了。”據統計,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不受影響的情況下,由于實現了資源投入量的源頭控制,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呈明顯下降趨勢。由表1可知,單位GDP能耗是一國能源利用效率指標,而目前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主體。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國內資源、環境基礎之上對“生產性正義”的探索。
二“、后物質主義”和“紅綠”思潮深刻影響資本主義價值體系
1.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觀發生轉向。“后物質主義”價值原則于20世紀80年代后流行歐美國家,是對占主流地位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檢討和合理替代———從工業社會熱衷于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忽視精神價值和生態價值的唯物質主義,轉向對生態環境、生活質量、人權和公民自由等非物質價值的關注。除此之外,包括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綠色工聯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學(自治市鎮主義)、包容性民主理論等被稱為“紅綠”(綠色左翼)思潮與“深綠”的生態無政府主義、“淺綠”的生態資本主義一并使這種價值分層和變遷更加豐富和復雜,而在“新社會運動”中興起的社群主義和社區自治理念也不斷挑戰傳統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2.理性消費觀對傳統消費觀的超越。長期以來,受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和自由競爭規律的驅使,生產的無限擴張性和有產階級對地位和權力的追崇培育了資本主義國家奢侈型、炫耀性和超前消費的方式和觀念,“人本身越來越成為一個貪婪的被動的消費者。物品不是用來為人服務,相反,人卻成了物品的奴仆。”異化消費作為資本主義制度性的內在矛盾之一,隨著“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普及和深入,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費方式的“綠化”,正在被逐漸解構:一是崇尚“低碳”。后工業時達的社會生產力使得物質滿足的邊際效益遞減,人們普遍接受了“增加消費并不會使人們更幸福”“錢是自己的,但資源是社會的”這樣的價值判斷:歐洲民眾開始踐行后物質主義的生活方式———崇尚“簡單的飲食”和“樸素低碳著裝”,酒店賓館的管理逐漸告別“一次性”時代,出行“零排放”———北歐國家元首自行車上下班已成為風尚。二是抵制奢侈。生活在“質”上的增長是后物質主義的基本特征,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人們的等級觀念日益淡漠,一種建立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基礎上的質樸消費觀、本色生活潮流興起。官、學、民住宅設計的簡樸化和建筑空間資源最優化,政府對奢侈型消費征收高額消費稅等,變革獲得了自上而下的形式。三是倡導“慢活”。對于片面追求效益而過勞破壞人的身體健康,使人與人的疏離感增加,心理健康和幸福指數下降,離婚率自殺率激增等現象,西方民眾有著深刻的反思。意大利、法國、英國等西歐國家開始推行“慢活”活動,放慢生活節奏,享受生活和自然。這種重視休息和精神消費的觀念變化甚至為緩解勞資矛盾提供了有效出口,如法國人“休假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準則更促成了法定勞動時間從1982年的每周39小時縮短至2000年的35小時。
3.對社會制度選擇的重新考量。后物質主義和“紅綠”思潮最具時代特點的衍生物,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內生的制度變革要求。一些理論流派在生態經濟學家、學者對資本主義利用新能源、回收利用極限、環保技術創新和經濟可持續性解決環境破壞和全球性貧困等主流觀點上不抱幻想,承認和確信“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失敗”,“資本主義的生態和經濟之間存在著一種體系內無法調和的根本性矛盾”,持這些觀點的理論流派和黨派正在迫切渴望一種替代性的選擇。2009年BBC在柏林墻倒塌20年之際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全球27個國家2.9萬人的意見中,半數以上被調查者不滿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相反,社會主義思想愈來愈受歡迎。
三、綠色政治促進了發達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從政治學角度看,綠色政治除了上述綠色思潮以外還包括綠色運動和綠黨運作。綠色運動首先是指19世紀后半期逐漸發展起來的環境保護運動,于20世紀60年代末演進為“新社會運動”;而綠黨是在該運動基礎之上,綠色運動團體借助現存政治手段特別是議會制民主以實現自己理論信念與運動目標的政黨化努力。
1“.新社會運動”賦予工人運動新的特點。綠色運動在內涵和形式上的擴展,演變具有實踐和理論形態的“新社會運動”。由此產生的“新中間階層”演變了傳統工人階級,體現為工人的白領化、多領化(從事環境衛生的綠領、高級管理層的金領、維修與營銷人員的灰領和大量女工的粉領)、知識化、智能化、有產化,折射出社會結構的多元變遷。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建立福利制度,資本家利用產業轉移離間了本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加之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和意識的變遷,工人運動一直處于低潮。工人階級本身就是材料和能源大量浪費和工業污染的直接感受者兼受害者,以環境運動為先導的“新社會運動”賦予工人運動復興全新的文化熏陶,使之產生新的時代特點:激進工會運動和生態學的合流,在歐洲和北美被人們描述為“工聯主義的生態學”或“綠色工聯主義”。這種綠色的新型工人組織有別于傳統官僚化工會,尋求自下而上的組織模式,斗爭運動上摒棄傳統工聯運動的經濟主義,拒絕大規模罷工、談判、書面合同和普遍接受的貿易自治,采用新奇策略“直接行動”、“消費者阻斷”、“減少生產”,強調“工人階級除了妥協的歷史還有著激進的運動史,工人群眾并非總是順從的羔羊”,這種“紅綠”運動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階級斗爭的新形式。
2.政黨“綠化”重組政黨格局。在西方社會傳統的政治色譜中,“紅”與“黑”是兩種基本底色。綠黨出現、傳統“左”與“右”二元區分式微,各黨派“同質性”價值日益增多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生態開始逐漸“綠化”和“解意識形態化”,政黨格局變化。一是綠黨的崛起轉換了西方社會政治發展主題。綠黨擺脫了傳統政治議題的束縛,其“倡導的主題———環境保護、女性平等、自助、分權化———在政治議程中已經贏得非常穩固的地位”,挑戰了按階級戰線和傳統意識形態劃線的政黨格局。二是綠黨的出現直接改變了政黨格局。20世紀90年代起,各國綠黨紛紛進入本國政府和議會,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德國綠黨還與社會組成“紅綠聯盟”,成為執政黨,打破了西方(以歐洲為典型)社會左右翼兩大政黨壟斷社會政治生活的格局,被譽為“新中間力量”。另外,綠黨還在歐洲、非洲、美洲、亞洲和大洋洲建立了地區性政黨聯盟或議會黨團,正逐漸成為一支世界性的政治力量。三是綠黨的壯大革新了傳統政黨的生存和運作方式。綠黨因主張生態保護、反暴力、無核化和基層民主的政治訴求一直擁有穩定的選民基礎,為了贏得比較優勢,綠黨成為左翼和右翼選舉中的爭取和聯合對象,其參政和執政改變了政治博弈的游戲規則,促進了政治民主化、政黨決策科學化和執政親民化。
3.政府轉型擴大社會自主空間。二戰后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經歷了從傳統軍事、政治、法律領域拓展至經濟領域的第一次職能轉型,但是在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綠色政治”主流化的態勢驅動下,政府越來越重視其社會公共服務職能(見表2)。社會化程度提高,這必然帶來在某些專業領域公共權力的下放(如環境保護和治理、社區管理服務等),“小政府大社會”的趨勢愈發明晰。在上述政府轉型的語境下,“新社會運動”使政府將大量的社會公共空間釋放出來,讓渡給綠色NGO或法人、社區組織承接運作,呈現公共事務管理民營化。在活動范圍上,由于這些團體和組織的制度化和職業化、非對抗性和建設性,如地球之友和綠色和平等組織的跨國化發展和全球環境(氣候變化)正義運動,其超越國內政治界限而著眼于一種國際或全球性視野,不僅為傳統工人運動的國際聯合思想提供了實踐范本,也成為目前廣泛討論的“建立一種全球公民社會治理模式”的主要推手。
四、解決全球生態問題有利于國際關系民主化
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標志著環境問題被列入國際政治議程,環境問題由于其本身的全球性、不可分類、不可量化、不易解決、高風險和長期性以及與國家核心利益的密切性現已逐漸擺脫傳統外交學“低端政治”的層次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重大因素,甚至有學者提出環境問題導致了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觀點。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舉行正式拉開了“環境外交”時代的大幕。
1.國際關系行為體努力構建國際環境治理的新范式。主權國家之間發展階段和工業化水平的不同導致的“發展和環境的優先次序”是目前阻礙全球環境問題合作的根本原因,由此出現了目前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益主體、利益陣營的不斷分化重組,既有歐盟與美國為首的傘形集團在“綠色壁壘”和資金技術轉讓問題上的矛盾與妥協,又有發展中國家訴求沖突下七十七國集團和小島嶼國家聯盟在氣候問題上的博弈,還有由于跨國環境治理引起的雙邊和多邊、區域性國家合作,這種動態的競爭與合作有利于打破傳統“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更廣泛的國際對話和構建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提供了全新的話語體系和行動平臺。國際組織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新動力,根據UIA2004—2005的調查數據,目前全球政府間國際組織約有7350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有51509個。“環境外交”發端以來的40年間,環境、資源、人口等已經深刻植入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議題之中,使各類國際組織的“綠化”成為一大趨勢,從聯合國到歐盟東盟非盟,從國際紅十字會到國際奧委會,都在為環境治理的全球化、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和治理的民主協商方式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2.國際環境機制發展不斷促進國際關系法制化進程。國際環境機制主要表現為通過國際環境談判而達成的多邊環境條約。國際環境機制的形成和維持理論與實踐,打破了傳統國際制度的“霸權穩定論”,尤其是全球氣候機制在美國退出的情況下得以生效的事實證明,處理某個環境問題的性質、談判達成的科學共識、替代技術和產品成本的高低以及強有力的正面領導是國際環境機制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沒有霸權國的包攬,國際環境機制依然可以運作。現有的國際環境機制的基本模式是公約—議定書,如生物多樣性公約、核安全公約、京都議定書等。這一模式的優點在于簽約各國可以在有具體政策分歧的情況下先行簽署,簽署后的進一步科學研究或執行將受到世界輿論的監督和國內環保力量的關注,從而又對態度消極的國家產生巨大壓力,進而促成原機制的完善。這一過程是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大突破,不單為國際環境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礎,同時也促進了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法制化進程。
五、對新變化的認識
1.新變化的出現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規律。正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言:“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生態文明是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共同規律,當代資本主義在遵循自身特殊規律的同時,也不斷在這一共同規律的影響下被迫開出人類文明的“花朵”,生態文明內涵中的“新因素”所具有的正義、平等、民主、互助、人與自然的和諧,繼而獲得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合理性等內在價值,正是社會主義價值的本質體現,可見,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應有之義,資本主義生態文明的自我調整和揚棄,也是社會主義因素在資本主義機體內的不斷激活,“兩個必然”依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2.新變化是有限的“環境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總體來說,當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生態文明形態下的經濟和社會改良運動,是一種“環境主義”的主張,法國左翼思想家、哲學家安德烈•高茲對這種“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環境主義”提出異議:“‘環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經濟合理性的自由運作施加新的約束和限制,但是這些約束和限制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趨勢,只是擴展了經濟合理性的范圍。”即資本主義國家只是局限于減少現有經濟文化體制對環境的影響,但由于現有的、在體制內的調整,無法解決經濟合理性與生態合理性的矛盾,最后也會由于被資本主義所接納而遲早要結束———保護環境成為追求更高利潤的權宜之計。因此這種自我調節依然使資本主義面臨著包括經濟增長的生態極限,重新抬頭的種族戰爭、民族戰爭和宗教戰爭、核訛詐和國際性資源分配之爭在內的四大危機。另外,從綠色政治的角度來看,其主體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從群眾運動轉向政黨政治,然而綠黨所倡導的“第三條道路”,其關于未來社會的設計和走向未來的道路迄今為止仍是不明晰不現實的,整體實力較弱,對“新階級”的利益整合也無法完成有效的社會變革,故其對在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進步上是極其有限的。
3.新變化還未能觸動資本主義世界原有的秩序慣性。由于全球生態問題的出現,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國際經濟秩序合理化進程正在被最廣泛地推進。生態文明的初步建構、新變化的出現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再一次獲得了先發制人的優勢,卻使謀取霸權和順從資本意志的頑疾復發,在全球環境問題的對話和合作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然在爭奪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依然在利用其主導的全球化體系進行的危機轉嫁和巧妙盤剝,依然將解決資源、氣候、核安全等問題還原為一國或地區經濟和軍事利益訴求。在國際政治處于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這些“生態帝國主義”延續了原有的弱肉強食的慣性,繼續制造國際環境非正義的不平等的國際關系現狀,生態問題的全球意義正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局限性而不斷打折。
作者:楊柳夏單位:華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