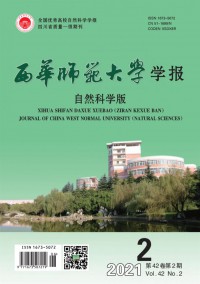陶淵明詩(shī)
前言:想要寫(xiě)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陶淵明詩(shī)范文,相信會(huì)為您的寫(xiě)作帶來(lái)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xiě)作思路和靈感。
陶淵明詩(shī)范文第1篇
一、田園詩(shī)恬淡、樸實(shí)自然的風(fēng)格
談田園詩(shī)離不開(kāi)陶淵明,談陶淵明自然會(huì)想起他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的千古名句。陶的田園詩(shī)對(duì)農(nóng)村事物和恬靜的環(huán)境給予了由衷的贊頌,樸實(shí)自然毫無(wú)喧飾,充分表達(dá)了詩(shī)人的真實(shí)感受。同時(shí)將農(nóng)村那寧?kù)o平和的生活表現(xiàn)得如仙境般優(yōu)美,令人神往。詩(shī)人對(duì)田園生活的贊美未直接說(shuō)出,而是通過(guò)草屋茅舍、榆柳桃李、遠(yuǎn)村炊煙、雞鳴狗吠、山氣飛鳥(niǎo)的白描,流露出對(duì)田園生活的由衷喜愛(ài)和深切依戀,表露出詩(shī)人那純凈的心地和平靜的心境,與簡(jiǎn)樸恬靜的田園風(fēng)光交融為了一體。
二、渾然天成的意境
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至關(guān)重要,而情又是最重要的,離開(kāi)情的景就沒(méi)有了生氣,離開(kāi)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而陶詩(shī)總能透過(guò)人人可見(jiàn)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達(dá)高于世人之情,寫(xiě)出人所未必悟出之理,又呈現(xiàn)新的意境,給人以美感。他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對(duì)人生、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深刻認(rèn)識(shí)形象化,把詩(shī)情與哲理、與景物緊密結(jié)合起來(lái),因而給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覺(jué)。可謂發(fā)乎事,源于景,緣乎情,而以理為統(tǒng)攝。
陶淵明的田園詩(shī)不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作單層次的、平面的再現(xiàn),而是在情、事、景、理的統(tǒng)一中構(gòu)成了多層次的藝術(shù)整體,給人們以豐富而深刻的審美享受。如《飲酒》其五:
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wú)車馬喧。問(wèn)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niǎo)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這首詩(shī)里,“悠悠”的情,南山和飛鳥(niǎo),還有對(duì)“心遠(yuǎn)地自偏”和“真意”的感嘆,概括起來(lái)就是外在的事與景和內(nèi)在的情與理的統(tǒng)一,構(gòu)成深遠(yuǎn)渾厚的意境。
三、質(zhì)樸自然的語(yǔ)言
陶淵明的田園詩(shī)能夠千古流傳,與它語(yǔ)言的質(zhì)樸關(guān)系很大。陶淵明獨(dú)特的生活經(jīng)歷,樸素的農(nóng)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園景色,要求盡可能采用近似“田家語(yǔ)”的樸素的語(yǔ)言和白描手法,從而形成田園詩(shī)平淡自然的風(fēng)格,達(dá)到“一語(yǔ)天然萬(wàn)古新,豪華落盡見(jiàn)真淳”。如千古名句“悠然見(jiàn)南山”中“見(jiàn)”字準(zhǔn)確地傳達(dá)了詩(shī)人采菊時(shí)俯仰自得的情貌,初不用意,猛然見(jiàn)山,是心理上偶然發(fā)現(xiàn)的喜悅,一個(gè)“見(jiàn)”字,使意境有飛動(dòng)之趣。《歸園田居》其三中有“帶月荷鋤歸”之語(yǔ),如果是“戴月”,只是披星戴月的客觀景象,沒(méi)有情感意趣的灌注。“帶月”則將月亮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使畫(huà)面上人的形象和月景融成一片,一人的情趣籠罩整個(gè)境界。以“帶”字寫(xiě)人帶月行,人的一片情意溢出,主觀色彩要濃郁得多。
四、清新、細(xì)膩的筆法
陶詩(shī)與當(dāng)時(shí)詩(shī)壇上流行的形象模糊、晦澀難解、淡乎寡味的玄言詩(shī)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陶詩(shī)刻畫(huà)田園山水,絕不追求華麗的辭藻,而是隨意點(diǎn)染,清新自然,且有無(wú)盡的神韻。如《飲酒》之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這幅在南山襯映下的薄暮美景,在詩(shī)人的全心感受下呈現(xiàn)在眼前。在這首詩(shī)中,“見(jiàn)”字體現(xiàn)了全詩(shī)的神韻,妙在對(duì)南山自然之景的勾勒,是詩(shī)人采菊時(shí)偶然視線的觸及,也是心境悠然之顯。如果改用“望”字,就是刻意追求,意味索然,而且與“悠然”不相適應(yīng)了。這首詩(shī)典型地體現(xiàn)了陶淵明清新自然的筆法。
陶淵明詩(shī)范文第2篇
《歸園田居》詩(shī),直承詩(shī)經(jīng)、楚辭、漢魏樂(lè)府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在內(nèi)容題材上一反玄言詩(shī)的空洞說(shuō)教,在藝術(shù)手法上一反綺麗的形式主義詩(shī)風(fēng),創(chuàng)造了自然清新的新詩(shī)風(fēng)。當(dāng)我們讀到“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的詩(shī)句時(shí),不只覺(jué)得作者的身心復(fù)得返自然,而且覺(jué)得詩(shī)歌這種藝術(shù)形式從思想內(nèi)容到藝術(shù)技巧上也都復(fù)得返自然了。
直抒胸臆的抒情是形成陶詩(shī)自然美的第一個(gè)原因。這在陶詩(shī)中是很突出的,如“少無(wú)適俗韻,性本愛(ài)丘山”,脫口而出,不粉飾,不做作,有什么說(shuō)什么,把坦蕩蕩的胸懷和盤(pán)托出。完全是久別重逢的老友于深夜促膝談心的口氣,不像道學(xué)家的談玄說(shuō)理、莫測(cè)高深,也不像那腐儒講學(xué)的掉書(shū)袋,更不像形式主義詩(shī)歌的賣弄才華。難怪歷代不少評(píng)論家都說(shuō)陶公非寫(xiě)詩(shī),直抒胸臆而已。
素描圖畫(huà)般的寫(xiě)景是形成陶詩(shī)自然美的第二個(gè)原因。陶詩(shī)一反當(dāng)時(shí)詩(shī)人的綺麗雕飾風(fēng)格。“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完全用的是白描手法,把自然景物有所選擇地羅列到讀者面前,這點(diǎn)很像杜詩(shī)“穿花蝶深深見(jiàn),點(diǎn)水蜻蜓款款飛”那樣清新、自然而富有情趣。似大匠運(yùn)斤,不留痕跡,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給人以負(fù)重若輕、事半功倍的感覺(jué)。他寫(xiě)村落的遠(yuǎn)景,沒(méi)有從具體的顏色、形狀、地勢(shì)、大小等方面去著筆,只用“曖曖”這個(gè)重疊詞加以修飾。寫(xiě)墟里煙,也沒(méi)有狀其顏色,只是用重疊詞“依依”去描繪。這還沒(méi)有什么難以理解的地方,因?yàn)榇迓浜托鏌煹念伾揪蜎](méi)有什么出色之處。但是作者對(duì)桃李榆柳描寫(xiě)卻似乎有點(diǎn)難以理解。桃紅柳綠是極鮮明的顏色,桃紅有“人面桃花相映紅”的美稱,柳樹(shù)有“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名句,這是比陶為晚的唐人名句,比陶為早的有《詩(shī)經(jīng)》詩(shī)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都從顏色著墨。陶詩(shī)卻沒(méi)有寫(xiě)顏色,只是寫(xiě)出了桃李榆柳的位置及其和房屋的關(guān)系,這不有點(diǎn)反常嗎?這是反常,也是獨(dú)創(chuàng)。比如一幅素描畫(huà),沒(méi)有五顏六色,濃墨重彩,只有幾筆淡淡的素描線,但是由于畫(huà)工技藝高超,畫(huà)出了素描對(duì)象的神韻和生氣,這就使欣賞者受到感染和啟發(fā),調(diào)動(dòng)自己過(guò)去的感受經(jīng)驗(yàn),從這無(wú)顏色的畫(huà)面中看出顏色來(lái),從而加深了對(duì)畫(huà)面的了解,得到一種美的享受。我們讀上面幾句陶詩(shī),眼前就浮起了比詩(shī)句字面所寫(xiě)要廣泛得多的畫(huà)面,村落那遠(yuǎn)離繁華的荒涼景象,背山傍溝的地勢(shì),房屋墻院的顏色等都透過(guò)“曖曖”這昏暗的字眼,經(jīng)過(guò)聯(lián)想而清晰地顯露出來(lái)。青藍(lán)色的墟煙徐徐上升,郁郁蒼蒼的榆柳,嬌艷嫵媚的桃李也都?xì)v歷在目,甚至那濃郁的桃花的香氣也似乎聞到了。這猶如一幅好的素描畫(huà),能夠引起欣賞者的再創(chuàng)造,達(dá)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dāng)我們回頭再看原詩(shī)句時(shí),更覺(jué)得它是那么的自然樸素。
陶淵明詩(shī)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hào)〕 G633.33〔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4―0463(2008)07(A)―0060―01
陶淵明一生中的大部分時(shí)間是在歸隱中度過(guò)的。歸隱后的陶淵明獨(dú)愛(ài),是他詠唱和贊頌的對(duì)象,更是表現(xiàn)他性格特征和美學(xué)意義的一個(gè)典型形象。詩(shī)人歸隱后對(duì)的詠唱體現(xiàn)了極高的審美情趣和審美愉悅。
一、“菊之境”與“我之境”相互融合
“菊之境”可謂之“無(wú)我之境”。王國(guó)維說(shuō):“無(wú)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wú)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陶淵明《飲酒》詩(shī)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一句就屬于“無(wú)我之境”。其實(shí),嚴(yán)格地說(shuō),詩(shī)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須有“我”,都必須是“我”的性格、情趣和經(jīng)驗(yàn)的寫(xiě)照。只是詩(shī)人情感不在詩(shī)中直接顯出,所以好像無(wú)我一般。也就是說(shuō)詩(shī)人的心境是“悠然”的,眼中的景色也是“悠然”的,詩(shī)人只是把這一景色的直覺(jué)訴諸筆端,表面看似與己無(wú)關(guān), 但情感內(nèi)涵卻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在這種“無(wú)我之境”中也滲透著“有我之境”,即“菊之境”融合著“我之境”。王國(guó)維說(shuō):“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我之境,于由動(dòng)之靜時(shí)得之。”《飲酒》中的“”是在“悠然”中染上情感色彩的。詩(shī)中的“我”,是披露自然風(fēng)貌的主觀存在。作為我觀之物,實(shí)際上也染上了“我”之色彩。 客觀冷靜的描繪滲透著主觀情思,主觀情思寄寓在客觀冷靜的描繪中。這里沒(méi)有斧鑿雕琢之痕,真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欣賞陶淵明的“菊”詩(shī),可以從“菊之境”和“我之境”的相互融合中感受詩(shī)人的生命情調(diào)和意味。
二、是可感的體現(xiàn)社會(huì)生活本質(zhì)的自然形象,是陶淵明精神的一種投影
是有形的實(shí)的,而精神是無(wú)形的。化精神為,就是要以神求形。歸隱的陶淵明寓精神于中,呈現(xiàn)出詩(shī)人淡泊寧?kù)o的心志。“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陶淵明《歸去來(lái)兮辭》),小徑荒蕪了,但松樹(shù)和依然寧?kù)o地存在著。詩(shī)人避開(kāi)了達(dá)官貴人的車馬喧囂,在悠然自得的田園生活中,獲得了自由而恬靜的心情。“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情景真切而富于生活情趣,真是“我的勞動(dòng)是生活的自由表現(xiàn),因而我享受了生活的愉快”。還呈現(xiàn)了陶淵明守志不移、剛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在東晉那個(gè)“終日驅(qū)車走”的追名逐利的時(shí)代,東籬采菊本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種行為,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一種無(wú)言抗?fàn)帯R渤尸F(xiàn)出陶淵明熱愛(ài)勞動(dòng)、歌頌勞動(dòng)的精神。“少無(wú)適俗韻,性本愛(ài)丘山”、“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shù)巔”等詩(shī)句勾勒出了一幅幅農(nóng)村風(fēng)俗畫(huà)面,體現(xiàn)了陶淵明由衷喜愛(ài)勞動(dòng)的情趣,這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是一脈相承的,是對(duì)詩(shī)人精神世界的沿襲。
三、對(duì)的詠唱,本質(zhì)上是一種審美情緒的外化
“菊之于淵明,猶蘭之于屈子,梅之于放翁,都是詩(shī)人高風(fēng)亮節(jié)的象征。” 詩(shī)的情緒在大自然中都能尋找出一種對(duì)應(yīng)物,情緒托于物,物化的情緒便是詩(shī)。陶淵明志隱味深,菊正是他情緒深沉凝聚的載體。
菊的風(fēng)姿,正是詩(shī)人的情緒。《和郭主簿》中說(shuō):“芳菊開(kāi)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盛開(kāi)在霜威下的正是詩(shī)人不屈性格的傳神寫(xiě)照。縱觀詩(shī)人一生的境遇,盡管有做官的希望存在,但在追名逐利的東晉,詩(shī)人反其道而行之,熱情歌頌霜威下的正是其志之所在。
陶淵明詩(shī)范文第4篇
陶淵明,字元亮,號(hào)五柳先生,世稱靖節(jié)先生,后改名為陶潛。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shī)人、文學(xué)家、辭賦家和散文家。因早年喪父,九歲時(shí)陶淵明就和寡母寄居在當(dāng)時(shí)名士外祖父孟嘉家中,由于時(shí)代思潮和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兼具著“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ài)丘山”兩種不同的志趣。他曾懷著“大濟(jì)蒼生”的愿望,幾度投身仕途,但最終因不愿“以心為形役”而選擇了“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wú)車馬喧”;他也曾抱著“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的報(bào)國(guó)志向,但最終因“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而選擇了“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最初接觸陶淵明的著作是他的散文《桃花源記》。文中給我們描繪了一個(gè)世外桃源:以一個(gè)外人的視角描繪一個(gè)沒(méi)有階級(jí),沒(méi)有剝削,自食其力,自給自足,和平恬靜,人人自得其樂(lè)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這與當(dāng)時(shí)戰(zhàn)爭(zhēng)頻乃的黑暗社會(huì)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同時(shí)這也是作者及當(dāng)時(shí)廣大勞動(dòng)人民所向往的一種理想社會(huì)。文中所涉及的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的生活現(xiàn)狀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人們的追求與想往,也反映出人們對(duì)當(dāng)時(shí)現(xiàn)狀的不滿與反抗。這是理想中的“三農(nóng)”,與當(dāng)時(shí)的生活形成了反差。
而我則更愿意稱陶淵明為“田園詩(shī)人”,因?yàn)樗奶飯@詩(shī)則更真實(shí)地反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的“三農(nóng)”現(xiàn)象,并且他是中國(guó)古代第一個(gè)真正能夠貼近土地、貼近農(nóng)民、貼近農(nóng)村的農(nóng)民詩(shī)人。讀陶淵明的詩(shī),我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能夠和村夫野老交朋友,真正了解他們的生活情趣和內(nèi)心世界;他能夠躬耕自資,自食其力,體會(huì)農(nóng)民生產(chǎn)勞動(dòng)的艱辛困苦;他能夠關(guān)注農(nóng)村的興衰榮辱,治亂否泰,傾注情真意切的憂患關(guān)注。所以,讀陶淵明的詩(shī),更多的是體會(huì)當(dāng)時(shí)的“三農(nóng)”現(xiàn)象。而陶淵明作為一個(gè)出身仕宦的隱逸詩(shī)人,家族雖已衰微,但心高氣傲,他何以對(duì)農(nóng)民、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如此熟悉,有如此眷戀呢?下面選取幾首陶詩(shī)淺析。
一、陶詩(shī)中的農(nóng)業(yè)狀況: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陶淵明《歸園田居(三)》中寫(xiě)到的。作為士大夫,陶淵明真真切切地體會(huì)到了“晨出肆微勤,日入負(fù)耒還。山中饒霜露,風(fēng)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fù)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楊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聲閑且哀。”從這些身歷其境的勞動(dòng)詩(shī)句來(lái)看,詩(shī)人對(duì)于農(nóng)村的艱苦勞動(dòng),勤勤懇懇,盡力而為。同時(shí)我們也看到了一個(gè)早出晚歸,身上沾滿了泥水,雖精疲力竭但不抱怨的農(nóng)民詩(shī)人苦中作樂(lè)的形象。從詩(shī)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那個(gè)戰(zhàn)爭(zhēng)頻乃的年代,作為農(nóng)民要想填飽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已經(jīng)適應(yīng)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nóng)民生活的陶淵明也習(xí)慣與農(nóng)民兄弟見(jiàn)面時(shí)最多的話題莫過(guò)于談?wù)撉f稼的長(zhǎng)勢(shì)。“相見(jiàn)無(wú)雜言,但道桑麻長(zhǎng)”與村民鄰里見(jiàn)面沒(méi)有其他的寒暄,直接切入話題:桑麻的長(zhǎng)勢(shì)。從這里,我們看到了當(dāng)時(shí)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勞動(dòng)環(huán)境和情景,體察到詩(shī)人作為農(nóng)民自食其力、自得其樂(lè)的可貴,也多少了解到一些農(nóng)家的稼穡之苦。
二、陶詩(shī)中的農(nóng)村形象: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wú)車馬喧
在陶詩(shī)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shī)人筆下恬靜而和諧的農(nóng)村面貌。“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暖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shù)顛。戶庭無(wú)塵雜,虛室有余閑。”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莊、煙霧在農(nóng)村中是一些再普通不過(guò)的事物,單獨(dú)看根本就不能給人多少美感,但經(jīng)他一組合使一個(gè)有花有果、有樹(shù)有人煙的農(nóng)家美景躍然紙上。“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wú)車馬喧。問(wèn)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寧?kù)o是陶淵明在詩(shī)中著力表現(xiàn)的農(nóng)村形象,這同時(shí)也是他內(nèi)心世界的反應(yīng),只有“心遠(yuǎn)地自偏”才能做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
另外,“少無(wú)適俗韻,性本愛(ài)丘山。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十三年。”就是在他歸隱的同時(shí),陶淵明作為曾胸懷“大濟(jì)蒼生”愿望的詩(shī)人,不可能只關(guān)心自己的事情。他在歌頌農(nóng)村美好的同時(shí)也沒(méi)有忘記那個(gè)帶給他失望的社會(huì)。“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農(nóng)村的破敗怎一個(gè)“窮”字可概括,僻陋的信息給農(nóng)村帶來(lái)的直接后果就是經(jīng)濟(jì)的衰退。“荒途無(wú)歸人,時(shí)時(shí)見(jiàn)廢墟”,破敗的農(nóng)村無(wú)人居住,到處留下的是倒塌的廢墟,這樣的農(nóng)村是詩(shī)人所處時(shí)代的真正寫(xiě)照。但詩(shī)人所希望的農(nóng)村卻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土地平曠,房屋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我們也很清楚,這種主觀上的理想農(nóng)村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從陶淵明的田園詩(shī)中能更真切的體會(huì)到當(dāng)時(shí)農(nóng)村的真實(shí)狀況。
三、陶詩(shī)中的農(nóng)民形象:聞多素心人,樂(lè)與數(shù)晨夕
陶淵明詩(shī)范文第5篇
關(guān)鍵詞:玄學(xué);陶淵明;詩(shī)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化身
魏晉時(shí)期,玄學(xué)盛行,玄學(xué)是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xué)說(shuō)為主的哲學(xué)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xué)”。玄學(xué)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mén)”。玄就是總天地萬(wàn)物一般規(guī)律的“道”,它體現(xiàn)了萬(wàn)物無(wú)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xué)作為一種本體之學(xué),對(duì)魏晉六朝的文學(xué)觀念產(chǎn)生了頗為深遠(yuǎn)的影響。玄學(xué)影響到魏晉士人的人生理想、價(jià)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審美情趣,進(jìn)而影響著他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
陶淵明所生活的東晉是一個(gè)偏安的王朝,山河破碎,最高統(tǒng)治者以及士大夫們難以擺脫精神上的苦悶,而玄學(xué)的崇無(wú)清虛的要旨與社會(huì)的精神需要恰好吻合,故東晉一代,玄學(xué)大暢其風(fēng)。玄學(xué)與文學(xué)多方位交互滲透,甚或達(dá)到水融之境。在玄學(xué)思潮占主流的大背景下,陶淵明不可能不受玄學(xué)的影響,在他的詩(shī)文中,到處可以見(jiàn)到玄學(xué)影響的痕跡,但這種痕跡不像其他玄W家平典似道德論的說(shuō)教,而是一種如水中之鹽、花中之蜜的別樣的玄學(xué)之美。陶詩(shī)語(yǔ)淡情深,與自然渾然天成,其中透露著玄學(xué)中的“自然”之思,處處與玄理暗合,相得益彰。陶淵明的作品是魏晉玄學(xué)滲入文學(xué)之中所結(jié)出的碩果。可以說(shuō)陶淵明即是“自然”和“真”之玄學(xué)的化身,即所謂的“真人”。他的作品也以全新的方式詮釋了玄學(xué)的要義。
陶淵明詩(shī)歌大部分內(nèi)容圍繞鄉(xiāng)村生活,充滿玄學(xué)之美和田園氣息。
陶詩(shī)所寫(xiě)內(nèi)容皆是最平常的鄉(xiāng)村之事,但在平常的景物中,卻包含著無(wú)限豐富的內(nèi)涵,具有空靈的意境,充滿著田園氣息。如《飲酒》之五:“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wú)車馬喧。問(wèn)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niǎo)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詩(shī)人的住所雖然建在喧鬧的環(huán)境中,卻察覺(jué)不到車馬的喧嘩,這表明他的內(nèi)心是恬忍隱退的。為什么會(huì)這樣呢?是因?yàn)椤靶倪h(yuǎn)地自偏”。“遠(yuǎn)”是玄學(xué)中最常用的概念,這里體現(xiàn)了作者所強(qiáng)調(diào)的歸隱是心靈的歸隱而非身體的歸隱,以及對(duì)爭(zhēng)名奪利的世界的冷漠的態(tài)度。緊接著詩(shī)人采菊東籬,悠然自得,飛鳥(niǎo)呼朋引伴而歸,大自然的一切顯得那么有生機(jī),此時(shí)詩(shī)人心境與大自然融為了一體。自然界與人的心界此刻達(dá)到了“和諧”之美,即所謂的“真意”。而對(duì)這種“真意”卻“欲辯已忘言”。從中可以看到陶淵明對(duì)玄學(xué)中“言意”之辨的態(tài)度,這正是老莊思想所說(shuō)的“得意忘言”含義之體現(xiàn)。全詩(shī)清新自然,寫(xiě)出了詩(shī)人與世無(wú)爭(zhēng)、怡然自得的感情。完美的畫(huà)面中蘊(yùn)含著人生真諦: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應(yīng)該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個(gè)自然運(yùn)動(dòng)中完成其個(gè)體生命,這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陶詩(shī)塑造了更加渾融的藝術(shù)境界,在思想上創(chuàng)造了更加“自然”的玄學(xué)境界。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shuō):“田園景色在他筆下,不再是作為哲理思辯或徒供觀賞的對(duì)峙物,而成為詩(shī)人生活(參加了一定田園勞動(dòng))興趣的一部分。”如《歸園田居》一:“少無(wú)適俗韻,性本愛(ài)丘山。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羈鳥(niǎo)念舊林,池魚(yú)思故淵。開(kāi)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shù)巔。戶庭無(wú)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這首詩(shī)所描寫(xiě)的景物,既有田園的景物,又抒寫(xiě)了胸中之意。“質(zhì)而實(shí)綺,癯而實(shí)腴”準(zhǔn)確描繪了陶淵明對(duì)村舍風(fēng)光的感悟,也蘊(yùn)含著他對(duì)人生哲理的思考。“性”、“虛”、“閑”等皆為玄學(xué)家經(jīng)常言及的語(yǔ)詞。其中“自然”一詞,是魏晉玄學(xué)的一個(gè)核心概念。在陶淵明眼中,農(nóng)村風(fēng)景就是一幅畫(huà),就是一首詩(shī),他以詩(shī)人的心胸面對(duì)田園世界,田園世界亦培植了陶淵明心中的詩(shī)意。陶淵明在對(duì)詩(shī)畫(huà)境界的賞會(huì)與田園世界的詩(shī)意感悟的同時(shí),已把玄學(xué)思想融入其中。
相關(guān)期刊更多
干燥技術(shù)與設(shè)備
部級(jí)期刊 審核時(shí)間1個(gè)月內(nèi)
中華國(guó)際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協(xié)會(huì);杭州錢(qián)江干燥設(shè)備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