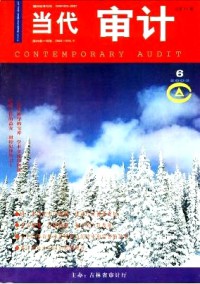當代科學哲學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當代科學哲學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1994年10月,在北京舉行了一次規格頗高的討論維也納學派及當代科學哲學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的第三天上午,5位來自3個不同國家的學者,同時出現在主席臺上,作了關于一種新型科學哲學學說——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Realism)——的講演。在許多中國學者,這是第一次聽說“建構實在論”這個名字。它到底是怎樣一種學說?它的創立者們自命為“新維也納學派”,與本世紀初的維也納學派有何傳承?它對中國當代的哲學與文化問題有何啟迪?在本文中,我將根據我與建構實在論的主要創立人,維也納大學科學理論與方法論研究所的弗里茨·瓦爾納(FritzWallner)教授的接觸,以及于1995年4至7月間,在他的研究所做訪問研究的經歷,來嘗試解答這些問題。
一、學科際與文化際的世界研究潮流
以瓦爾納教授為主的一批奧地利哲學家和科學家創立的建構實在論,公允地講,并不是一種成熟的科學哲學學說,而是一個尚在發育中的科學哲學范式。之所以它能引人矚目,之所以它已多少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則要歸功于它的學科際(interdiscipline,或譯“跨學科”)與文化際(intercultural,或譯“跨文化”)結構。它們反映了當代西方思潮中逐漸突出的兩種傾向特別是后者。這兩種傾向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的應用,正方興未艾。對應地,有兩個命題需要被高度注意:1.科學主義已經失敗了;2.西方科學不是普遍的,超文化的,而是歐洲文化和歷史的特殊產物。理解這兩個命題,將幫助我們理解建構實在論及其所在的當代西方思潮的大背景。
關于第一個命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科學主義。國內有些學者傾向于把一切強調科學之重要性的主張,例如,五四時期“科學與民主”的口號,都稱為科學主義,這是學術上不嚴密的。應該說,科學主義首先是一種反權威的和基于經驗事實的態度,“它堅持對已被接受的一切事物進行檢驗,并且在其不符合于‘經驗的事實’時予以拒斥。它自身作為一種傳統,要求在對實在界的準確感知中,排除任何外來的阻礙,無論此種阻礙是來自傳統、制度的權威抑或內在的熱情或沖動。”〔1〕自啟蒙時代以來,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就是以科學主義的立場,對一切束縛社會發展的舊傳統、舊制度進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隨著人類自我認識與完善程度的不斷提高,科學主義立場也越來越暴露出其局限性。
科學主義的要害在于它以“經驗的事實”為至高無上的檢驗標準。為此需要保證存在至少一種普遍適用的乃至永恒的方法,即科學方法,只須利用此種方法便可以從經驗事實推演出理論結果而保持住其可靠性。可以說,存在共通的因此原則上可以被形式化的科學方法,是一切西方主流科學哲學的前提假定,也是科學主義立場的基石。
最近十數年來的學科際研究卻強烈地動搖了這個基石。學科際研究提出的論點是:不同學科間存在不同的、無法統一的方法論,科學是“多”而不是“一”。
他們考察現實社會中不同學科關于同一社會問題的討論而發現,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對同一事實的注釋往往相去甚遠,這體現了他們方法論上的差異。(關于這類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可參見文獻〔2〕)實踐中這種有關應用的學科際合作,很少能達到所謂理想科學的一致性,而是在極大的分歧中,以談判的方式達成妥協式的結果。科學主義立場只是一種夢想,現實中的科學必然是“多”。
瓦爾納教授把這一學科際問題提升到思想史的層次上去考察。他認為萌生于歐洲的現代科學受到歐洲神學的影響比一般所以為的要大得多,例如在“統一思想”的觀念上,因此總傾向于設定一種“基本”科學,以統轄其它科學。這其實是沿襲了當初神學統轄其它一切門類知識的想法〔3〕。瓦爾納教授創立建構實在論的一個動機,就是從哲學上對現實社會中及思想史上的科學的“多”的一面進行論證,從而把學科際研究的有關成果上升為更具統一性的結論,即對“思維的統一性”的詰難(參見下文)。如果人類思維是無法統一的,學科際活動就應當以別樣的方式進行。
由上述簡短述評我們還可看出,關于科學的多元性的研究與另一個命題,即現代科學是歐洲文化特殊條件下的產物,是緊緊聯系著的。這就促使我們從學科際問題轉向文化際問題。
僅僅10年前,歐洲學術界還不存在所謂“文化際”的概念。當時流行的是“比較研究”,如比較哲學、比較文學等。它雖然已開諸文化平等觀念之先,但基本上還是靜態的。近10年來,由于后現代主義之類思潮對歐洲文化一些基本信念提出了強烈的質詢,知識界越來越具有開放和變革傾向。蘇聯、東歐事變雖被不少人視作歐美式自由民主理想的勝利,但有識之士卻感到,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套價值體系也同時喪失了意義,歐洲文化本身有喪失目標而陷入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之勢。今后向何處去?這成了嚴肅的話題。文化際研究無疑也肩負著歐洲文化自我理解的任務。僅僅1995年上半年,在維也納就誕生了兩個新的文化際研究團體。一個是FranzWimmer教授組織的文化際哲學研究小組,另一個是GeorgWinckler教授主持的學科際與文化際研究中心(ZIIS)。
西方文化長期被許多人奉為圭臬的理由,在于它的兩項巨大成就:民主和科學。文化際研究既然倡導文化平等,就當然不遺余力地要破除對它們的盲目崇拜。例如Wimmer教授便力圖論證東西方“人權”觀的平等地位〔4〕。在科學方面,則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現代科學作為一種萌生于西方文化中的文化現象,并不完全適用于非西方文化國家。“科學的普遍性只是一種幻覺。”“換句話說,僅僅依靠科學和技術的普遍方法就去照搬一種建立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完全陌生的傳統、歷史和現實的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是不夠的。”〔5〕科學很難說是價值、文化與制度上完全中立的。
目前非西方文化的發展中國家似乎陷入了一種非此即彼的困境:要么現代化同時西方化,要么拒絕西化但同時在現代化方面也遭到重重困難。由于現代化的趨勢是難以抗拒的,事實上除少數文化(如吉卜賽文化、印第安文化)仍在頑強抵抗之外,整個地球都在向現代化邁進。那么,我們真地要走向文化上的天下一統嗎?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包括建構實在論在內的諸種文化際科學觀,肯定發展中國家需要新的發展模式,特別是需要一種別樣的科學。用瓦爾納教授的話說:“諸種在文化上修正過的科學。”([3],p.27)新科學的誕生,很難想象其會是對西方式科學的簡單否定,或簡單地用發展中國家原有價值觀去“裁剪”西方科學,而應該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用Wimmer教授的概念說,“多話(Ploylogue”)”)中孕育出來。
在這個層次上,文化際研究的最終目標就不僅是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出謀劃策,而是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一切人類文化的并存共進探索可行之路。在女性主義者等批評者眼中,當前的西方式科學本質上就是追求對自然資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6〕以這種科學為基礎的西方式發展道路可能正在把人類帶向危險的境地。解決全球問題,需要有方法論、哲學基礎上的某種革新。瓦爾納教授創立建構實在論的另一動機,便是試圖通過文化際的科學哲學探討,來促進此種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革新。因此,目前他與我們這一批中國學者正在試圖開辟“建構實在論與中國的現代化”的研究課題。
二、建構實在論的傳承與創新
在這一學科際和文化際的潮流中,瓦爾納教授從過往哲學傳統中汲取了哪些成分,又作出了哪些創新呢?
就我的理解來看,建構實在論從過往的科學哲學中主要吸收了兩點,一是維也納學派強烈的反形而上學傳統;一是康德和維特根斯坦的建構主義。而他對過往科學哲學的批判,則是從對其核心概念——“合法性”(legitimacy)——的批判開始的。
建構實在論的全部理論與實踐,都首先根植于這樣一個認識,即傳統的,以“合法性”問題為核心的科學哲學,已不能適應學科際和文化際活動的需要。擺脫合法性的出路在于以建構主義取代摹寫主義。
“合法性”(legitimacy)或“合法化”(legitimazation)是自培根、笛卡爾時代以來認識論的首要問題,它力圖回答:人類憑什么能獲得正確的認識?換言之,人類認識如何竟能夠合乎“自然的法則”(naturallaw,通常譯作“自然規律”)?在神學時代,這個問題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上帝是自然的立法者,而人的知識來自上帝的啟迪,當然是合法的。一旦“上帝死了”,歐洲學者們就不得不為知識尋找其他的合法性依據。由于相信自然法則不是由人制定的,所以合法性依據必須是多少外在于人的東西,但這樣外在于人的東西如何又竟能與人類認識相為一體?這一直是歐洲思想史上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近現代科學哲學,直到當今的英美派科學哲學,都沒有擺脫這一夢魘。
瓦爾納教授認為,根本的出路是放棄合法性問題,從而放棄那種認為科學知識(乃至一般的真性知識)摹寫自然界的想法。在他看來,合法性及相應的摹寫真理(descriptivetruth)的概念,都是空洞的形而上學。本世紀初的維也納學派對形而上學的抨擊是正確的,問題是還不夠徹底,還假定了摹寫真理的存在,特別是假定了經驗的可靠性(合法性)。但是,經驗的可靠性不能靠經驗本身來證明,可見其只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幻想。如果徹底貫徹維也納學派的立場,就必須走向建構主義,即承認一切人類知識,都只是主體依據各種素材在頭腦中建構(construct)出來的。實在(或現實)只是建構的實在(constructivereality),這便是建構實在論名稱的由來。〔7〕
但是,如果人類知識只是建構,就會在避開合法性難題后面臨有效性難題:為什么人類憑藉頭腦中的建構能夠有效地支配外部世界?由此我們看到瓦爾納教授哲學的第二個特點是:通過區分“環境界”與“現實界”,避免了建構主義的舊有困難,并為“運行”和“闡釋”之間的區分賦予了新的意義。
傳統上,解決建構主義的上述困難有種種途徑,只是都不令人滿意。例如康德為了解釋建構的有效性,便把建構活動歸屬于一個抽象的、普遍的主體。康德并且區分開了自在之物和現象界,認為自在之物不是人類的建構,但也非人類認識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現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這就使現象界與自在之物之間的區別僅僅是玄虛的、形而上的區別。針對康德的這一缺陷,維特根斯坦拋棄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說拒絕談論自在之物,認為“我的語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維特根斯坦的建構中放棄了超驗的普遍主體,因此在《邏輯哲學論》中,他不得不假定實在論主體和唯我論主體是同一的。〔8〕不過,在他的晚期哲學中,維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構主義,他拋棄了那種認為所有語言都能達到同樣目標的主張,而認為主體性是在諸種不同的語言游戲中實現的。他也拋棄了為認識尋求某種同一的資質的想法。〔9〕
瓦爾納教授繼承了維特根斯坦的建構主義,并且通過區分環境界和現實界來避免其舊有困難。環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處在于,它是可以被人類活動所運作的。與之同時人類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環境界,換句話說,人類的此種實踐活動是不能被邏輯地測度的。在運作環境界的過程中人們建構起一些“實體”,譬如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個電子等等,這些實體并不原本地摹寫環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類認識中進行建構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總和便是人類認識的參照——現實界(實在界)。我們看到,在這里,瓦爾納試圖區分“運行的有效性”和“建構的可理解性”來解決建構主義的困難。換言之,運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構的對象,而是通過建構來實現的,因此不能成為認識論的適當話題。知識意味著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構,使知識的范圍局限于現實界。
關于“運行”和“理解”之間的區別,早已有人做出。不過,傳統的認識論始終相信,人類認識能在“運行”與“闡釋”之間建立同一。可運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標志,而理解也就意味著可以運作。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如果補充上“力量即知識”,便反映了這種思想。在瓦爾納看來,此種思想混淆了人類的兩種不同資質,模糊了人類的自我。他認為不能假設人類思維的同一性。這一觀點進一步導向了如下結論。
第三,建構實在論強調“闡釋”(理解)對科學的重要性,以及服務于此的“異離化”策略的運用,為學科際和文化際活動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來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學正在變得工具主義化,瓦爾納教授認為,這是在運行與闡釋之間不作區分,最終以運行代替闡釋(理解)的必然后果。“歐洲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把對知識的仲裁權信托給了經驗事實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條)
瓦爾納不但區分開運行和闡釋,而且認為闡釋對知識而言比運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學科(瓦爾納稱為“精神科學”)向自然科學靠攏,追求運行的有效性,便顯出是一條歧路。“從事精神科學的人們必須被看成是闡釋的主人,他們能成為自然科學家的訓練員。”([9],第2章第5.16條)“在‘硬科學,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社會的和心理的影響而污染了的科學之間的差別,將被闡釋的不定程度之間的差別所取代,被那些更能變換闡釋的諸科學和較不能變換闡釋的諸科學之間的區分所取代。在闡釋上的低水準將和知識上的低水準聯系在一起。”([9],第2章第5.17條)這樣,學科際合作的圖景就改變了。
為了有效地進行闡釋,瓦爾納教授引入了“異離化”(Verfremdung)的概念。這個德文詞在此處是從釋悟學(Hermeneutics)借用過來的,意味著把一種本文(text)從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來,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學科際問題上,異離化要求科學家們能用別種學科的語言表達自己學科內的思想,從而實現對本學科語言的反思,并達到理解。我們看到,這正是實踐中的學科際合作(或稱跨學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學科研究中,某一領域的科學家向其它領域科學家提出的問題往往是:“我的工作中還有某某環節不能實現,你們能否幫我實現?”這只是運作上的相互補充和銜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種跨學科合作雖能形成科學運作體系的龐大增殖,卻無助于理解科學的本性,更白白喪失了在學科際合作中發掘方法論革新之路的機會。
在文化際問題上,異離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否則將喪失異離化的可能性,也就喪失了理解的可能性。異離化是適用于文化際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論,在科學交流方面有特殊意義。科學原本處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當把它“輸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時,實際上是一個對科學進行異離化的過程。通過詳細考察這一過程,我們便能真正理解何謂科學,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態,最終有可能使科學交流過程不再伴隨著一種文化對其它各種文化的壓服。
三、小結
建構實在論,作為一種站在文化際與學科際潮流最前列的學說,試圖對抗的是有至少70年傳統的主流科學哲學,其所遭到的批評,其所暴露出來的不成熟之處,都是很多的。筆者曾就建構實在論請教于一些主流科學哲學家,包括羅伯特·科恩(RobertCohen)這樣的學術泰斗,他們多數對該學說并不持激賞的態度。但是該學說中呈現出來的創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當代歐洲學者最前沿的大膽探索。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悠久和強壯的非西方傳統。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維艱。從洋務派的“中體西用”,五四時期的“賽先生”,本世紀50年代提出的現代化目標,70年代“科學是生產力”與80年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直到90年代的“科教興國”戰略,中國人對科學的重要性不是沒有認識,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運行機制,使科學不但能在中國社會內部找到穩定的立足點與生長點,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應用于并推動全社會的發展。這里是否存在一個文化上的“不適應”呢?如果真是這樣,建構實在論作為一種探討科學在文化際“異離化”的科學哲學,就對中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注釋:
〔1〕Sills,DavidL.,ed.,Internation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NewYork,1972,Vol7,p407.
〔2〕Collingridge,D&C.Reeve,ScienceSpeakstoPower,London,1986,pp.37—39.
〔3〕Wallner,Fritz,AchtVorlesungeniiberdenKonstruktivenRealismus,Wien,1990,pp.19—29.
〔4〕Wimmer,Franz,DieIdeederMenschenrechteininterkulturellerSicht,StudienzurinterkulturellenPhilosophie,Bd.1(1993),S.245—264.
〔5〕約翰斯頓,安·,艾·薩松主編,《新技術與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6〕,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第7頁,第8頁。
〔6〕例如Keller,EvelynFox,ReflectiononGenderandScience,London&NewHeaven,1985,pp.36—37.
〔7〕Wallner,F.,ConstructiveRealism,Wien,1994,pp.52—59.
〔8〕Wittgenstein,L.,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5.6,5.64;見張申府譯:《名理論(邏輯哲學論)》,北京,1988,第71頁,第72頁。
〔9〕瓦爾納,弗.,《建構實在論》,吳向紅譯,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