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治清明的法治表現(xiàn)和歷史原因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宋朝政治清明的法治表現(xiàn)和歷史原因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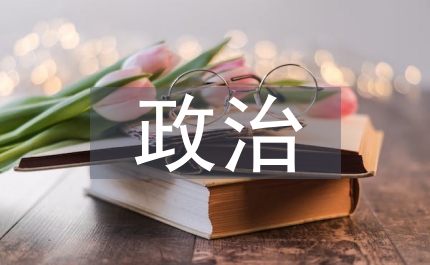
在傳統(tǒng)中國,政治清明一直是士大夫和普通民眾所倡導(dǎo)和追求的政治理念和行政方式,它在夏商周時(shí)期就已出現(xiàn)。在中國歷朝歷代都存在政治清明思想,特別是一些被稱為“盛世”、“治世”的強(qiáng)盛朝代,不僅當(dāng)時(shí)的政治人物基本上做到了“政治清明”,后世也是以此作為褒獎的依據(jù)。政治清明的立法與實(shí)踐,成功與失敗,因而也成為中國政治法律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面向。政治清明因此也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宋代,中國的政治清明達(dá)到了一個成熟且繁盛的階段。在此期間,不僅涌現(xiàn)出千古青天包拯等賢臣,還有太祖太宗等重視文治的明君;不僅有成熟完備的治吏之法,更有法制實(shí)踐中高揚(yáng)的人文主義情懷。所以,趙宋君臣的法制思想和實(shí)踐,①是研究和探討政治清明的絕好的素材和切入點(diǎn)。
一、趙宋君臣追求政治清明的法制表現(xiàn)
通過考察趙宋史事,可以發(fā)現(xiàn)趙宋王朝君臣法律思想觀念里面,②政治清明是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而為達(dá)致政治清明而進(jìn)行的法制實(shí)踐,也成為兩宋法制建設(shè)中的重要內(nèi)容。趙宋君臣對政治清明的追求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視法制建設(shè)與法律知識政治清明對法制建設(shè)和執(zhí)法司法官員的首要要求是法令完備而且執(zhí)行良好。有宋一代,雖以武開國,但重視法制建設(shè)卻是一個悠久的傳統(tǒng)。首先,皇帝重視和懂得法律,太祖說:“王者禁人為非,莫先法令”,[1](卷200)太宗說:“法律之書,甚資政理”,[2](卷16)仁宗說:“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為首務(wù)。”[3](卷143)其次,皇帝親自參與制定和修改法律。據(jù)陳景良教授考證,“從《宋史•刑法志》的記載來看,從北宋到南宋,都有皇帝直接參與法律的訂正”。③北宋神宗即“留意法令,每有司進(jìn)擬,多所是正”;南宋孝宗“法司更定律令,必親為訂正之”。再次,倡導(dǎo)律學(xué)考試。太祖建隆三年八月下詔:“諸道法司參軍,皆以律疏試判”,后形成制度。《宋史•刑法志》稱“海內(nèi)悉平,文教寖盛。士初試官,皆習(xí)律令”。《宋史•選舉志》總結(jié)說:“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tǒng)、大義、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yè)進(jìn)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jìn)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也就是說,律學(xué)考試和律學(xué)知識成為宋代士大夫參與司法活動乃至入朝為官的必備條件。皇帝對法制的重視也引導(dǎo)了士大夫的價(jià)值取向和行為,“工吏事,曉法律”成為宋代士大夫群體的一種風(fēng)尚。所謂“工吏事”,指士大夫群體從自覺的社會責(zé)任心出發(fā),強(qiáng)烈要求參政并對典章法令十分嫻熟;“曉法律”,意謂精通律條與律意。[4]這首先體現(xiàn)在士大夫群體對吏事的關(guān)注,南宋著名司法官員劉克莊即坦陳“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xí)為吏,勤苦三年”。[5](卷194)其次,士大夫爭言法令,掌握法律知識,蘇轍曾有“天下爭誦法令”之語[6](卷38),蘇軾也有“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之句。第三,士大夫積極參與律學(xué)考試并處理司法實(shí)務(wù),這一點(diǎn)從廣為人知包拯斷案故事中可以得到佐證,《宋史》中許多列傳都記載了傳主處理的獄訟事務(wù)。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宋代士大夫在司法訴訟活動中總結(jié)出了很多寶貴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如《折獄龜鑒》,《洗冤集錄》,《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成為后人研究宋代法制的重要依據(jù)。趙宋君臣重視法制建設(shè)與法律知識,為政治清明的實(shí)現(xiàn)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如果沒有法律制度上的完備,僅靠圣君賢臣的理想主義情懷,政治清明難免會如《小戴禮記》所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二)弘揚(yáng)并踐行恤刑慎刑思想政治清明要求在立法、執(zhí)法、司法實(shí)踐中體現(xiàn)“哀矜折獄”、“恤刑慎殺”的人文情懷。趙宋開國皇帝的形象在《宋史•刑法志》中是仁厚寬恕的:“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shí)躬自折獄慮囚,務(wù)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yán),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復(fù)奏輒得減宥。”事實(shí)上,在立法上,趙宋皇帝也是寬仁的。仁宗告誡大臣說:“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力行,”[7]孝宗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立法貴乎中制。”[8](卷11至12)《宋史•刑法志》記載,在執(zhí)法中,太祖下詔說:“禁民為非,乃設(shè)法令,臨下以簡,務(wù)必哀矜”,“真宗性寬慈,尤慎刑辟”,高宗則“性仁柔,其于用法,每從寬厚”。皇帝踐行恤刑慎刑的具體措施有二:其一,選用儒臣執(zhí)掌基層司法。《玉海》載“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宋史•選舉志》云:“開寶六年壬子朔始以士人為司寇參軍,改諸州馬步院為司寇院”,《宋史•刑法志》亦稱“法吏寖用儒臣,務(wù)存仁恕”。其二,親自折獄錄囚以示哀矜。[9]《宋史•刑法志》顯示,趙宋皇帝親自錄囚始于太祖,太祖不僅“每親濾囚徒”,還下詔命令兩京及諸州長官督促獄掾每五日一錄囚;太宗常說:“朕于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冤滯耳”,而且“親錄京城系囚,遂至日旰”,并重申“諸州長史五日一慮囚”;高宗也做到了“每臨軒錄囚,未嘗有送下者”。其三,創(chuàng)立“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yuǎn)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shù)。”[10]因?yàn)槭艿綄徟袑蛹壓蛯徑Y(jié)權(quán)限的限制,宋代士大夫的司法活動以解決民事糾紛為主,但他們的做法也突出的體現(xiàn)了保護(hù)孤幼的德性原則。他們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奉行“興教化,息訴訟”的傳統(tǒng),一方面又迫于矛盾必須化解,糾紛必須解決的壓力,不再把民事糾紛視為“細(xì)故”,而是十分重視,認(rèn)真審理。在審理中,他們對德性原則的把握,更強(qiáng)調(diào)推行“德性原則”于保護(hù)孤幼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之中,在啟迪人的內(nèi)在自覺性的同時(shí),努力塑造一種“溫厚樸實(shí)又聰慧強(qiáng)干”的理想人格。不言“權(quán)利”而從儒家“矜老恤幼”的仁愛意識出發(fā),既是宋代士大夫和西方職業(yè)法學(xué)家的最大不同之處,也是兩宋司法活動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④恤刑慎刑思想的弘揚(yáng)和實(shí)踐,突出地體現(xiàn)了趙宋君臣在追求政治清明過程中的民本主義價(jià)值取向。
(三)嚴(yán)防和重懲官員貪贓枉法政治清明尤其要求對貪墨官員的嚴(yán)懲不貸,嚴(yán)懲貪官污吏也是中國歷朝歷代的一致做法。趙宋雖然“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dú)于贓吏最嚴(yán)”。[11]太祖經(jīng)常告誡臣下:“朕固不吝爵賞,若犯吾法,唯有劍耳”,[12](卷12)太宗更親筆寫下《戒石銘》:“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13]在警示之外,更有嚴(yán)懲措施作為后盾。宋初,職官坐贓多棄市或杖斃于朝。[14]太祖時(shí),“大名府文簿郭凱坐贓棄市,蔡河綱官王訓(xùn)等以糠土雜軍糧,磔于市”。[15]在配套懲罰上,對貪贓枉法之官,不得適用請、減、贖、當(dāng)?shù)葍?yōu)待措施,太宗時(shí),“詔諸職官以贓論罪,雖遇赦不得敘,永為定制”。[16]真宗時(shí),審刑院主官建議“官吏因公事受財(cái),證佐明白,望論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從之。皇帝權(quán)威的高壓,加上內(nèi)心的道德自省,宋代士大夫也呈現(xiàn)出恪守操行,清正廉明的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包拯包龍圖。根據(jù)《宋史•包拯傳》記載,包拯雖貴為樞密副使,龍圖閣大學(xué)士,但“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shí)”,俗諺有云:“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老包”。死前他還立遺囑說:“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包拯之外,陳希亮,劉溫叟,真德秀等俱有清名,從而形成了宋朝獨(dú)特的“清官文化”和“清官文學(xué)”。[17]當(dāng)然,宋朝的貪墨現(xiàn)象也是存在的,特別是北宋蔡京當(dāng)國,“賄賂公行”,“廉吏十一,貪吏十九”,[18](卷43)南宋賈似道專權(quán),“賂相濁天,貪炎爍天”。[19](卷62)但是,兩宋皇帝和士大夫能夠不斷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yàn),始終把懲貪和清廉思想貫徹于司法實(shí)踐與個人修養(yǎng)之中,的確是難能可貴的。[20]不能因?yàn)橥醭┢谪澑瘒?yán)重就從整體上否認(rèn)趙宋君臣追求清正廉潔,嚴(yán)懲貪贓枉法的歷史進(jìn)步性。(四)注重訴訟權(quán)利以保障民權(quán)政治清明還要求對民眾私有權(quán)利和訴訟權(quán)利的予以有效保護(hù)。趙宋皇帝對民眾權(quán)利的保護(hù)主要體現(xiàn)在擴(kuò)大越訴范圍。宋初承接唐律規(guī)定,嚴(yán)格禁止越級告訴,太祖即下詔:“自今應(yīng)有論訴人等,仰所在曉諭,不得驀越訴狀。違者,先科越訴之罪,即送本屬州縣,據(jù)所訴依理區(qū)分。”[21](卷198)太宗、真宗亦屢次下詔,禁止越訴。但在南渡之后,民間紛爭驟起,且多有官吏舞法弄權(quán)之事,如果還嚴(yán)格壓抑民眾的權(quán)利訴求,會使政權(quán)陷入危險(xiǎn)的境地。所以,統(tǒng)治者一方面設(shè)立“民事被罪法”,重懲官吏額外講求、肆意科配的行為,另一方面增設(shè)越訴之法,擴(kuò)大百姓訴訟權(quán)利,以越訴悅民心,從而達(dá)到寬恤民力、恢復(fù)生產(chǎn)、鞏固政權(quán)的目的。[22]據(jù)陳景良教授考證,趙宋允許越訴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幾類:第一,官吏擅自苛斂百姓;第二,官吏審理案件不依法;第三,下戶為豪強(qiáng)侵奪,州縣不受理者;第四,凡豪奸公吏因戰(zhàn)火寇準(zhǔn)而侵占百姓物業(yè);第五,權(quán)貴及市舶官員利用職權(quán)違法和買番商貨物;第六,違禁刁難商旅。[23]此外,趙宋皇帝還清醒的認(rèn)識到,國家不能與民爭利,在立法中就注重保護(hù)民間私有財(cái)產(chǎn)。《宋史•刑法志》載,南宋孝宗時(shí),“丞相趙雄上《淳熙條法事類》,帝讀至收騾馬、舟船、契書稅,曰:‘恐后有算及舟車之譏。’《戶令》:‘戶絕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及二萬貫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絕,及二萬貫?zāi)巳≈怯行睦湄?cái)也。……并另削去之。’”趙宋士大夫在司法實(shí)踐中更加重視權(quán)利訴訟,具體體現(xiàn)在:士大夫從憂患意識出發(fā),開始關(guān)心注意下層農(nóng)戶的利益,認(rèn)識到“客戶乃主戶之本”,強(qiáng)調(diào)治理國家,以關(guān)心民事為首要;在審理財(cái)產(chǎn)繼承的案件中,注意保護(hù)婦女的合法權(quán)益,在室女在不同階段享有不同程度的繼承權(quán);在司法審判中開始保護(hù)孤幼及下層勞動者的權(quán)益,創(chuàng)設(shè)“檢校”制度,在某些情況下,允許“以卑告尊,以幼告長”;廣開越訴之門,注重保護(hù)下層民眾及商人的合法權(quán)益。[24]總之,趙宋君臣從實(shí)體法和程序法兩個方面都加強(qiáng)了民權(quán)的保護(hù),維護(hù)了法律秩序和政治局勢的穩(wěn)定。
二、趙宋君臣重視政治清明的歷史原因
趙宋君臣重視政治清明的原因,有一些是歷史的共性因素,如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熏陶、維護(hù)政權(quán)穩(wěn)定的需要等。這些因素多屬于老生常談,在此需要著重探討趙宋君臣重視政治清明的特殊性因素。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研究者注意:
(一)“防五季之弊”的政治共識趙宋君臣重視政治清明首先是因?yàn)閷ν硖坪臀宕肥逻M(jìn)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君臣之間達(dá)成了“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防弊”政治共識。晚唐以迄五代,政治局勢動蕩,政權(quán)更迭頻繁,法制混亂,縉紳無行,刑罰嚴(yán)苛,民眾疾苦。趙宋王朝是建立在以暴制暴的征戰(zhàn)殺伐基礎(chǔ)之上,趙宋法制文明也是從晚唐和五代的整治黑暗中走出來的。太祖、太宗通過反省史事,確立了“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政治原則和法制原則,在此指導(dǎo)下的典章制度,成為趙宋的“祖宗家法”,并被后世嗣君和臣工奉行不墜。⑤因?yàn)閷ξ寮镜姆此迹在w宋君臣重視法制建設(shè)和法律知識,以結(jié)束五季以來的法制混亂的局面,也利用法制防范后宮、宦寺、外戚、方鎮(zhèn)、權(quán)臣等可能對政權(quán)和政局造成威脅的因素。宋初恢復(fù)刑部死刑按復(fù)權(quán)又設(shè)置審刑院監(jiān)督的舉措就深刻體現(xiàn)了這一政治共識。《宋史•刑法志》載:“先是,藩鎮(zhèn)跋扈,專殺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問,刑部按復(fù)之職廢矣。”這是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司法權(quán)為武將把持的遺禍。后來,“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復(fù)。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后復(fù)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結(jié)果就是“內(nèi)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復(fù)察”,實(shí)現(xiàn)了司法審判權(quán)的分割與制衡。在此基礎(chǔ)上,“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另外,宋制,在登聞鼓院外,別設(shè)登聞檢院,受理對前者的投訴,也是基于防弊的目的。因?yàn)閷ξ寮镜姆此迹在w宋君臣秉承恤刑慎刑的思想,寬厚為懷,臨下以簡,以減輕五季以來的刑罰嚴(yán)苛。因?yàn)閷ξ寮镜姆此迹在w宋君臣特別注重打擊官吏貪贓枉法,以改變五季以來官員無行、寡廉鮮恥的面貌。《宋史•刑法志》稱:“時(shí)郡縣吏承五季之習(xí),黷貨厲民,故尤懲貪墨之罪。”開寶四年,嶺南英州知州王元吉一個多月就貪贓枉法七十多萬,太祖以嶺南兩廣之地剛剛平定,尤其要嚴(yán)懲貪官污吏,特下詔判處王元吉棄市之刑。因?yàn)閷ξ寮镜姆此迹在w宋君主注重保障民眾權(quán)益,以撫慰自五季以來飽受戰(zhàn)火煎熬和苛政侵?jǐn)_的民眾。在太祖乾德年間討伐后蜀的戰(zhàn)役中,有一位西川行營大校,殺了一位民女并割了她的乳房,太祖把大校召到京城,痛斥他的罪行,近臣設(shè)法營救開脫,太祖說:“我興兵討伐有罪的后蜀,民婦何罪,怎么能如此殘忍!”隨后就將大校斬殺。總之,趙宋君臣對政治清明的追求,最直接的動因就是對五季政治和法制黑暗的反思,并采取了有效的防弊措施。
(二)“內(nèi)省而廣大”的文化特質(zhì)宋文化“內(nèi)省而廣大”的特質(zhì)是造成趙宋君臣重視政治清明的另一特殊原因。陳景良教授指出“在儒、釋、道三家合流的基礎(chǔ)上成熟起來,以理學(xué)建構(gòu)為標(biāo)志的宋文化,不僅將綱常倫理確立為萬事萬物之所當(dāng)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強(qiáng)調(diào)人們對‘天理’的自覺意識。”[25](P321)因此,宋文化具有“廣大而內(nèi)省”的特質(zhì)。秉承這一特質(zhì)的宋代士大夫群體,不僅有著對于“天人關(guān)系”的執(zhí)著探索,還有著疑經(jīng)非圣、斷以己意、敢于創(chuàng)新、鄙薄雷同的獨(dú)立思考精神。因此有宋一代,士大夫群體積極入世,參與政治活動,表現(xiàn)出慷慨激昂的政治氣概,形成了趙宋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歷史局面。⑥正因?yàn)橛羞@樣的政治擔(dān)當(dāng)與入世精神,趙宋士大夫并不認(rèn)為知曉法律,熟諳吏事是“末技”,并不以聽訟斷獄為“鄙事”,反而積極學(xué)習(xí)和運(yùn)用律學(xué)知識,投身于司法實(shí)踐。同時(shí),也因?yàn)樗麄儗θ寮覀鹘y(tǒng)人格精神的堅(jiān)持,對儒家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捍衛(wèi),他們能夠在執(zhí)法司法活動中潔身自好、清正廉明,能夠聽訟以情、以民為本,能夠體察民瘼、保障民權(quán)。再看趙宋皇帝。太祖、太宗雖然是以武定國,但是在建政過程中,深刻體會到文治的重要性,加之因自身的奪權(quán)路徑而產(chǎn)生的對武將的深刻的猜忌和不信任感,接連提出“欲武臣讀書”、⑦“宰相須用讀書人”,⑧“事業(yè)付之書生”[26](卷30)的決策,從而實(shí)現(xiàn)了“王朝統(tǒng)治人群的轉(zhuǎn)變”。[27]后嗣君主一方面因?yàn)殂∈刈嬗?xùn),一方面也因?yàn)閺男【徒邮芪某嫉慕逃谡紊蠟槭看蠓蛄粝铝藦V闊的揮灑空間。同時(shí),也因?yàn)橼w宋皇帝受到宋文化的滲透,儒家傳統(tǒng)的恤刑慎殺思想,勤政保民思想他們的觀念中能夠生根發(fā)芽,并影響其政治法律行為。總之,趙宋君臣追求政治清明的思想和實(shí)踐,是與宋文化“內(nèi)省而廣大”特質(zhì)分不開的。
(三)豐富而多彩的經(jīng)濟(jì)生活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一定的政治法律觀念,是由其背后的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方式和狀況決定的。趙宋君臣重視政治清明的另一特殊原因,就是有宋一代豐富多彩的經(jīng)濟(jì)生活產(chǎn)生的迫切需要。陳景良教授將宋代經(jīng)濟(jì)社會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概括為:地主階級內(nèi)部士庶界限被打破;租佃制成為土地制度的主導(dǎo)形態(tài);工商業(yè)者的社會地位大為提高。[28](P320-321)因此,宋朝思想流派中出現(xiàn)了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學(xué)派”,針對傳統(tǒng)“義利觀”,他們主張“欲利可言”、“義利雙行”;針對工商業(yè)政策,他們主張“與商賈共利”,“士農(nóng)工商皆本”。同時(shí),因?yàn)橼w宋北面和西面有金和西夏兩個強(qiáng)敵,路上商業(yè)渠道被阻斷,也被迫重視海上貿(mào)易,開辟“海上絲綢之路”。在這樣的經(jīng)濟(jì)背景下,趙宋皇帝在立法上,擴(kuò)大了民事權(quán)利主體的范圍,部曲、雇匠、人力、女使都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其合法權(quán)益受到法律的保護(hù);立法還尤其注重規(guī)范和保護(hù)海上商貿(mào),專門制定《市舶條法》和市舶司。士大夫在司法活動中,也重視處理經(jīng)濟(jì)糾紛,保護(hù)孤幼權(quán)益。在司法程序上,如前所述,趙宋皇帝擴(kuò)大了基層民眾越訴的范圍,士大夫也廣開越訴之門,從程序上保障了權(quán)利的救濟(jì)。總之,兩宋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私有財(cái)產(chǎn)觀念的發(fā)展,并提出了保護(hù)私產(chǎn)、保障民權(quán)的現(xiàn)實(shí)訴求,趙宋君臣對經(jīng)濟(jì)生活需求進(jìn)行了法制回應(yīng),保障了經(jīng)濟(jì)秩序的穩(wěn)定,促進(jìn)了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保護(hù)了民眾的權(quán)利,從而反過來為政治清明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
結(jié)語
綜上所述,“政治清明”是“清明”的文化內(nèi)涵中最具探討價(jià)值的一層,通過對趙宋君臣追求政治清明的法律思想和實(shí)踐及其歷史背景的聚焦考察,我們簡要而粗淺的勾勒了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政治清明的基本內(nèi)涵,即重視法制建設(shè)與法律知識,弘揚(yáng)并踐行恤刑慎刑思想,嚴(yán)防和重懲官員貪贓枉法,注重訴訟權(quán)利以保障民權(quán)。最后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今時(shí)今日研究闡釋政治清明,并不是要復(fù)活“青天觀念”、“人治傳統(tǒng)”,不是要提倡“三綱五常”、“愚忠愚孝”,不是要恢復(fù)“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道法自然”、“倫理本位”。我們的期待在于,在民主法治價(jià)值觀念的指引下,從實(shí)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實(shí)現(xiàn)人的自我解放的意義上,來重新探尋“清明文化”的積極意義,實(shí)現(xiàn)“政治清明”的理性回歸。本文的研究,就是為這種探尋與回歸做的一種基礎(chǔ)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