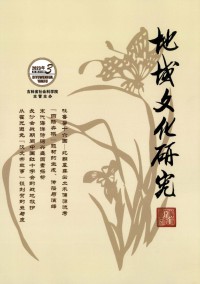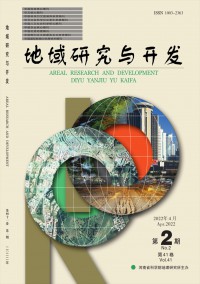地域文學在文學教學改革的功能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地域文學在文學教學改革的功能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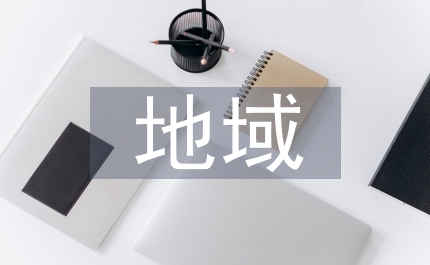
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結合當代文學自身的特點及發展現狀,筆者認為應加強當代文學教學中的地域文學內容,以地域文學為平臺充分發揮當代文學的現實性、時代性特征,并以此充分調動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人文素養。選擇地域文學作為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充分尊重并體現了當代文學的近年來的地域化發展趨勢,凸顯了當代文學的“當代性”特征。事實上,中國新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與地方色彩、地域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嚴家炎曾這樣總結:“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來說,區域文化產生了有時隱蔽,有時顯著然而總體上卻非常深刻的影響,不僅影響了作家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內容、藝術風格、表現手法,而且還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群體。’,卿)而自新時期以來,地域經驗、地域表達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日漸突出。經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及改革文學等政治理性的余波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外來刺激與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的雙重刺激下,開始尋找自我經驗的獨特存在與個性表達。一部分中國作家們將自己追尋的民族之根、文學之根深植于地域經驗、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賈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是由自己熟穩的地方一隅人手,道盡中國社會的轉型之痛,發展之惑。地域經驗、地域文化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滋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尤為可貴。當經濟大潮洶涌襲來時,文學曾經的神圣色彩、轟動效應在一夜之間喪失殆盡,此時救中國當代文學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也恰恰是極具地方色彩的文學創作,不僅僅有文學陜軍、文學豫軍、文學湘軍等的異軍突起,向文壇奉獻了諸如《白鹿原》、《日光流年》等一系列重量級作品,同時余華、蘇童、莫言等作家也將此前創作中地域氣韻進一步發展成為了獨特的文學空間。在文學險些失去深度的艱難歲月里,正是對特定文化空間的深刻剖析承擔了文學對于社會、對于人的應有的思考。對于某一特定文化空間的關注與追問,刺激了作家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特征:余華的江南小鎮,蘇童的“楓楊樹村”、“香椿樹街”,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閻連科的“耙褸山脈”,陳忠實的“白鹿原”等都成為了具有標識性意義的文化空間,也正是他們旺盛的創作賦予中國當代文學生機與活力。近年來,由于多種因素的共同促進,地方“軍”的隊伍不斷壯大,文學楚軍、文學桂軍等相繼涌現、漸成規模,并且地域文學與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語境的整體發展形成了互動,地域文學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為中國當代文學向縱深開掘提供了動力,而中國當代文學的種種焦點問題也都在地域文學的發展中得到了不同側面、不同層次的豐富展現。總體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已經呈現出并將繼續保持著地域化的發展趨勢。
豐富多元的地域文學既充分體現出當代文學的現實性與當代性特征,同時也為當代文學的教學提供了絕佳的平臺。如果想對當代文學有較為透徹的了解,必須在鑒賞與闡釋文本的基礎上進行深入思考,總結文學發展規律,因此除了培養學生的專業文學理論素養之外,還需使其逐漸具備綜合運用文化、歷史、哲學等多學科知識進行理性思考的能力。當代文學課程多開設于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各方面知識較為薄弱、尚不具備融會貫通的能力,因此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面臨著普及與提高的兩難抉擇。如果將重點停留在文本的簡單陳述及表層解說,雖然照顧了學生的興趣卻很難實現提高認識、培養素質的終極目標;如果將重點提升為深人開掘文本的內涵意蘊,學生則很可能會因難以理解而喪失興趣。事實上,尋找普及與提高之間的最佳契合點就是要尋找一個適當的平臺,這一平臺應該既能符合學生的情感經驗、理解能力又能提供進一步闡釋、提升的空間。地域文學恰恰就具備了這樣的特質。以筆者所在的河南地方高校為例,近年來河南文學的蓬勃發展就為當代文學的課堂實踐提供了難易適中的操作平臺。河南地方高校的學生來源主要是河南本地的學生,尤其是以農村學生為主,他們熟悉鄉土生活,也對變動中的中國鄉村文化有著切膚的體驗。河南作家的創作也多集中于對于鄉村、農民的描摩,文本中所涉及的場景、人物、情節等多能與學生的自身經驗產生重合。因此,學生可以通過自身經驗與文本產生共鳴,在此基礎上,教師可以適當對學生進行啟發,使學生從感性層面逐漸深人到理性思索,挖掘文本的精神內涵及審美特征。比如,在河南作家筆下密集地出現了權力書寫,作品多表現人們對于權力的瘋狂追逐及由此而來的人性的變形、扭曲。對于權力的迷戀、依賴,既源于中原文化長期以來作為正統文化典型積淀而成的集體無意識,也是中原地帶民生多艱的生存環境所造成的精神創傷。由于權力書寫所引起的對于人的存在與異化問題的關注,使得河南作家對于現代性有了新的認知,因此產生了對傳統現實主義寫作的反叛沖動,他們通過保持寫作與現實之間的彈性關系,建立突入現實的民間立場及呈現現實的陌生化策略等手段,使現實主義回歸本義,恢復了生機。高度發達的權力意識,既呈現于文本中,也沉潛于這些有著長期鄉村生活經驗的學生的精神深處,并在他們的生活中得到或隱或現的表現。教師的教學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間里,通過特定區域的生命體驗,引導學生對權力及由此而來的復雜人性有所審視,并啟發他們注意文本所采取的審美策略及藝術手法,使他們能夠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礎上獲得一定的理論訓練,審美訓練,并由此產生一定的自我精神追問。
地域文學除了能夠為當代文學教學提供難易適中,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文本平臺外,還為課程提供了生動鮮活、話語矛盾交鋒的文化生態場域。所謂文化生態場域,指的是影響文學發展的諸多因素所構成的有機體,它既包括顯性的文學事件,傳播媒介與生存機制等,也包涵著隱性的話語交鋒。文化生態場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學的發展軌跡,而文學創作、文學發展也對其有所反映和介人。研究者指出:“現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不同于古代文學,是一個只有起點而沒有終點的學科,……它與其所在的當代文化生態場域具有特別密切的關系。”叩t叨當代文學的這一特性決定了,當代文學的教學實踐除了文本、作家、文學潮流的介紹與理解之外,亦不能缺少對當代文學產生的文化場域的剖析。只有通過兩者充分的結合、互為補充,才能形成對當代文學的豐富立體的理解,使當代文學課程真正向縱深發展。文化場域雖具體可感,卻也紛繁復雜,學生對其的把握很容易流于表面,而缺少去偽存真、由具體事件上升為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如果將眾多的文化事件納人到當代文學課程的講授中,又不免會有喧賓奪主之嫌。因此,可以以學生們較為熟悉的人與事為契機,從地域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選擇典型性事件對中國當代文化生態場進行厘析。仍以文學豫軍為例。文學豫軍中的代表作家劉震云,其創作類型多樣,自以“新寫實主義”的《一地雞毛》打響名號之后,他既創作了《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這樣的充滿了眩目的敘事技巧,晦澀象征隱喻的實驗性文本,也創作了《我叫劉躍進》、《手機》式的飽含著脈脈溫情,以平實敘事感人的底層寫作,并最終將兩種創作風格完美地融會貫通,寫就了《一句頂一萬句》,以個人的成長注解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歷程,對人類寂寞的宿命進行了中國式的表達。劉震云的不斷超越,解決的并非只是作家本人的創作瓶頸問題,而是為建構良性中國當代文化生態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向。自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快速確立之時,中國文化的局勢就已經由精英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二元對立轉向了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多元競爭,并且精英文化迅速式微,大眾文化快速崛起壯大。面臨這一變局,一部分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們曾經大聲疾呼,可是他們的呼聲卻很快寥落。
更多的精英們開始痛苦地審視自身,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創作理念,試圖去尋找新路。劉震云的成功,說明了精英話語并非與大眾話語、主流話語決然對立,它還是有可能,也有能力對大眾話語的庸俗,對主流話語的刻板有所糾正的。這種將話語對立、沖突轉化為話語的匯合、互促,也未嘗不是解決問題的良策。而這種理念不僅滲透于劉震云的創作中,還表現在他的生存方式里。作為與影視結緣較早的作家,劉震云的名聲大震,一定程度上也依賴于影視作品的熱播、熱映,但劉震云參與的每部影視作品,娛樂性與思想性都得到了較好的結合。甚至包括劉震云每次出場時的著裝風格,獲得茅盾文學獎時以流行歌曲作為獲獎感言的話語方式,都充分地體現出他對精英文化的變通與改造。關于當代中國文化話語沖突的問題,是抽象的玄思,將之與學生們熟悉并引以為傲的家鄉文化名人結合起來之后,可以使抽象的問題感性化,具體化,使學生從感性體驗中逐步完成理性思考,這既提升了學生的興趣與參與意識,也符合文學研究的規律,即由感性而至理性,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并歸納問題的規律。在當代文學的教學內容中,強化地域文學,由學生較為熟悉的文本、作家、文學潮流、文化現象入手,可以達到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促進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建構的目的。但對于地域文學的引人,還要適當方可達到最佳效果。這個適當,一方面是指量要適當,引人地域文學,并非把當代文學史講成某一地的當代文學史,而是要從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來看地域文學,以地域文學的具體個例來對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進行闡釋。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要適當,即在講解地域文學時,仍需不時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比較,從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中發掘共性問題,把對地域文學的微觀個體考察引向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宏觀整體的規律把握,并從地域文學特殊的解決方式中尋找到某種新質。因此,在當代文學教學實踐中適度、科學地加人地域文學的內容,將有助于突出當代文學現實性、當代性的特征,并且能夠使教學實踐在一個難易適中,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文本平臺上展開,有助于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他們的參與意識,使他們能夠由感性的文本閱讀逐漸深人至理性的規律把握,并對當代文學文化生態場域有一定的了解,達到培養藝術審美與人文精神綜合素質的教學目標。
作者:張翼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文檔上傳者
- 地域產品保護制度
- 談地域文學的時代感與地域性
- 地域文化旅游文化品牌
- 淺論民間美術地域特征
- 當代公共藝術地域性表達
- 公共藝術與地域價值
- 地域性設計戶外廣告論文
- 現代藝術對地域景觀演進的益處
- 地域文化在園林設計的應用
- 地域文化室內設計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