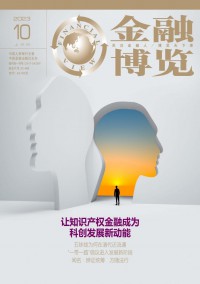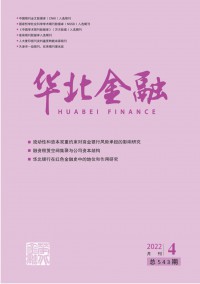金融發展財政支出對城鄉貧富懸殊的作用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金融發展財政支出對城鄉貧富懸殊的作用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問題的提出
城鄉收入差距日趨擴大,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據中國社科院的2011年《城鄉一體化藍皮書》顯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已達到國際公認的結構失衡程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比值,從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除少數幾年外,絕大多數年份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根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二元經濟結構。但是,該差距并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從某個角度看,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矛盾,與長期以來城鄉發展不協調有很大關系。
二、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對于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最為典型的是庫茲涅茨(Kuznets,1955)提出的倒U曲線假說。他認為當收入水平較低的時候,金融發展會擴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而當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金融發展有助于緩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目前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差距之間的關系并無定論。例如,許平祥(2011)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數與金融中介之間的倒U字假設能通過檢驗,即存在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效應。田杰、陶建平(2011)運用1701個縣(市)的面板數據,驗證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效率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由于我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制度以及農村金融環境都與國外不同,因此,庫茲涅茨效應可能在中國金融發展中并不成立。例如,王征和魯釗陽(2011)運用動態面板模型證明農村金融發展的規模、結構和效率與城鄉收入差距正相關,而并非倒U型關系,即農村金融的發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各學者的研究結論之所以出現較大差異,主要是研究方法、樣本時間以及模型中其他控制變量不同所致。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之間究竟是倒U型關系還是單純的線性關系。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不均衡,而且各地區之間金融制度和經濟主體行為差異較大,基于總體樣本得出的結論可能并不適用于某一特定地區。另外,政府在我國當前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的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必然存在著重要影響,而已有研究成果很少將政府財政支出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對金融發展和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進行比較的研究更是鮮見。基于此,本文通過構建區域虛擬變量,運用我國1993—2010年省際面板數據,比較研究了金融發展規模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水平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深入剖析這種影響在區域上的差異,進而提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及模型設定
1.城鄉收入差距指標(Y)。王少平和歐陽志剛(2008)提出用泰爾指數來衡量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但該指標計算過于復雜,而且對中等收入水平的變化不敏感。國際上應用較為流行的基尼系數,則由于我國相關統計資料的缺乏,難以準確計算。鑒于此,本文將目前學者們使用較多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作為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的指標。2.金融發展指標(fir)。目前衡量地區金融發展水平,主要從金融發展的規模、結構和效率三方面測度。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測量的角度不同,不會對研究結論造成實質性影響,因此本文選擇以金融發展的規模來度量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麥氏指標(M2/GDP)和戈氏指標(貸款/GDP)是目前衡量金融發展規模常用的兩個指標,國內很多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麥氏指標無法有效地解釋中國M2/GDP偏高的問題。因此本文選用戈氏指標,將金融發展規模定義為各省人民幣貸款余額與各省GDP之比。3.財政支持指標(fis)。為了體現地方政府一般性財政支出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考慮各地區經濟總量的差異,本文選擇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總額與各省GDP之比來衡量地方財政支持的力度。4.其他控制變量。除了金融發展和財政支持外,根據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如下因素也會對城鄉收入差距造成影響:(1)城鄉就業結構(emps)。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鎮,外出務工收入已經成為農村居民純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即使在農村內部,來自二、三產業的非農產業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基于此,本文將城鄉就業結構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并將城鄉就業結構定義為emps=(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總就業人數。(2)地區開放程度(open)。本文將地區開放程度定義為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已有文獻大多選擇城市化水平作為控制變量,并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地區城市化的指標。但本文認為,由于我國目前城鄉戶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外出務工人員選擇了“離土不離鄉”的就業模式,因此以戶籍所在地為計算依據的城鎮人口數量無法反映城鎮實際的人口數量。而地區開放程度往往與城市化水平正相關,同時地區開放程度還會對勞動力的就業觀念產成影響,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因此將開放程度作為模型中的控制變量更為合理。5.區域虛擬變量。為了對比金融發展和財政支持對不同地區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設置了west和mid兩個虛擬變量:若該截面屬于西部地區,則west=1,否則west=0;若該截面屬于中部地區,則mid=1,否則mid=0。虛擬變量作為解釋變量有兩種引入模式:加法方式和乘法方式。經反復嘗試,作為加法方式引入模型中的兩個虛擬變量都不顯著,即區域因素只會影響相應解釋變量的系數,而不會對模型的截距項產生顯著影響,因此選擇乘法方式引入虛擬變量。綜上所述,最終設定的面板數據模型如下: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省份和第t年,e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數據說明
為避免我國經濟金融數據結構性斷點問題對實證結果的影響,同時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借鑒王征等(2011)的分析思路,將樣本的時間跨度確定為1993—2010年。本文有關農業貸款的原始數據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其余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數據庫和CCER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由于重慶在1997年后才成為直轄市,為便于研究,將其數據合并到四川省,最終的數據涉及30個省級單位。在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劃分上,本文以各省地理位置為主要依據,同時參考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將四川(含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劃分為西部地區;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為中部地區;其余11個省級行政區為東部地區。
(三)數據平穩性及協整檢驗
由于大多數經濟變量都是非平穩變量,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很容易導致“偽回歸”,因此需要對面板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平穩性檢驗的方法主要有LLC檢驗、IPS檢驗以及Hadri檢驗。其中LLC檢驗的原假設是截面單元含有相同的單位根,IPS和Hadri檢驗的原假設是截面單元含有不同的單位根,具體的檢驗模型根據各變量序列的趨勢進行選擇,檢驗的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5%顯著性水平下,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在面板數據模型中,由于個體的異質性、非平衡面板數據、空間相關性以及縱剖面時間序列的協整性等問題的存在,使得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遠遠復雜于時間序列的協整檢驗。常用于面板數據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高(Kao,1999)提出的同質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和佩德羅尼(Pedroni,1999、2004)提出的異質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本文利用佩德羅尼檢驗方法對變量間的協整關系加以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協整檢驗的組內和組間統計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因此可以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四)模型估計與分析根據截面單元是否存在個體效應以及個體效應和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可以把面板模型分為混合數據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不同的模型對應不同的估計方法,而且不同模型的估計結果有較大差異。為了選擇最合適的模型,本文同時給出了上述三種模型的估計結果和相應的檢驗統計量(見表3)。固定效應模型對應的F檢驗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個體效應不顯著的原假設,因此固定效應模型比混合數據模型更合適。Breusch-Pagan檢驗的結果顯示,存在個體隨機效應,因此隨機效應模型比混合數據模型更合適。Hausman檢驗對應的概率值表明,可以在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個體效應和解釋變量無關的原假設,即固定效應模型比隨機效應模型更合適。綜上所述,固定效應模型是最優選擇,因此選擇表3中第1列的回歸結果來分析金融發展和財政支持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合適的。具體來說:
1.金融發展規模的影響。
可以看出,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是正相關的,而且在1%水平下顯著。但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則呈負相關關系,而且相對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規模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的效果更為顯著。這說明金融發展規模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這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也是相符的。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脫農化傾向,大量的資金從農村流向城市,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相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在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下,較好地支援了農村的發展。
2.財政支持的影響。
總體來講,地方財政支出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但其影響程度按照東部、中部、西部的順序依次遞增。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面臨發展地方經濟和政績考核的壓力,尤其是財政分權后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權得以增強,這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目標偏向于經濟增長而忽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公平目標。中西部地區由于城鄉生產率差異較大,因此地方政府財政偏向的程度更為明顯,而東部地區城鄉生產率差異相對較小,財政的偏向程度也相對小一些。
3.其他變量的影響。
(1)城鄉就業結構。從表3中可以看出,城鄉就業結構與城鄉收入差距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這意味著雖然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竭力增加農民收入,但單純的生產性勞動收入對農民純收入的提高貢獻有限,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農業生產,選擇外出務工,而農業人口的減少又進一步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2)地區開放程度。從估計結果看,地區開放程度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這主要是由于我國與對外貿易相關的產業主要集中于城鎮,貿易發展主要提高了城鎮居民的收入,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不大。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前提下,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了東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但是對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則有抑制作用。這主要是由于國家產業政策對中西部地區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西部城鄉金融資源的配置。財政支出水平則與城鄉收入差距呈正相關關系,與東部地區相比,這種現象在中西部地區更為明顯。基于以上結論,本文認為,對于西部和中部地區,應繼續制定和落實有關政策,鼓勵、引導資金支持農村建設,進一步鞏固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成果。通過建立農村資金回流反哺機制,逐步緩解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約束和金融壓抑問題。與中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則呈現出一定的脫農化傾向。因此,在保證中西部地區金融支持的同時,也不應忽視東部地區城鄉金融的協調發展。與此同時,應改善地方財政支出結構。過于追求GDP的增長必然導致財政支出追求短期經濟利益,擠占農業支出。因此有必要將經濟發展的公平性和人民生活質量等指標納入考核體系,促使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部門,將財政支出的重點逐漸向農村地區傾斜。